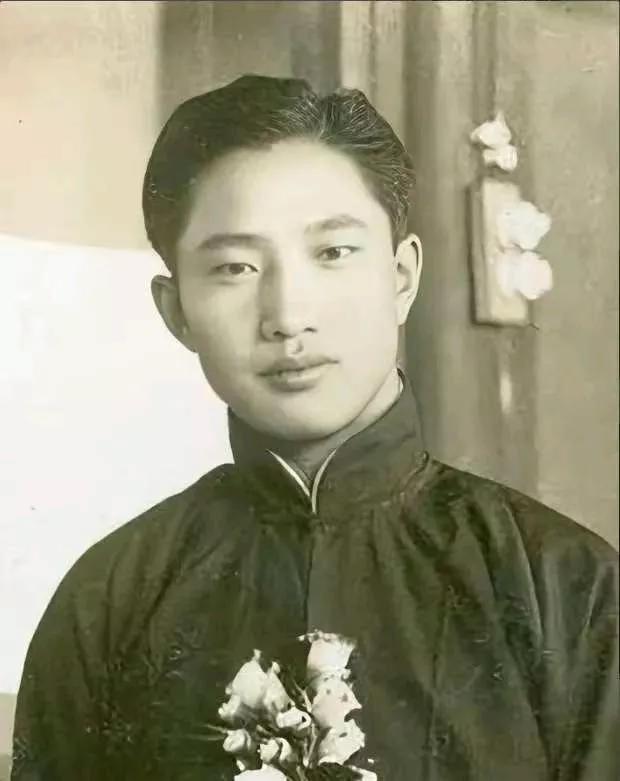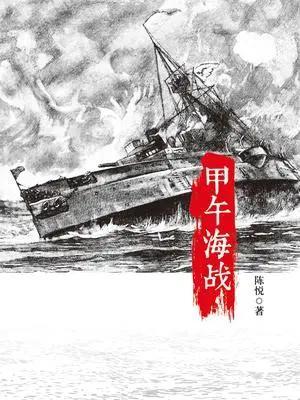1968年一个深夜,周恩来刚躺床上,准备睡觉。警卫员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间,总理突然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 1968年,外面风雷激荡,内部盘根错节。他每天要处理的事,堆起来能把人埋了。咱们今天上班摸个鱼都觉得累,你想象一下他那会儿的压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脑子里盘的,不是明天要见的下一个外宾,也不是要批的下一份文件,而是一个警卫员,在他身边待了多久。 那个警卫员叫高振普,当时愣了一下,回答说:“快两年了。” 总理“嗯”了一声,又问:“家里都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他关心的,从来都是具体的人。不是一个模糊的“人民”概念,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家庭、有困难的张三李四。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一种本能。 聊到这儿,想起另一件关于“家”的事。 总理的家,在中南海西花厅。说是个家,其实就是个办公室加宿舍。那房子老旧,夏天返潮,地上能泛出白花花的碱。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都心疼,好说歹说,劝他修一修。最后总算拿“保护文物”的名义让他点了头,但总理有言在先:“哪里坏了修哪里,绝不能铺张浪费。” 结果,秘书趁他外出,想着让总理住得舒服点,就自作主张,把青砖地换成了木地板,还添了新地毯、新窗帘、两把沙发。这在咱们今天看来,算个啥?顶多算个精装修。可总理回来一看,站在门口,脸都沉下来了。 他没进屋,直接问:“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 秘书赶紧认错。总理一摆手,指着屋里:“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否则我不进!这不是我的家!” 什么意思?在他心里,这个“家”一旦超出了普通公民的标准,变得“特殊”了,就不再是他的家了。他的家,必须和亿万中国人的家,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哪怕一丝一毫的“特权”。 最后,新添的东西全搬走了,西花厅恢复了旧貌,总理这才肯进屋。事后他还在会上几次三番地作检讨,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 他的“家”,小到可以不住,但他的“国”,大到他拿命来撑。 现在的生活好了,西花厅那样的老房子,很多人都看不上了。我们讨论的是消费升级,是AI如何改变生活,是去哪个国家旅行。这当然是好事,说明国家发展了,这盛世,如他所愿。 但与此同时,有些东西,是不是也变味儿了? 前阵子刚处理了一批干部,豪宅、豪车,生活奢靡得让人咋舌。他们的“家”倒是富丽堂皇,可“国”在他们心里还剩多少分量?总理那句“这不是我的家”,今天听来,格外振聋发聩。一个领导干部,一旦把个人的安乐窝看得比人民的福祉更重,他就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这不仅仅是针对官员。我们普通人也一样。 现在的社会,精致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大家都在算计自己的得失,追求个人的“小确幸”。这没错,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只剩下这个,那就危险了。 总理不一样。他的一生,是“无我”的一生。 他没有子女,他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他的孩子。他没留下遗产,他的所有工资,除了日常开销,大部分都交了党费,或者资助了身边有困难的同志。他甚至没留下骨灰,他说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继续为人民服务。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太“圣人”了,离我们太远。 其实不是。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他会因为在延安坠马,右臂留下终身残疾而痛苦;他会在看到邢台地震的惨状时,当着所有人的面流下眼泪;他会和妻子邓颖超写信,落款是“吻你万千”。 他所有的“不近人情”,都只针对他自己。 他把所有的温情和柔软,都给了别人。 就像1968年那个深夜,他累得马上就要睡着了,心里还惦记着那个两年没回过家的警卫员。 这种对“人”的极致关怀,和对自己“神”一般的严苛,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周恩来。 说到底,他守护的,是一种信念,一种秩序。 他相信,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相信,国家总理,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这个国家的公职人员,立下了一个叫“周恩来”的标准。这个标准,直到今天,五十年过去了,依然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合格的最高标尺。 我们今天纪念他,学习他,不是要过他那样的苦日子。时代不同了,我们完全有条件,也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真正要学的,是他那份精神上的清醒和自持。 是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懂得如何取舍;是当你有能力为自己谋取更多便利的时候,还能不能像他一样,问自己一句:“凭什么?” 总理的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凭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凭我是人民的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