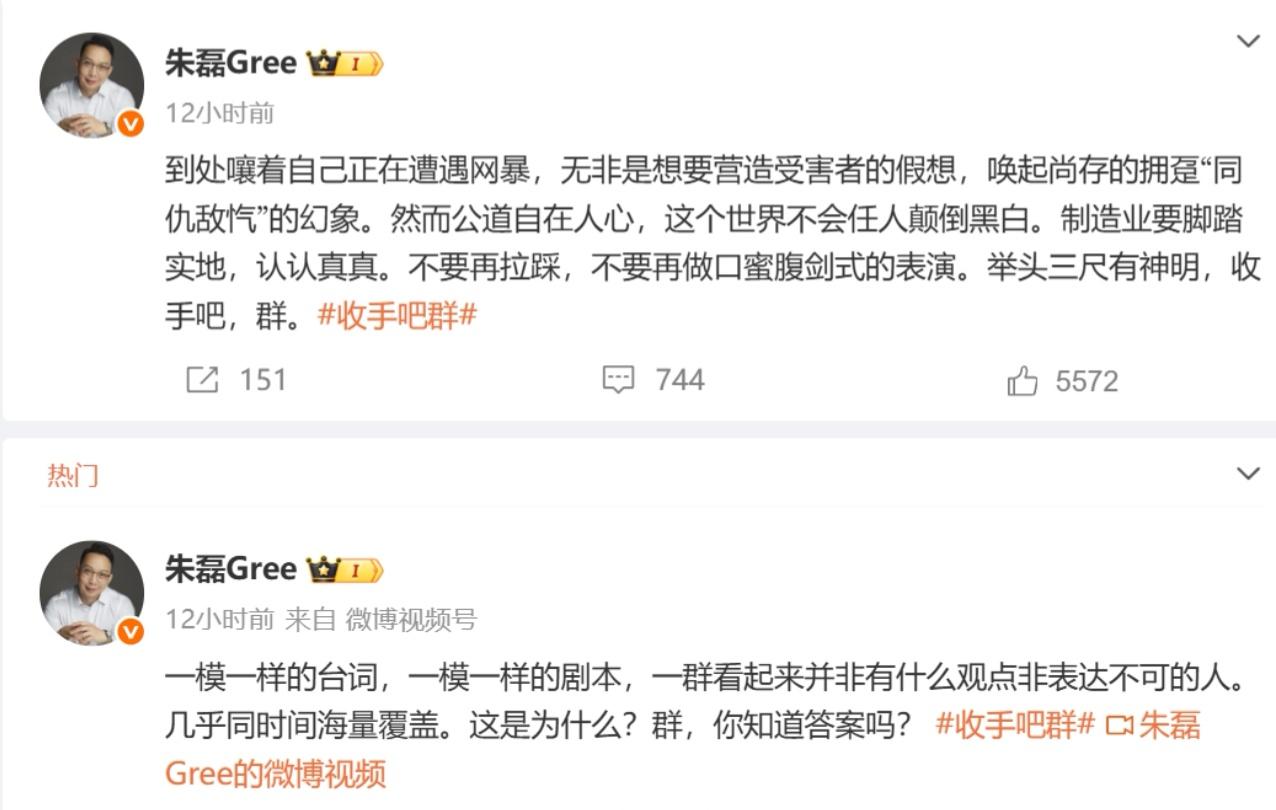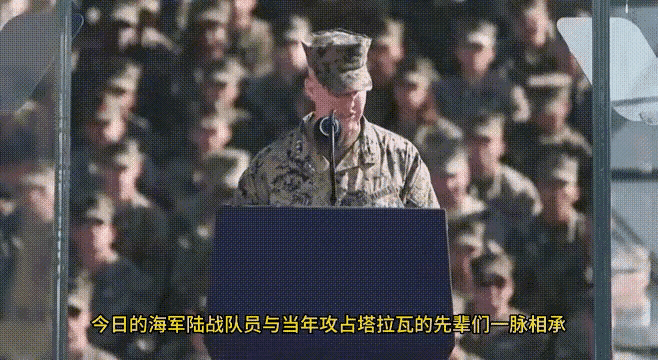1932年,12岁的段桂秀嫁给了21岁的王金长,新婚第3天,王金长去参军,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段桂秀拒绝改嫁,87年后,段桂秀在王金长的墓碑前大哭:“金长哥,我等了你整整87年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19年春天,江西于都的山头刚披上一层绿意,烈士陵园的石板路还带着雨后潮湿的味道,段桂秀拄着竹棍,一步一顿地走上台阶,她已经走不快了,岁月把腰压弯了,眼睛也看不清了,但她知道自己要找什么。 碑石一列列排开,像沉默的战士站得笔挺,她的手在碑面上慢慢摸,指尖粗糙干裂,像一把锈了的钩子,勾起了埋藏几十年的记忆,摸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时,她的身体突然前倾,整个人扑倒在碑前,额头贴着冰冷的石面,唇边颤了又颤。 她出生在1920年,刚满月就被送到了王家,那个欠收的年头,父母用一袋糙米把她换出去,别人家的童养媳是下人,她却遇上了好人家,婆婆心软,喂她米汤,王金长大她几岁,从不欺负她,还会分自己抓的鸟蛋和山果给她吃。 她和王金长一起长大,打小就跟在他后头,他上山砍柴,她在山脚摘野莓;他插秧,她提着篮子捡田螺,她学会的第一个词不是“娘”,而是“哥哥”。 十二岁那年,她穿上红褂子,嫁进王家,没有锣鼓,没有鞭炮,一张八仙桌上摆了几样粗茶淡饭,她坐在炕沿上,手里捏着绣花帕子,心里忐忑又欢喜,这场婚礼简单却热烈,她以为余生就是和他一起种地、养鸡、过日子。 三天后,王金长报名参军,她不懂什么是红军,只觉得天突然塌了一角,他走的时候,她站在村口,双脚像钉在地上,他把一件旧外衣塞给她,还留下几块银元,她没说话,只是一直看着,直到他背影消失在河雾里。 婆婆身体不好,躺床上起不来,小叔子还要喂饭,段桂秀年纪小,个子瘦,力气却大得吓人,她每天去挑水、背煤、烧石灰,肩膀被竹筐磨破,眼睛被石灰熏得红肿,别人劝她别撑了,改嫁过日子去,她不说话,只顾干活。 她等,一年又一年,她不认字,也不识方向,但她知道王金长说过会回来,她记得那件外衣的味道,记得他走时穿的布鞋,她觉得,只要她不忘,他就不会走远。 1949年听说解放了,有人说红军回来了,她就天天守在村口,一批批部队经过,她眼睛都不眨地盯着,可一个个都不是她要找的人,有人问她找谁,她说找人,问叫什么,她只说叫王金长。 1953年的春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她正在院子里喂鸡,信被风吹到竹竿上,她够了几次才拿到,信封粗糙发黄,里面那张纸写着烈士两个字,她愣了好久,最后蹲在地上不动了,鸡在她脚边走来走去,啄着撒落的谷子。 她不信,她把那张纸锁在箱底,像锁住一个梦,别人再劝她改嫁,她还是不答应,她说守家要紧,为了撑起家,她把小叔子的儿子过继过来,给孩子取名“地长”,希望这份情分能像土地一样长久。 她老得慢,别人白发了,她还是黑发,别人走不动了,她还能挑柴,她不去庙里烧香,也不求神拜佛,她只求一个人能回来,她把红布留在屋檐下,那是结婚时的喜布,她每年晒一次,怕它褪色了。 1978年,继子成亲,她从箱子里拿出那块红布,挂在新房门口,村里人都说那布有福气,后来谁家娶媳妇都来跟她借,她也乐意,每次都叮嘱一句:“用完还我,” 几十年过去,她的家从茅草屋变砖瓦房,家里的孩子也一代代长大,她抱上了重孙,墙上挂上了新画,那幅画是画家根据资料画的王金长,方脸宽额,眉骨上一道浅痕,她常坐在画像前发呆,像在和画里人说话。 她从不把王金长称作“丈夫”,也不说“老公”,她一直叫他“金长哥”,这个称呼,她用了近百年。 2019年那天,她终于站在了那块石碑前,她的眼睛看不清,但手指摸得出那个名字,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贴着碑,一遍遍地摸,那是一种确认,也是一种告别。 那年夏天,家里人带她去了北京,她坐着轮椅进了天安门广场,摸着栏杆,看着升旗,她不说话,只是看,她知道他没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但她替他看了,她来告诉他,新中国真的来了,家也守住了。 她今年一百零六岁,眼睛花了,耳朵背了,但她还记得他,屋子墙上那幅画像前,她坐着的竹椅从来没挪动过,她每天都要坐上去,看一会儿。 她说过一句话,别人问她苦不苦,她听完笑了,没说话,有人再问她后悔吗,她只摇头,她说得最多的句子就是:“我在等,” 春风一年年吹绿山头,村口的大樟树也换了新叶,她坐的那个角落,阳光总是刚刚好,照在她的发丝上,像为她的等待镀上了金光,她等了整整一生,从少女等到老妪,从旧中国等到新世纪,等到石碑落字,画像上墙。 信息来源:(中国国防报——从青丝到白发,106岁的她还在默默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