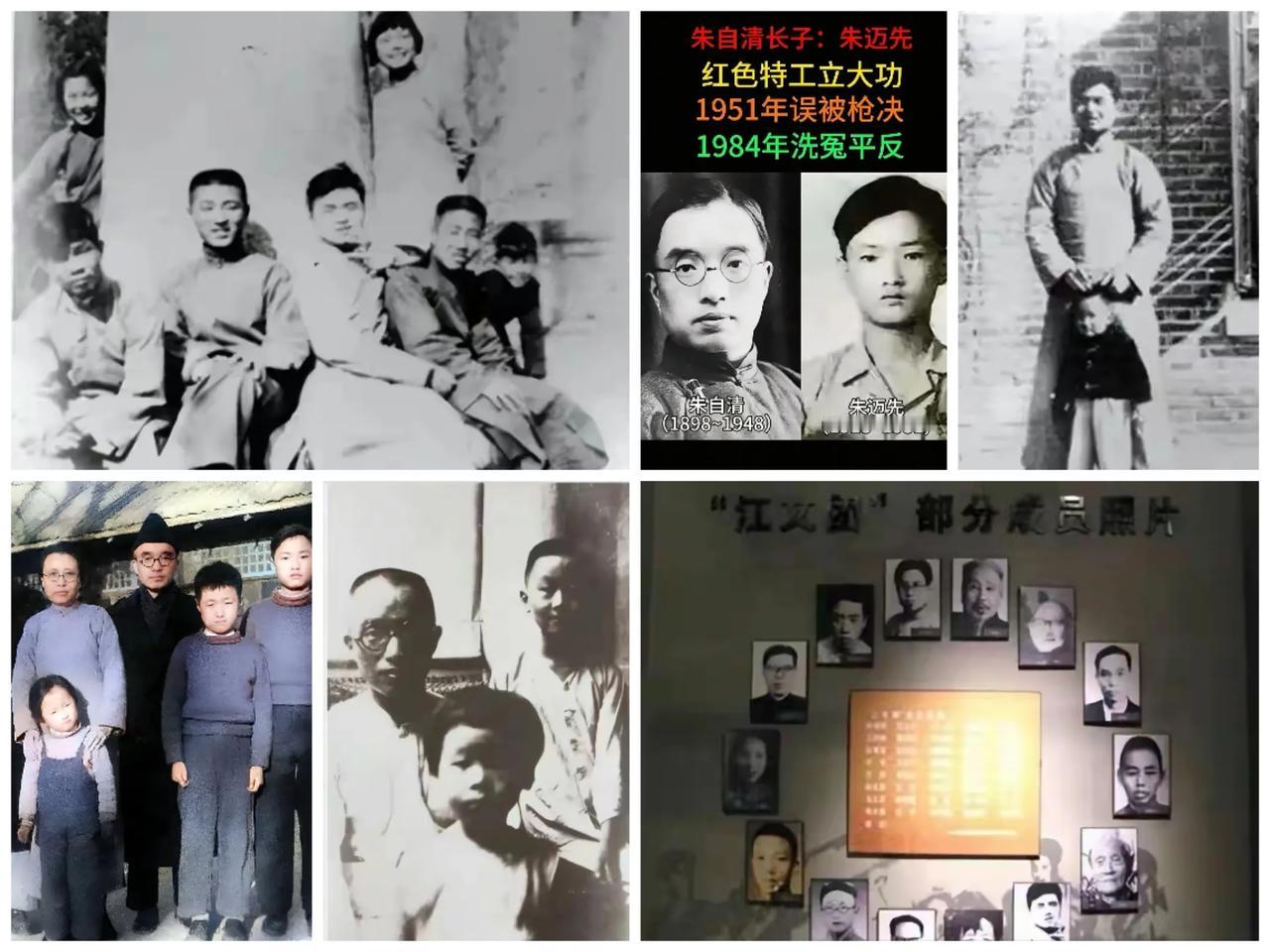34岁的王牌特工涂作潮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想要一个老婆,但是必须要满足他两个要求:第一,这个女人不能太有文化;第二,这个女人必须要有孩子… 这事发生在1930年代末的上海。那时候的上海,街头车水马龙,楼上是租界,楼下是岗哨,白天是商人,晚上是战场。 而涂作潮,正是这个看似平静世界背后的“影子”。 他在上海的身份是“蒋林根”,恒利无线电修理铺的老板。 买卖不大,一栋楼住他一个人,楼下一摊烂电线,楼上却藏着一台特制的电台。 这电台,能把延安最新的命令传到法租界,也能把情报从南京带到重庆。 可问题来了,他太孤独了。不是心情孤独,是身份孤独。 一个三十好几的老板,整栋楼没人住,没老婆没孩子,这在老上海就是个大问题。 邻居米店的老板有天实在忍不住,当着街坊的面问他:“蒋老板,你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那一刻,涂作潮知道,再不想办法,他就不是暴露的问题,是死的问题。 于是,他向组织开口了,但这条件一开,谁听了都得皱眉头。 “老婆不能太有文化。” “必须带个孩子。” 说实话,换别人讲这话,组织估计当场就把人拉去“思想汇报”了。 但对他,没人敢轻易否定。因为他不是普通人,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无线电专家。 1928年,他从长沙出发,辗转被送到苏联,原本是去学理论,结果英文不行,数学也不行,差点被劝退。 他咬牙换了方向,硬是把无线电维修学成了“拿手绝活”。 回国后,他一手改装了七瓦特的隐蔽电台,还教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李白。 他懂技术,更懂潜伏。所以他说要结婚,组织不敢不听。 可这两个条件,麻烦就麻烦在,太细了。 “不能太有文化”,怕的是女人聪明过头,一不小心看懂了密码本; “必须带个孩子”,是为了立刻营造出“二婚男人”的形象,减少邻居的好奇心。 这不是挑老婆,是挑“战友”。而且是你不能说实话,还得演一辈子的那种战友。 几天后,媒人找来了张小梅,纱厂女工,文盲,丈夫肺病死得早,带着五岁儿子住在姑妈家。 她来相亲那天,穿了件洗旧的花布衫,低头站在门口,一句话不多问。 涂作潮看了她一眼,转头点头:“行,就她。” 结婚没多久,规矩就立下了: “阁楼不能上,晚上不能问,东西不能动。” 张小梅什么都没说,照做了。她不是不疑惑,而是太懂没得选。 她带着儿子,突然有了个家,吃穿不愁,还有人尊重她。 她不问,是因为她明白,这男人身上有秘密,问了,就是祸。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邻居也慢慢不再多嘴。 张小梅每天带娃、做饭、洗衣服,楼下是家庭,楼上是战场。 后来她又生了三个孩子,家里越来越像“正常人家”。 谁都想不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商人,晚上在阁楼上操作的,是能决定战局的电波。 可战争不会让人安稳太久。 1942年,叛徒出卖,李白被捕,整个上海地下网络被连根拔起。组织下令:“马上撤离。” 涂作潮知道,这次走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破例,把张小梅带上了阁楼。 他把自己的真名说了出来,把过往也交代清楚:“我叫涂作潮,不是蒋林根。我要走了,如果我回不来,有困难,你就找毛泽东。” 张小梅没哭,也没问,只是点了点头。 他走的那天,天还没亮。她站在门口,抱着最小的儿子,一句话没说。 这一别,就是整整一年。 1943年,组织终于找到了张小梅,把她和孩子带到了延安。 她下车那天,涂作潮已经在窑洞口站了很久。他看着她,眼圈一下就红了。 “你还好吗?” 张小梅没应,只是把孩子往前一推:“你儿子,长高了。” 后来他们在延安重建了家。战争还没结束,但他们终于可以不用演戏地过日子了。 信息来源:《涂作潮:为天论曲直 不改绳墨心》——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