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6岁了,运气好的话还能活二十多年,运气不好的话,随时都可能会离开。因为我有好几个同学,闺蜜都提前走了,有几个才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更让人扎心的是,就算我能活80岁,我也只剩二十多年了。 前阵子整理旧物,翻出和玲子她们的毕业照,照片上她扎着马尾辫,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去年同学聚会还说要一起去爬泰山,结果没过仨月,她老公就发消息说人没了,心梗,走得突然。 56岁这年,我开始算一道减法题。 不是房贷,不是存款,是日子。 运气好,能活满80岁,减法结果是24年;运气不好,就是未知数—就像我那几个提前交卷的同学,有的刚过45岁,朋友圈停在春天的花田里,再也没更新。 前阵子收拾阳台角落的旧纸箱,翻出个落灰的铁盒子。 打开时呛得我打了个喷嚏,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亮盒底压着的毕业照。 边角泛黄,塑料相框磨出毛边,照片上玲子站在第三排左数第二个,扎着高马尾,发梢还翘着几缕碎毛—那是当年流行的“不听话发型”,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左边那颗牙尖上还有个小小的豁口,是初中啃苹果硌的,她为此别扭了好久,说像只傻兔子。 我拿手擦了擦相框,指腹蹭过她的脸,照片上的油墨有点发黏。 去年深秋的同学聚会,她穿件驼色大衣,坐在我对面剥橘子,橘子汁溅到桌布上,她说“开春咱去爬泰山吧,就咱几个,不带老公孩子,从红门爬到玉皇顶,看日出时喊一嗓子,把这些年的烦心事都喊出去”,我们都笑她矫情,说她儿子都上大学了还学小姑娘说“烦心事”。 结果开春还没到,三月底的一个周三下午,我正蹲在厨房择菜,手机震了震,是玲子老公发来的消息,就一句话:“玲子走了,心梗,今天早上。”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分钟,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我没关,直到蒸汽熏得眼睛疼。 后来同学说,她走得突然,早上还跟老公说“晚上包韭菜盒子”,刷着牙就倒了,没遭罪—有人说这是福气,可我总想起她剥橘子时,指甲缝里沾着的橘络,想起她笑起来虎牙上的豁口,想起她说“爬泰山喊一嗓子”时眼里的光,福气吗?我摸着照片边角,倒觉得像欠了她一场日出。 收拾完旧物,我把那张毕业照摆在了客厅的书架上,就在我常坐的沙发对面。 现在每天早上喝豆浆时,我都会看一眼照片上的玲子,看她翘着的发梢,露着的虎牙。 人这一辈子,到底是长还是短呢? 短到一个约定还没来得及兑现,一个橘子还没剥完,就再也没机会说“改天”;长到一张泛黄的照片,能让你在56岁的某个清晨,突然明白“珍惜”不是句空话,是此刻能摸到的温度,能拨通的电话,能说出口的“我想你了”。 那天晚上,我翻出通讯录,给三个久未联系的老同学发了消息,没说别的,就问“周末有空吗,出来喝杯茶”。 有人秒回“好啊,老地方见”,有人隔了半小时回“刚哄完孙子,明早我去接你”。 现在看日历,不再是数“还有多少天过年”“还有多少天发工资”,是数“还有多少个周末能和她们喝茶”“还有多少个春天能一起去爬泰山”。 或许我们都怕“提前走”,可比起“走得突然”,更怕的是“该说的话没说,该见的人没见,该一起做的事,永远停在了‘再说吧’”。 书架上的照片还在那儿,玲子的虎牙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我想,等下次见到那几个老同学,我要跟她们说:“咱下周就去爬泰山吧,别等开春了,现在山上的叶子正红呢—反正我们都没那么多‘以后’了,可我们还有‘现在’啊。
56岁那年,我开始算一道减法题:余生只剩24个春天
小依自强不息
2025-11-28 16:19:38
0
阅读: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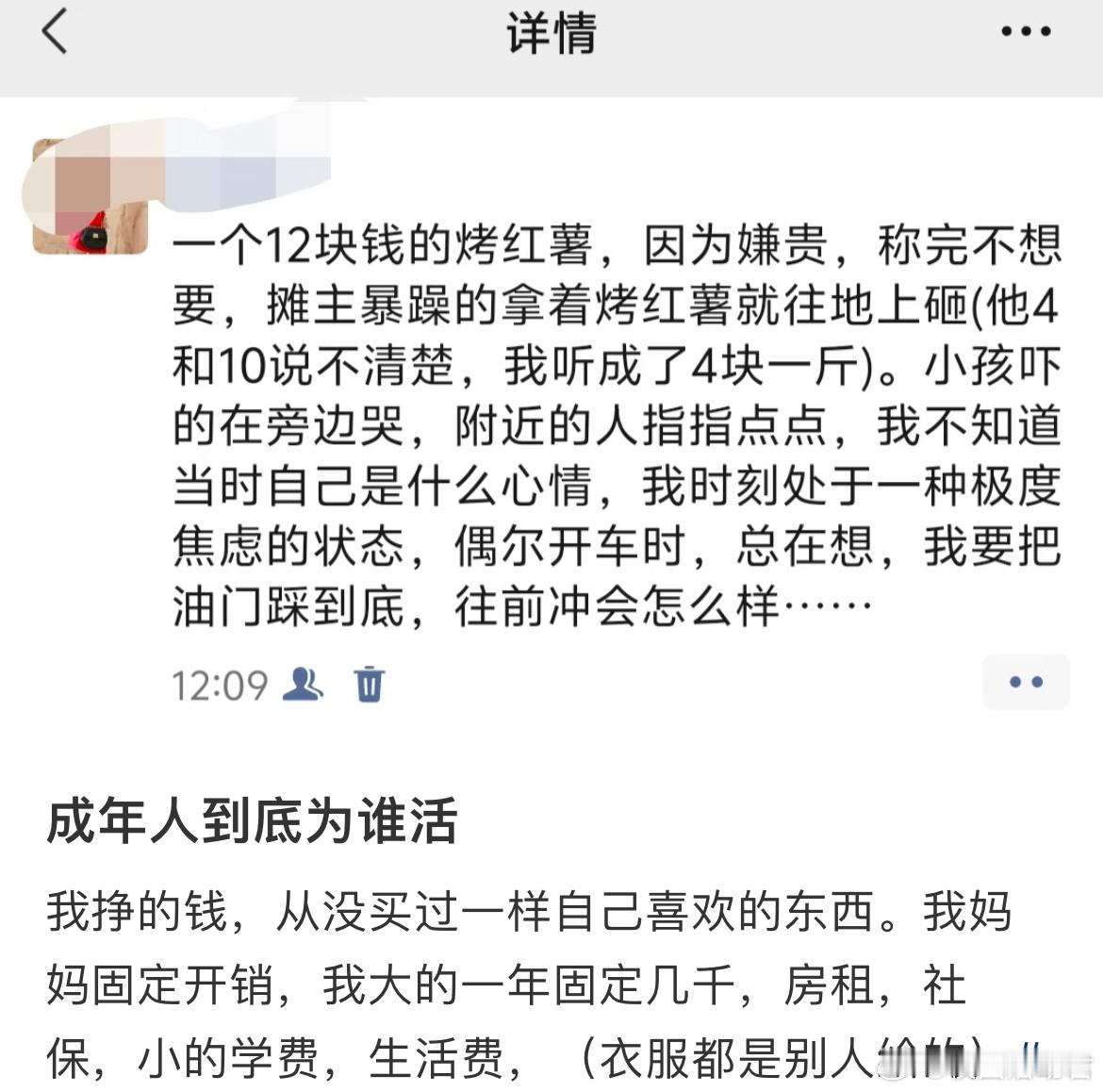
![马上2026年了,还有人说这样的话。[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61814260872508460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