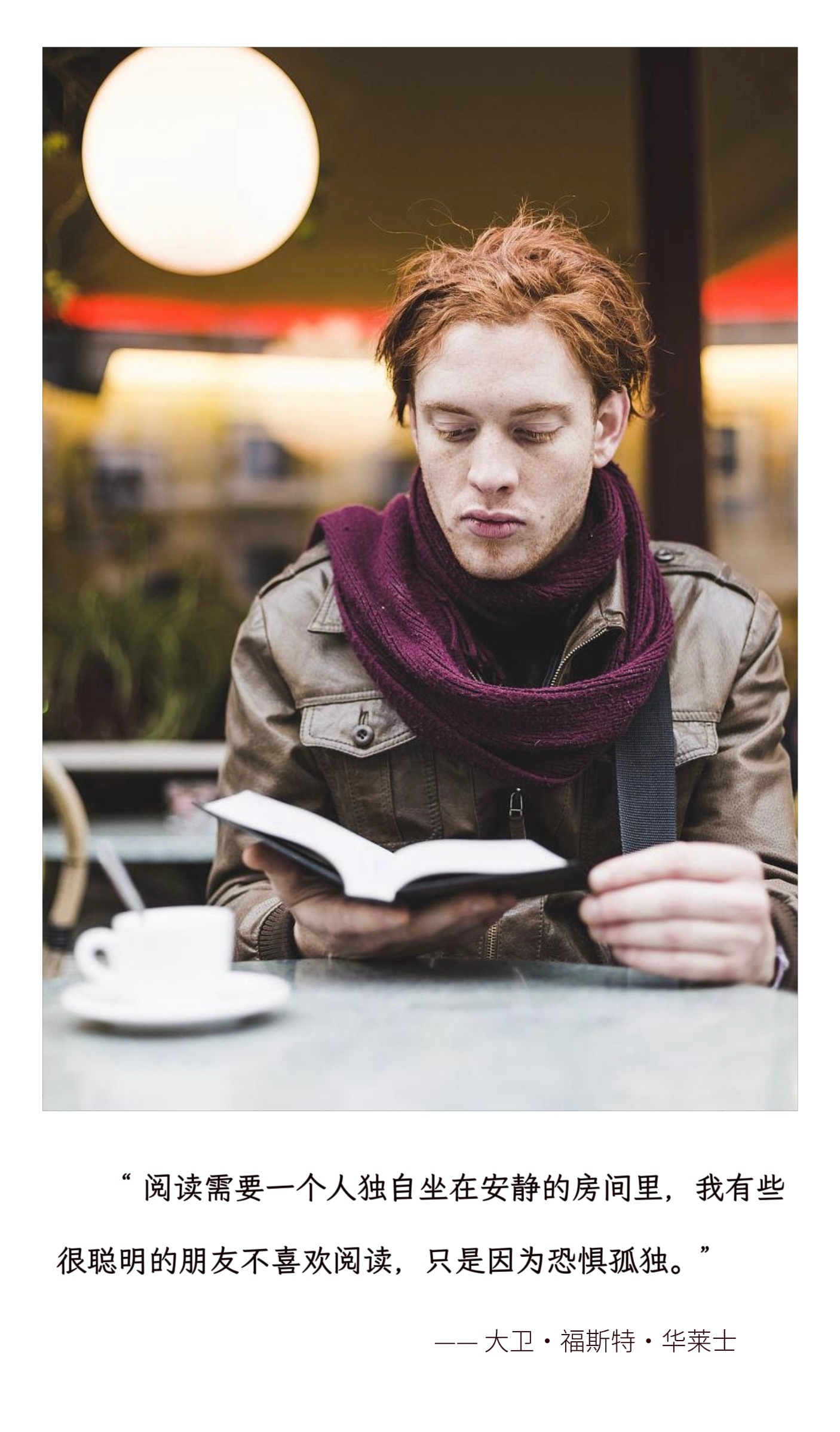【酒吧里的“读书表演”,是在消费知识,还是消费自己?】 (摘自·文艺圈 12月7日 「 文化周报 」 ) 一个男人走进酒吧,在吧台前坐下,点一杯酒,从帆布包里取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然后埋头阅读。在TikTok和Instagram上,这种在公共场合阅读的行为被称为“表演型阅读”:把书当作配饰,随身携带大部头作品,用以吸引潜在的约会对象。当其他人都戴着降噪耳机刷新社交媒体时,表演型阅读似乎提供了某种智识上的优越感。 这种指认方式多少显得武断,但社交媒体期望将任何情绪放大,“表演型阅读”已经扎根于大众想象之中。在美国语境下,特朗普的竞选宣言(我爱那些读书不多的人!)甚至为这种指认方式提供了政治正义:坚持阅读很难,但指责这种行为是装腔作势总归容易得多。然而,仅仅十年前,约翰·沃特斯的名言“如果你跟某人回家,发现他家里没有书,就别和他上床”还被印在帆布包上。 文化规范固然是一种匿名的现实,但它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新语词是诊疗新生的文化现象,还是照亮了早已存在的事实? 社交媒体上对阅读的符号化始于2021年,当时名人组织的读书会迎来井喷,而TikTok上致力于推广与讨论流行小说的“BookTok”也把书籍变成了一种“配饰”。杂志《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莎拉·马纳维斯(Sarah Manavis)曾写道,BookTok “本质上就是表演性的”,那些“潮书”之所以爆红,并非因为文本的质量,而是它们象征着一种“愈发时髦的、伪知识分子式的审美”。作为某种姿态性的反拨,阅读大部头自然携带着更多的智识资源。放回中文语境,伍迪·艾伦、“高智感”和“知识分子穿搭”的搜索量暴涨也就不难理解了。 阅读这一行为的审美化,只是商品化进程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在经济意义上并无任何特殊性。文化左派和保守主义者一度联合起来批判新技术的侵扰,在雷蒙·威廉斯的巨著《文化与社会》中,他将“文化”作为最高上诉法庭而批评文化的商品化、庸俗化以及对人们集体生活方式的败坏。 新媒体的整合功能将旧媒介推向墓碑,摄影、音乐和电影纷纷坍缩为图标。直到今天,阅读仍然是社交媒体唯一无法复制的文化形式,纸张的厚重感是无法模拟的。然而,据《卫报》统计,近五年世界范围内的纸质书销量不降反增,英国图书馆的人流量也逐年增长,这对文化唯物主义者而言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即便在个体主义盛行的主流社会中,对真实的迷恋和苛求也迫使人们不断审视自身,在场感需要持续不断的设计。“美德信号”(virtue signalling)在2010年代中期变得备受厌恶,用简单的文字进行政治声援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姿态,真诚的表达反而被视为别有所图——这是消费逻辑的副产品,所有不讽刺、不解构的内容都被指认为表演,与此一同发生的,是美国公民识字率的下降、高等教育对人文学科的削减和人工智能对时间的侵占,老生常谈的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问题似乎已经无法唤起公众的警惕。 至于前文提到的《无尽的玩笑》,或许是当下最适配“表演型阅读”的文本,作者在其中描绘了一个政治动荡、企业割据、自然环境濒临崩溃的反乌托邦世界,而小说中的人物几乎对此毫无察觉,他们通过酒精、高强度健身和过度的媒体消费逃避真实世界,这不啻为一种共享的孤独。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华莱士说“阅读需要一个人独自坐在安静的房间里,我有些很聪明的朋友不喜欢阅读,只是因为恐惧孤独。”而互联网恰恰最擅长驱散这种恐惧——不断划动屏幕,即便不能消解孤独,也足够以拖代变,尽量延后。他担心在一个充斥着强感官刺激的时代,阅读将会失去自身的道德价值。一个并不遥远的问题是:如果在公共场合阅读会遭人嘲笑,我们需要回家锁上房门偷偷读书吗? 网页链接 在酒吧读书,是装腔作势吗?丨文化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