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晚上,钱学森从实验室忙碌回到家,和家人共进晚餐,味觉敏感的他感觉到食物味道有点不对,警卫拿去化验后大吃一惊,竟有人在食物里下了毒。 1964年的那个傍晚,钱学森家里的餐桌上气氛陡然凝固,此时距离他在罗布泊见证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没剩几个月了,但死亡的威胁并不在戈壁滩,反而率先爬上了北京寓所的饭桌,这并不是他在海外遭遇软禁的续集,而是一场真实发生在北京核心地带的致命暗战。 当那盘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端上来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死神就潜伏在油脂与酱油的香气之间,钱学森并不是一个美食家,但常年与危险化学品和高精尖数据打交道的经历,让他对此有着近乎直觉的敏感。 刚把肉夹到鼻下,那股平日里熟悉的肉香中,似乎混入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怪味,那不仅仅是所谓的“馊”更夹杂着某种难以名状的苦涩与金属气息,这与昨天、前天的味道截然不同“别吃,不对劲”。 这句话瞬间打破了家庭晚餐的温馨,警卫员几乎是冲过来端走了盘子,直奔食品化验室,要知道,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周恩来特意指派了有着丰富食品检验经验的段恩润负责他的饮食,所有的食材理论上都是“绝对干净”的。 然而,显微镜和试剂给出的结果让所有人都背脊发凉:剧毒,这并不是食材源头的问题,毒是在饭菜出锅后的那个瞬间投进去的,安保人员顺藤摸瓜,目光锁定在了负责送菜的那对爷孙身上。 那位看似老实巴交、这几日风雨无阻推着板车送新鲜蔬菜的老头,当天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把视线拉回后厨的那短短几分钟,一场精心设计的“诛心”戏码刚刚落幕,事实上,敌特分子早就盯上了这条供应链。 那位平日里与钱学森夫妇相处融洽、甚至被视为亲人的老送菜工,几天前在半路遭遇了此生最大的噩梦:一名陌生男子用枪顶住了他孙子的脑门,对于特务而言,无论是在大洋彼岸还是在皇城根下,只要能达成目的,没有什么人性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老人在孙子性命和恩人安危之间崩溃了,那包毒药是他流着泪,趁着大厨和蒋英女士忙碌的空档,颤抖着手撒进去并用筷子搅拌的,但他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当调查人员在那座破败的荒庙里找到他们时,只看到了两具冰冷的尸体,老头和他的孙儿都被灭口了。 对于藏在暗处的间谍来说,只有死人才永远不会供出幕后主使,这件事给原本就森严的安保工作再次敲响了警钟,从那之后,钱家的厨房变成了真正的“实验室”这不是夸张,是真正配上了从德国进口的专业显微镜和电冰箱。 所有的食材采购渠道被彻底清洗,换成了清一色的“自己人”每一颗白菜、每一块猪肉,都要经过清洗、切样,放在高倍显微镜下寻找是否存在异常晶体,留样观察24小时无碍后才能处理。 这种连开国元帅都未曾享有的“待遇”折射出的是国家对于这位科学巨匠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其实,这种如影随形的死亡阴影,早在十多年前大洋彼岸的那个码头上就埋下了伏笔,当钱学森还在加州理工拿着5万美元年薪、住着花园洋房时,他眼里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但当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初现,他决定带上妻子蒋英回国时,美国人却让他见识了什么叫“科学家的国界”那位海军次长金贝尔曾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宁可毙了也不能放。 这绝非一句恐吓,回国之路本身就是一场特工与反特工的较量,想当年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靠岸香港的那一刻,码头到罗湖海关仅仅三百米的距离,充满了让人窒息的压迫感,外交部为了骗过眼线,不得不伪造了一封署名“父亲”的家书,告诫他此时万万不可下船乱跑。 在那段碎石路上,一家人手紧紧握在一起,耳边除了船笛,全是这一家人心跳的声音,更早之前,为了消磨他的意志,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把他扔进特米诺岛的监狱,那是精神上的凌迟:探照灯24小时高强度照射,守卫每隔十分钟就用沉重的皮靴踢门查房。 剥夺睡眠、没收了那14磅重的珍贵笔记,半个月的时间,在那座孤岛上,一个意气风发的顶尖学者生生被折磨得失声、暴瘦,甚至一度不仅身体垮了,连说话的能力都暂时丧失,如果没有妻子蒋英没日没夜熬汤照料,没有加州理工同事凑出的那1.5万美金保释金。 钱学森或许真就折在那个黑暗的牢笼里了,即便是保释后的五年,特工的车也像尾巴一样时刻黏在他家门口,他就是在那样的绝境下,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心理素质,或许正是他在1964年那个投毒夜晚能如此冷静分析气味异样的原因。 1964年10月16日,也就是投毒风波后的同一年,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三年后的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再到1970年4月,伴随着长征火箭的轰鸣,“东方红一号”让来自中国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宇宙。 信息来源:纪念钱学森归国七十周年,这场展览在京举行 2025-09-18 18:43·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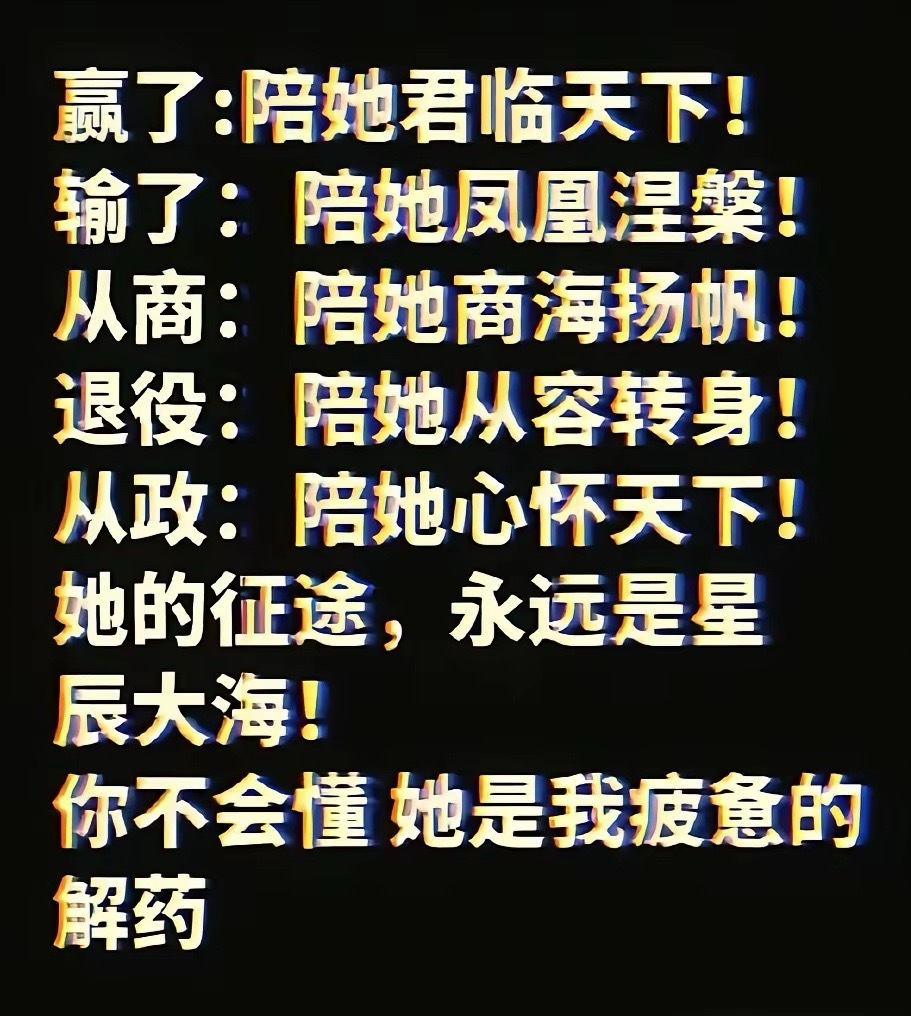



山风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