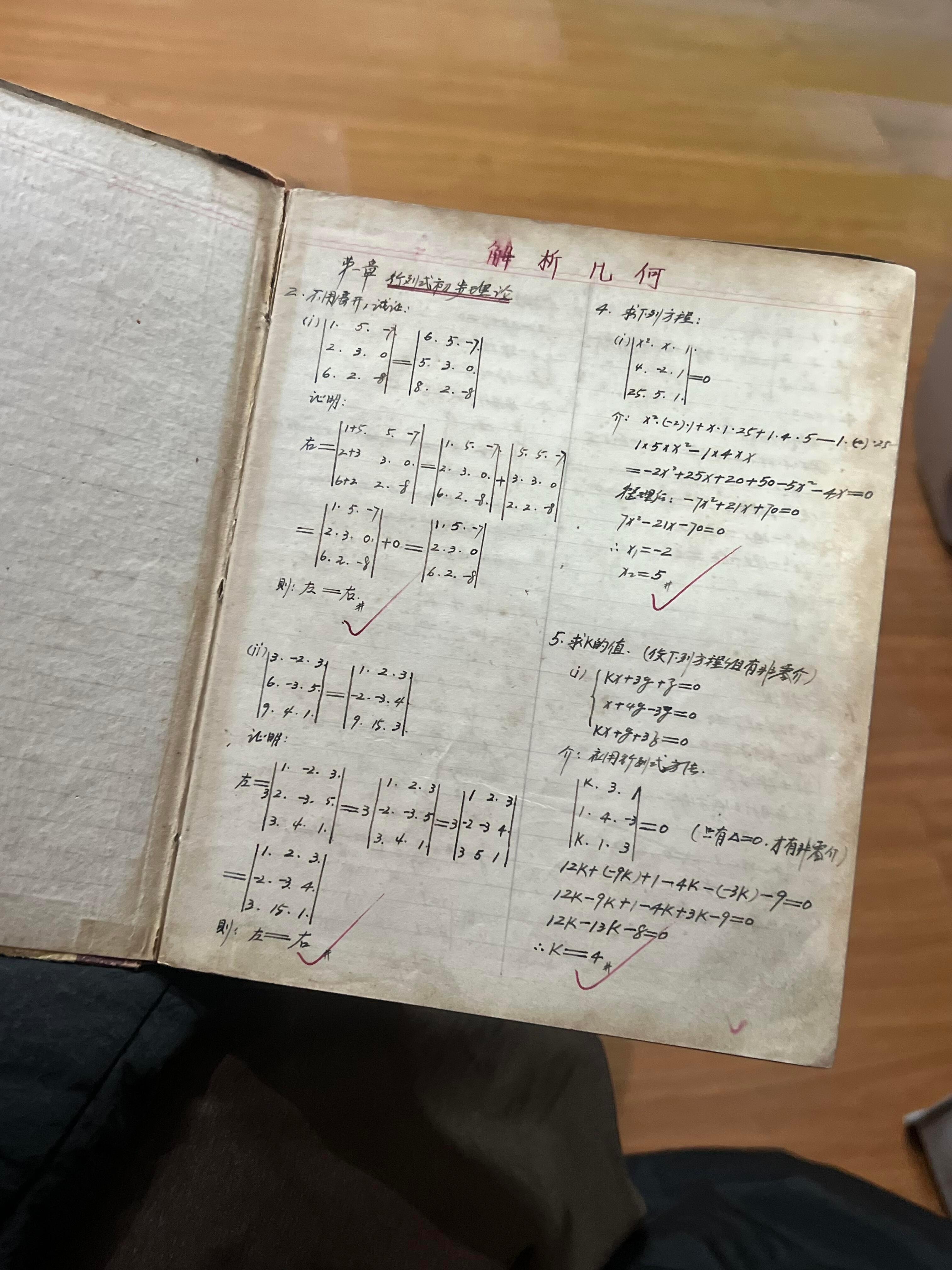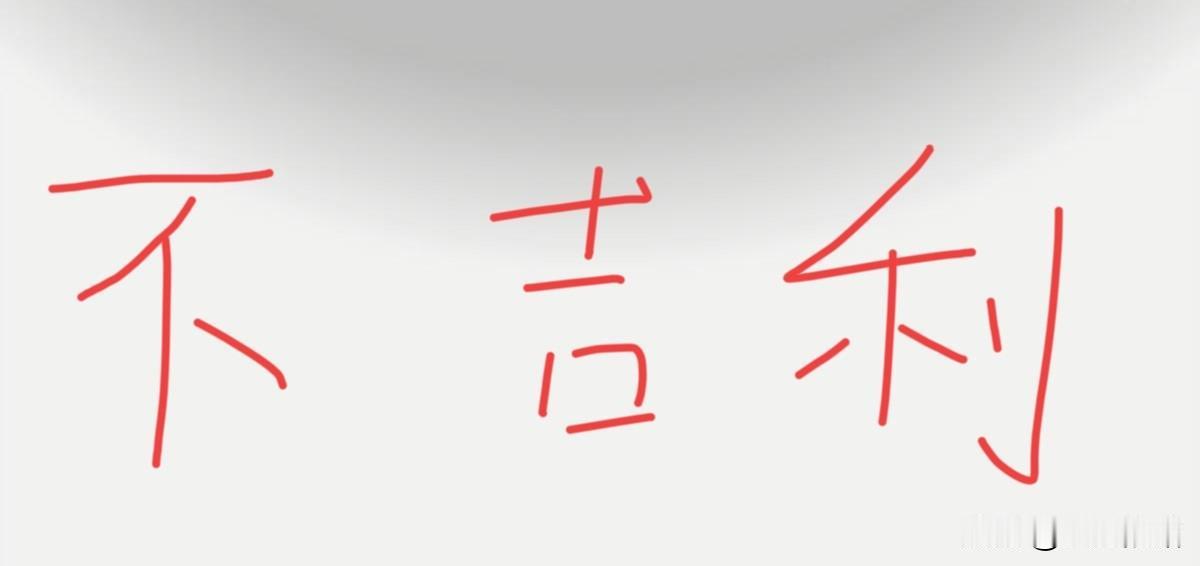1900年,连生两女的朱环佩再次怀孕,丈夫:“再生女儿我就纳妾,”谁料,生下来还是女儿,就在朱环佩伤心落泪时,婆婆却说:“别哭,我有办法! 徐德生在城里钱庄做账房,是那种一眼看去就很“体面”的人。长衫永远浆洗得笔挺,袖口不见一丝毛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 算盘拨得不急不慢,账目写得清清楚楚,连掌柜都说他“稳当”。他说话从不高声,遇事先拱手、再开口,仿佛嗓音大一点,都会坏了分寸。 可这份体面,一到族里修谱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单薄。 每逢清明或冬至,徐氏宗祠里香火缭绕,男人们围坐在长桌旁,桌上摊着厚厚的族谱。 谁家新添了男丁,谁家的名字就被郑重地添上,毛笔落纸时,旁边总有人笑着恭喜:“香火不断,好福气。” 轮到徐德生时,他总是提前坐直身子,双手放在膝上,背脊挺得笔直,像在钱庄柜台前等人对账一样端正。 可族谱翻到他那一页,总是很快就过去了。纸页翻动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像在他耳边敲了一记闷锣。 他脸上维持着一贯的平静,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毫不在意,可镜片后的眼神,却常常暗了几分,脸色也比平日更白。 席间总有长辈不经意似的开口:“德生啊,账算得再好,家里没个儿子,总是缺点什么。”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字字落在他心上。 他只能陪着笑,点头应声,不敢反驳。有人还会接一句:“女人家,再能干也是别人家的,早晚要嫁出去。” 这句话像一条规矩,挂在宗祠的梁上,年年回响。 徐德生心里明白,在族人眼里,他在钱庄再受器重,也比不过谁家添了个男婴。 他回家时,脚步总比平日慢些,进门前还要理一理衣襟,仿佛只要外表够体面,心里的那点空缺,就不会被人看见。 朱环佩心里明白。她不识字,嫁进徐家前,在娘家只是个会纺线、会做针线的姑娘。生了头胎女儿,婆婆只是叹气。 二胎还是女儿,婆婆沉默了好几天。到了第三次怀孕,徐德生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要是再生女儿……我就纳妾吧。总得给祖宗一个交代。” 那一夜,朱环佩背对着丈夫,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她不是怕纳妾,是怕自己这一生,就这样被“没生儿子”这四个字定了罪。 孩子出生那天,雨下得很大。稳婆抱着襁褓出来,脸色有些为难,低声说:“是个小姐。” 朱环佩只觉得眼前一黑,耳边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她转过脸,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既是委屈,也是绝望。她甚至不敢看丈夫的表情。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婆婆忽然开口了。 “别哭,”老太太的声音不高,却很稳,“我有办法。” 朱环佩愣住了。她以为婆婆要干脆给丈夫纳妾。可婆婆慢慢走到床边,看了看襁褓里的孩子,又看了看朱环佩,语气出奇地笃定。 “谁说女子不能撑起门楣?”婆婆说,“从今天起,你教这三个孩子读书、写字、学算账。” 朱环佩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女子读书?那可是少见得很的事。 婆婆继续说:“徐家靠的不是田产,是账目,是脑子。男人能学的,女人也能学。她们若有本事,谁还敢看不起?” 那一年起,徐家的后院多了一张旧木桌,几本从旧书铺淘来的蒙学书。朱环佩自己不识字,就在旁边一笔一画地看着,陪着女儿们念。 大女儿慎仪性子稳,算盘打得飞快;二女儿慎和心细手巧,常把书里的人体图画描得清清楚楚;最小的慎言,话不多,却对数字格外敏感。 邻里最初只是当笑话看:“女孩子念书?早晚还不是嫁人。” 可几年下来,风向慢慢变了。 大女儿出嫁时,对方是城里绸缎庄的少东家。成亲后,账目一乱,掌柜们头疼不已,是她站出来,一笔一笔理清流水,硬是把亏损的铺子救了回来。绸缎庄里从此没人敢轻看这位少奶奶。 二女儿后来进了教会办的医院,学医护。白大褂一穿,写病历、配药、照料病人,样样利索。有人说她“不守妇道”,她却用一封封工整的书信,换来了家里源源不断的银元。 最小的慎言,毕业后回到绍兴,在女子学堂教算学。她站在讲台上,粉笔敲着黑板,底下坐着一排排和她当年一样怯生生的女孩。 族里渐渐没人再提“纳妾”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