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看到有个老大爷在门口外面卖鸡蛋。老大爷一看到我,赶忙问:要买点鸡蛋吗?这是我自己家养的鸡下的土鸡蛋。 我停下脚步,往竹篮里瞅了瞅,鸡蛋个头不大,壳上有深褐浅褐的斑点,像撒了把碎芝麻。 大爷见我没应声,又往前凑了凑,竹篮把手磨得发亮,边缘缠着圈旧布条,看着有些年头了。 “刚从鸡窝里拾出来的,”他用袖口擦了擦额头,“早上五点多就往这儿赶,怕来晚了占不着好位置。” 我摸了摸口袋,现金只有三块多,手机昨晚忘了充电,屏幕暗着开不了机,当时我心里还嘀咕,这年头谁还只收现金啊? “大爷,您这儿能扫码不?我没带够现金。”我举了举黑屏的手机,有点不好意思。 大爷愣了一下,摆摆手,手背在蓝布褂子上蹭了蹭:“不会弄那玩意儿,我老婆子走得早,孩子们在外地,就我跟这些鸡作伴,扫码啥的学不会。” 他说着叹了口气,蹲下身把竹篮往台阶里挪了挪,躲开被风掀起的塑料袋,“要不你先拿几个去吃?不值当特地跑一趟换钱,下次路过再给就行。” 我正想说不用,眼角余光瞥见他从竹篮底下拽出个印着小猫图案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半袋猫粮,捏了一小撮撒在脚边的花坛沿上。 没过几秒,三只瘦得能看见肋骨的流浪猫从冬青丛里钻出来,弓着背蹭他的裤腿,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呼噜声。 “这些小家伙,天天在这儿等我,”大爷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我老婆子活着的时候最喜欢猫,走之前还念叨,说楼下花坛里的猫崽没人喂,让我别忘了。” 他用粗糙的手指挠了挠最胖那只猫的下巴,猫舒服得眯起眼,尾巴卷住他的脚踝,“我卖鸡蛋不为挣钱,就想每天出来透透气,顺便给它们带点吃的,就当……就当老婆子还在,看着我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刚才还觉得他固执不肯学扫码,这会儿倒觉得那竹篮里的鸡蛋,像是盛着比现金更沉的东西。 “大爷,我去超市服务台试试能不能换点现金,您等我会儿。”我拎着购物袋往超市里跑,服务台的小姑娘挺好,用我的手机扫了她的码,换了五十块现金。 跑出来时,大爷正把一个鸡蛋轻轻放在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手里,小姑娘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他又找了两块回去,“够了够了,三个鸡蛋哪用这么多。” 我把五十块递过去:“大爷,来两斤鸡蛋。”他称的时候手抖了抖,多抓了三个塞进来,“送你的,刚下的,给孩子吃。” 我没推辞,蹲下身跟猫玩了会儿,最瘦的那只胆子小,老躲在他身后,只露出双圆溜溜的眼睛瞅我。 “明天我还来,”大爷收拾着摊子,把猫粮袋仔细折好塞进布兜,“这些小家伙认人,我不来,它们该饿肚子了。” 回家路上,我把鸡蛋小心放在车筐里,风从耳边吹过,带着点青草和泥土的味儿,跟大爷身上的味道有点像。 晚上给鸡蛋拍照发了朋友圈,配文说“今天买到了会‘讲故事’的鸡蛋”,评论里有邻居问在哪儿买的,我说超市门口,明天早上七点。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到超市门口时,大爷已经在了,竹篮旁边围了好几个邻居,有提着菜篮的阿姨,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都在买鸡蛋,说要“支持大爷喂猫”。 大爷忙得满头汗,却笑得比昨天更开心,一个劲儿说“够了够了,吃不完别买这么多”,手里的秤杆却压得弯弯的。 后来我每周都会去买一次鸡蛋,有时是我,有时是我爱人,去的时候总看见大爷蹲在花坛边喂猫,阳光照在他和猫身上,毛茸茸的,暖烘烘的。 有次我问他,天天这么累,图啥呢?他指了指天上的云,慢悠悠地说:“你看那云,飘着飘着就散了,可人心里的念想,不散,就像这鸡蛋,看着普普通通,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劲儿。” 现在超市门口的流浪猫胖了不少,胆子也大了,见人就喵喵叫,有只三花猫还被邻居收养了,取名叫“鸡蛋”。 我偶尔还会想起第一次见大爷的样子,手背皴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草屑,可他蹲下来喂猫时,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 原来这世上的暖,不一定非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有时就是一个鸡蛋的温度,一句“下次再给”的信任,和一个老人蹲在花坛边,给流浪猫挠下巴的温柔。 就像今天早上,我又去买鸡蛋,大爷从竹篮底下摸出个小铁盒,里面是晒干的猫薄荷,非要塞给我,说“拿回去给‘鸡蛋’闻闻,它肯定喜欢”,阳光正好,照得鸡蛋壳上的泥土,都闪着光。
今天超市买完东西出来,看到有个老大爷在门口外面卖鸡蛋。老大爷一看到我,赶忙问:要
卓君直率
2026-01-02 16:42:02
0
阅读: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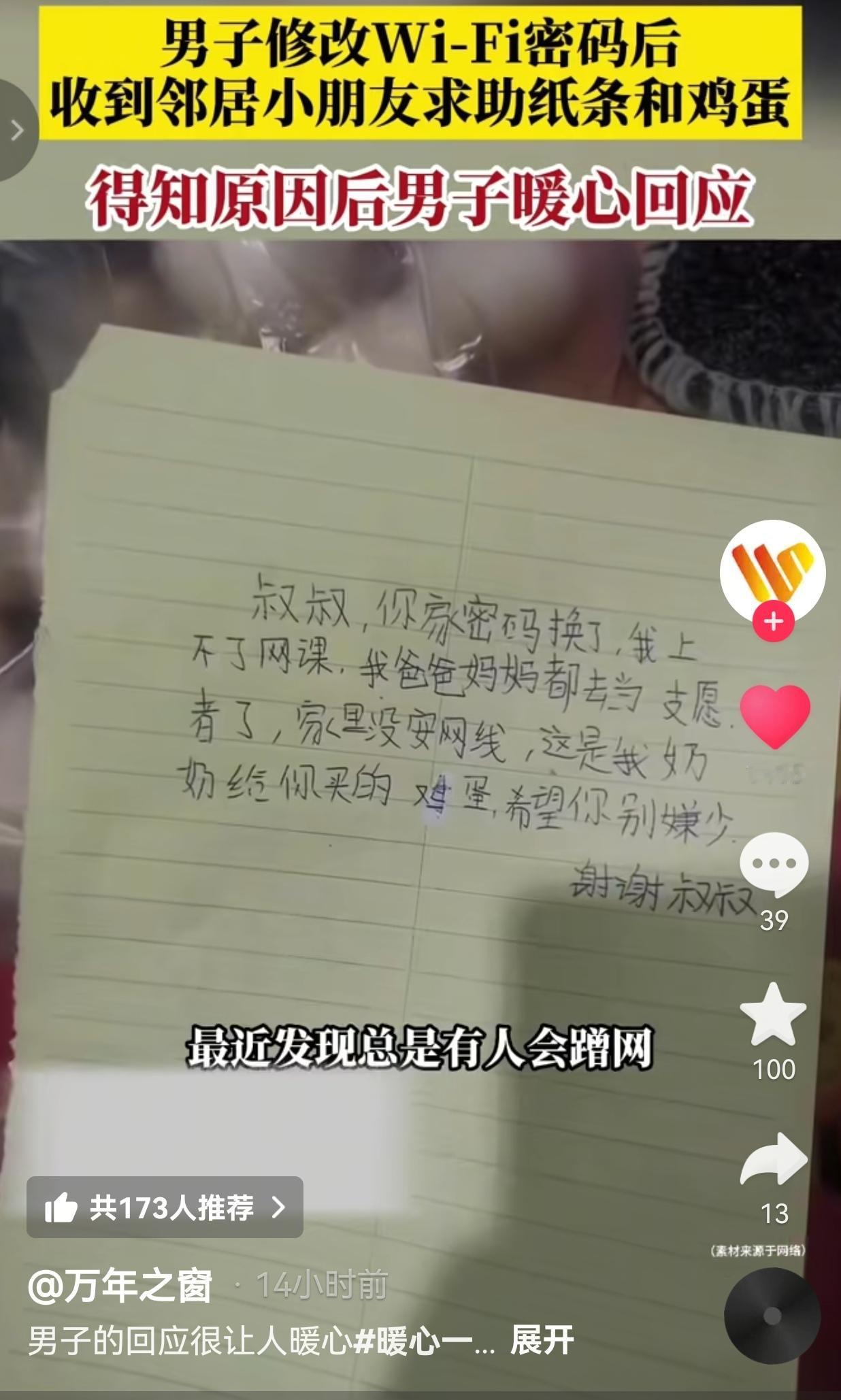








一剑客
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