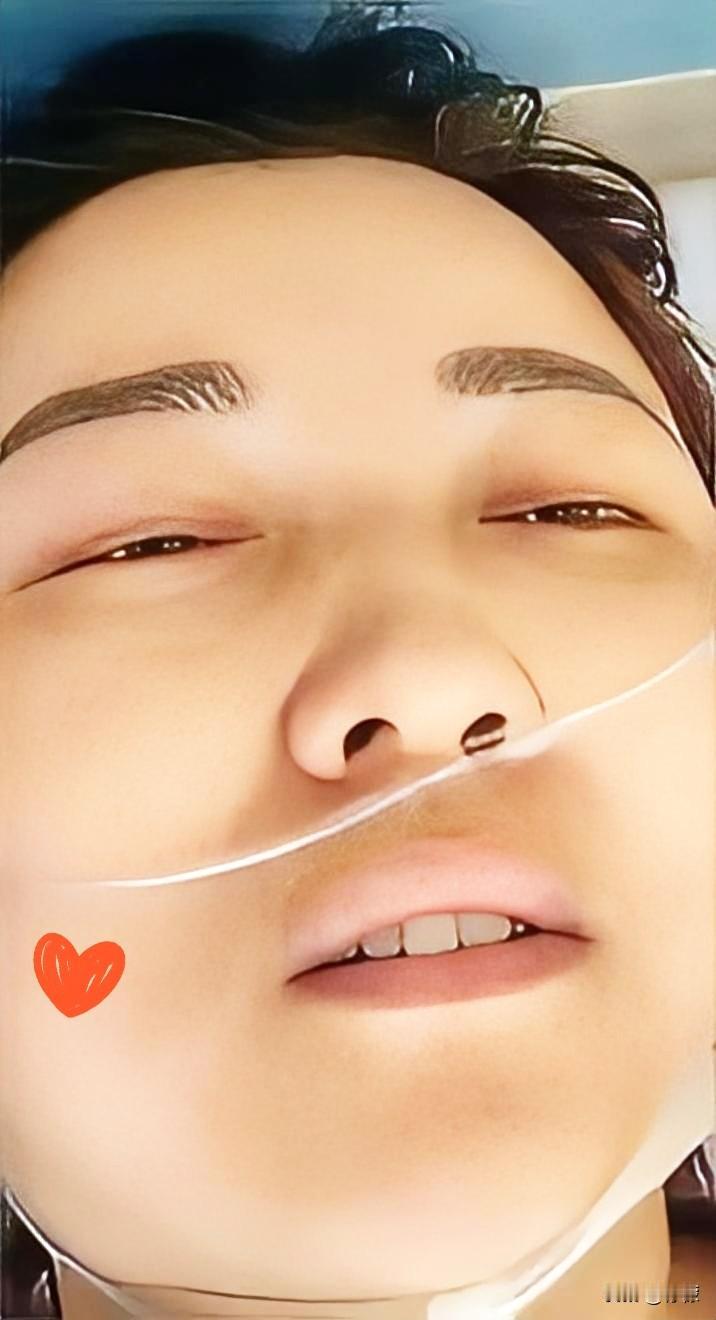[微风]15岁富家女逃婚去延安,死活不当官太太,却在1978年的德国波恩,哭得几近昏厥打镇定剂才停。 1978年的南洋,廖冰这个名字代表着绸缎、洋楼和取之不尽的财富,作为富商家里备受宠爱的“千金小姐”,她本该按部就班地当个相夫教子的贵太太。 但这个姑娘骨头里大概天生就少了一根“顺从”的神经,12岁那年碰上九一八事变,她就能甚至顶着英国殖民者的审讯,在街头喊出“爱国无罪”。 到了15岁,家里刚把门当户对的婚事摆上台面,她反手就卷了几块银元,那是真的视金山银山如粪土,提着行李就消失在了南洋。 她那双本该戴玉镯的手,这一路又是扒火车又是徒步,早就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原来的绫罗绸缎最后变成了陕北公学的粗布军装。 1938年夏天,21岁的廖冰站在了延安的黄土地上,因为生得细皮嫩肉,一口带着南洋味儿的软糯口音,不知情的人总以为她是来这儿“体验生活”的大小姐。 甚至组织上见她读过中国女子大学,人又灵气,好心想给她牵线搭桥,介绍几位屡立战功的指挥员,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安稳日子”。 若是为了荣华富贵,她何必逃离南洋?廖冰当时就急红了眼,梗着脖子把“好意”顶了回去,那话说是掷地有声:“我来延安是救图存亡的,不是来当金丝雀、做官太太的!” 这股子倔劲儿不光在嘴上,更在她那双甚至没摸过锄头的手上,她不去机关坐办公室,偏要往最苦的地方钻。 在物资匮乏的兵工厂,她跟着老师傅学造子弹,指缝里的火药味洗了又染,胳膊被飞溅的火星烫伤,随手抹把草药继续干;冬天挤在冷炕上,夏天去开荒,那个娇滴滴的大小姐早就死在了南洋,活在延安的是一个手掌磨出厚茧的战士。 后来哪怕是调去《新中华报》当编辑,这双手也没闲着,到了1942年的晋西北根据地,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她这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反身成了高家村的支部书记。 没有纸印报纸,她就领着人上山砍竹子,硬是土法上马建起造纸厂;前线缺衣少食,她带着村里妇女纳鞋底、做军鞋,甚至还办起了新闻干部训练班,那个年代的“小姐”脾气硬是被战火锻炼成了钢铁般的意志。 可命运这东西,最喜欢在人最坚定的时候下绊子。 因为特殊的华侨背景,加上那股子“不愿做官太太”的傲气,建国后的廖冰在那个特殊年代并没有得到优待,反而遭受了一系列的磨难。 她被下放到农场,曾经造过子弹、办过报纸、写过文章的手,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挥舞着锄头镰刀,有人劝她服个软,去找找当年那些如今身居高位的老战友、老熟人,哪怕只是叙叙旧,境遇也大不相同。 但她愣是一次都没去,在她看来,既然当年没选那条当“太太”的路,如今为了这点磨难去低头求人,那当年的血便白流了,那些屈辱和非议,她全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只有深夜梦回延安战火时,泪水才会打湿枕巾。 直到1978年,她与波恩的那次偶遇,街头上,廖冰撞见了一位曾在兵工厂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两双手颤抖着握在一起,本来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可随着话匣子打开,残酷的现实像重锤一样砸了下来。 老战友告诉她,当年和她们一起熬夜造子弹的姐妹,有的早已把热血洒在了抗日前线,成了黄土垄中的一捧白骨;而另一些活下来的,在后来的风雨飘摇中没能熬住。 最讽刺的是,她得知当年自己没日没夜亲手造出的子弹,确确实实帮助部队打赢了仗,立下了赫赫战功,成就了无数人的坦途,而她自己却因为那份近乎洁癖的“清高”和“出身”,在大半辈子里蹉跎受辱。 这一刻,她感到了无助和悲怆,她蹲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哭的根本不是自己吃过的那些苦,也不是后悔当年逃离豪门的决定。 她崩溃的是那些明明有着同样炽热理想的同伴,没能等到这春暖花开的一天;是那份毫无保留的赤诚付出,最后换来的竟是如此沉重的误解。 那一针镇定剂能止住她身体的抽搐,却抚不平那代人心中的伤痕,在那个波澜壮阔又充满遗憾的时代里,廖冰用一生的颠沛流离给“信仰”二字做了最昂贵、也最沉痛的证明,没人知道那天醒来后她看着窗外的莱茵河在想什么,或许,依然是那片遥远而贫瘠的黄土高坡。 信源:吕梁新闻网 廖冰:战斗在新闻战线的一员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