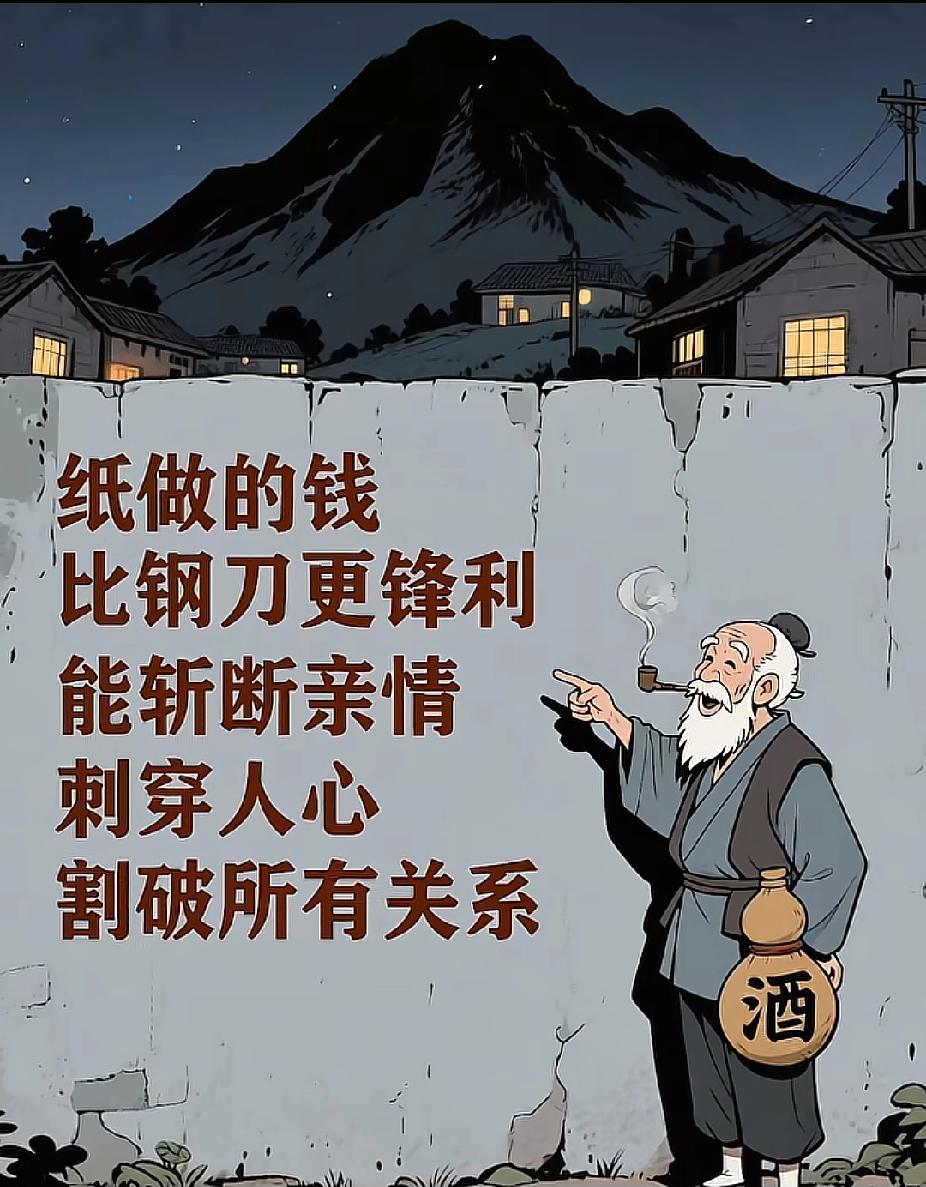大伯有钱有势,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一次也没有接,后来他又发了消息,我也装作没看见,只因为前年我父亲去世,他竟然一个关心的电话都没有。手机在桌上震第三次时,我正擦着父亲生前常坐的藤椅。屏幕上 “大伯” 两个字亮着,我瞥了眼,伸手按灭了。 藤椅扶手被磨得发亮,木纹里卡着些细灰,我拿抹布来回蹭,蹭着蹭着就想起前年那个雪夜。父亲走的时候窗外飘着雪,我蹲在灵堂前烧纸,火光照着墙上他和大伯年轻时的合照——俩小伙子穿着军大衣,站在长白山的雪地里,笑得露出白牙。那时候他们是真亲啊,听妈说,大伯当年为了供父亲读书,在砖窑厂扛了三年砖,肩膀磨出的茧子比铜钱还厚。可后来怎么就成这样了呢?父亲病重那半年,天天望着门口念叨“哥咋还不来看我”,我给大伯打电话,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国外”,堂哥说大伯忙,忙着上市忙着签合同,忙得连亲弟弟的死活都顾不上了。 手机又震,这次是条短信,大伯发来的:“小宇,我在你家楼下,带了样你爸的东西,见一面吧。”我盯着屏幕发愣,手指悬在“删除”键上,终究没按下去。楼下传来关车门的声音,我扒着窗户往下看,大伯穿件黑色羽绒服,头发白了大半,背好像也驼了点,手里拎着个旧木盒子,站在单元门口搓手,跟电视里那个前呼后拥的大老板判若两人。 开门时,他眼睛直勾勾盯着客厅墙上父亲的遗像,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侧身让他进来,没倒茶,也没说话。他把木盒子放在茶几上,打开,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还有个褪色的红布包。“这些是你爸写给我的信,从他上大学到后来……”他声音有点哑,“红布包里是当年我欠的债条,你爸偷偷帮我还的,我去年才知道。” 我拿起最上面的信,是父亲读大学时写的:“哥,你寄的钱收到了,够买过冬的棉鞋了。你在砖窑厂别太拼命,腰不好就歇着,等我毕业挣钱了,咱就把妈接来城里……”后面的字被水洇了,晕成一片模糊。红布包里的债条皱巴巴的,上面的数字让我心口一紧——那是笔能压垮普通家庭的巨款,父亲当年工资才多少?他是怎么攒出来的? “你爸走的前三天,给我打过电话。”大伯突然开口,眼圈红了,“他说‘哥,我知道你难,那些债别放在心上,咱兄弟俩,从来不分你我’。我那时候正在外地谈一个项目,对方是债主的亲戚,我得盯着把债彻底清了,想着清完债就回去陪他,谁知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录音笔,“这是他最后给我打的电话,我一直没敢听。” 按下播放键,父亲的声音传出来,带着病后的虚弱,却还是笑着:“哥,等你忙完了,咱还像小时候那样,去后山摘酸枣,我记得你最爱吃……”声音突然断了,接着是大伯压抑的哭声。我攥着信的手开始抖,原来父亲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大伯不是忙,是在偷偷扛着债,怕牵连家人;他知道大伯不来看他,是不想让他跟着操心;他甚至在生命最后一刻,还在替大伯着想。 “小宇,”大伯看着我,眼里全是愧疚,“是我混蛋,我以为把债还了,把日子过好了,就能弥补你爸,却忘了他最想要的不是钱,是我这个哥在身边。”他从包里拿出个存折,“这是拆迁款,写的你的名字。还有,你堂妹下个月结婚,我想……想请你当证婚人,你爸以前总说,你是咱老李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我看着桌上的信,看着录音笔,看着大伯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兄弟啊,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拿起存折塞回他手里,又把红布包和信小心收进木盒:“拆迁款我自己去领,证婚人我当。”大伯猛地抬头,眼里闪着光。“不过,”我补充道,“以后别总说忙,有空多来看看我爸的照片,他肯定想你。” 大伯用力点头,眼泪掉在木盒子上,砸出一小片湿痕。我把他送到楼下,看着他坐进车里,车开出去老远,他还从后窗朝我挥手。阳光照在藤椅上,暖洋洋的,我坐上去,好像父亲还在我身后,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就对了,咱老李家的人,心不能散。”
“冲动是魔鬼!”上海,女子在二楼冲洗窗台,脏水漏到一楼阳台,遭邻居质问,女子怼一
【7评论】【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