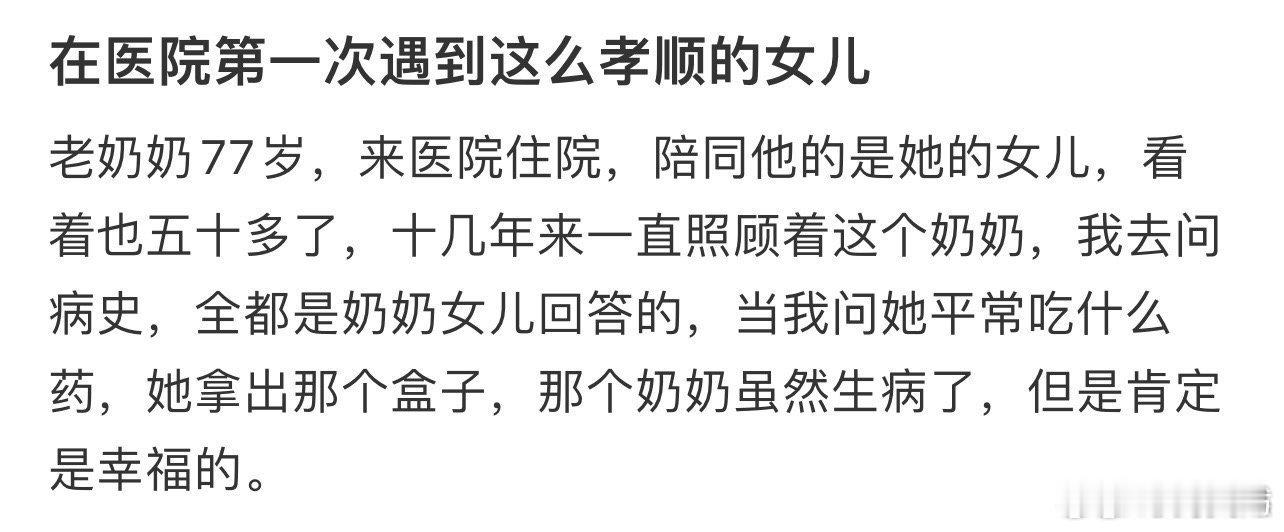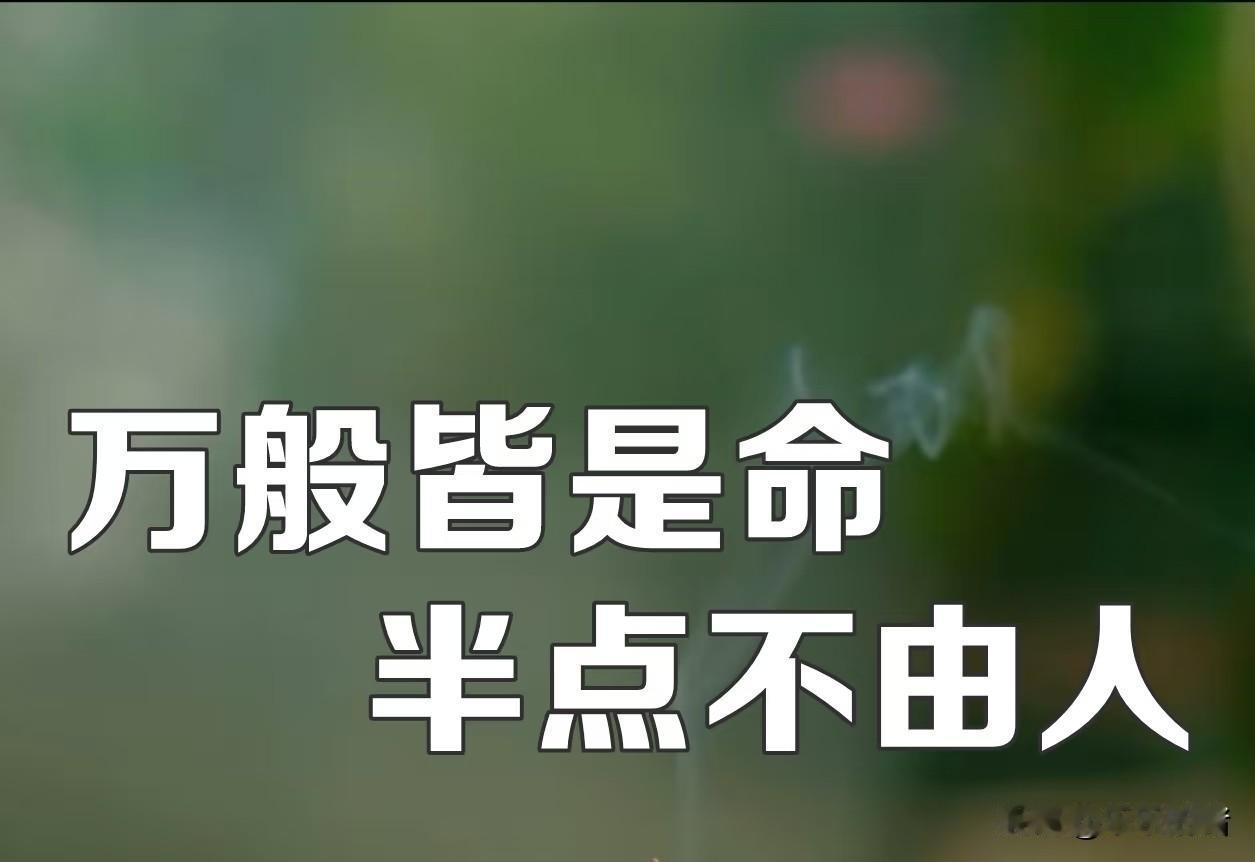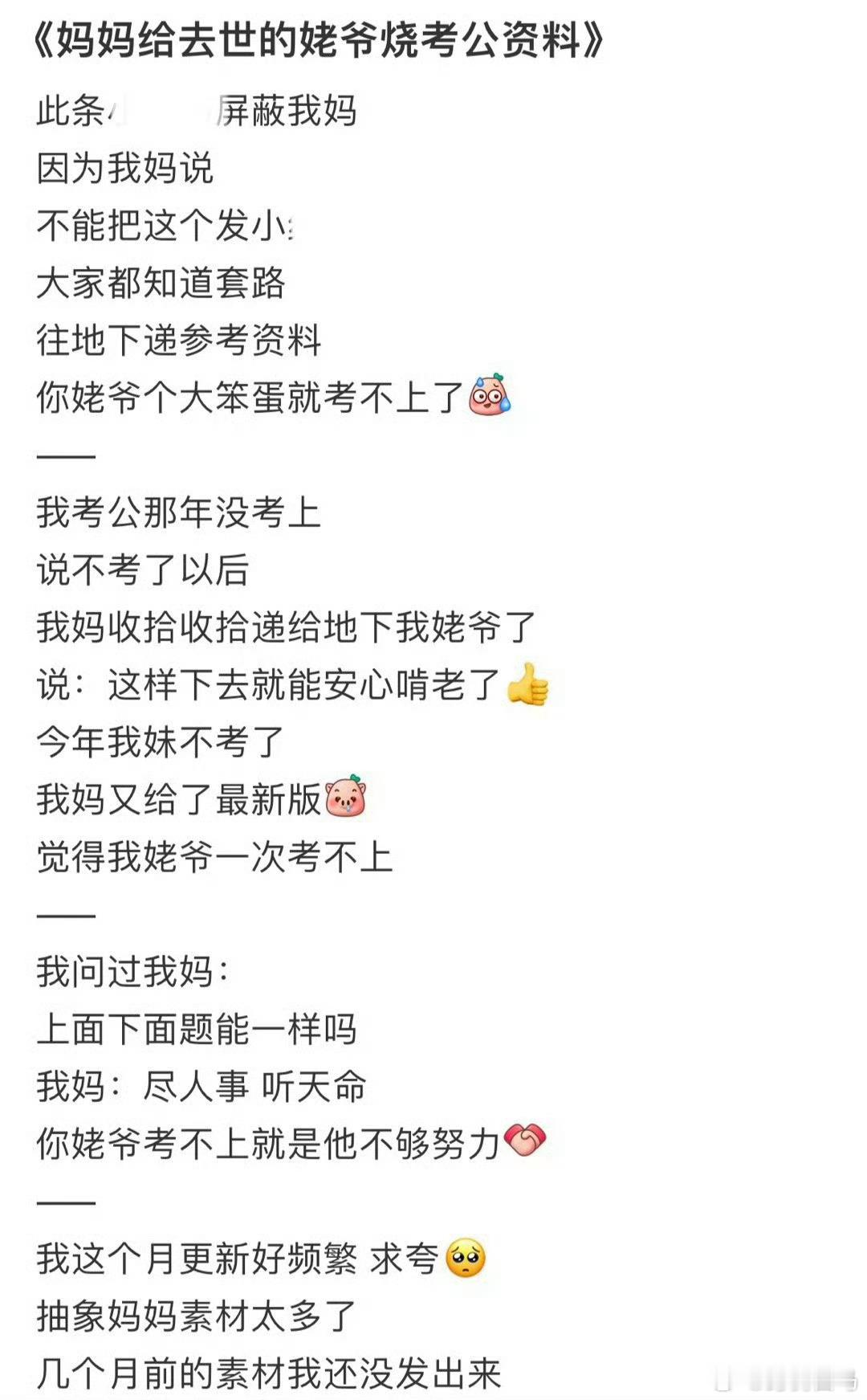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我和大哥家轮流养老,四月份的时候,母亲在大哥家摔了一跤。 那天我正在菜市场给孩子挑草莓,大哥的电话带着哭腔打过来:“小妹,妈在阳台够那盆绿萝,踩着凳子晃了一下,坐地上起不来了!”我手一抖,草莓盒子“啪”地掉在水泥地上,鲜红的果子滚了一地,卖草莓的大姐赶紧帮我捡:“姑娘别急,先接电话!” 赶到医院时,母亲正坐在候诊椅上,右腿不敢沾地,手里紧紧攥着个旧布包——我认得,那是父亲生前给她缝的药包,里面总装着降压片和薄荷糖。医生看完片子说右踝骨骨裂,得打石膏固定,至少一个月不能走路。大哥蹲在母亲脚边,手指戳着石膏边缘:“都怪我,早知道把那盆破花扔了!”母亲却拍了拍他手背:“怪那凳子腿滑,跟花有啥关系?” 回家的路上,母亲突然说:“回老房子住吧,那边卧室离厕所近,我自己能挪。”我和大哥都愣住了——老房子在六楼,没电梯,父亲走后就空着,去年雨季还漏过雨。我和大哥面面相觑,她这是何苦呢?放着现成的照顾不要,偏要回那爬楼都费劲的老房子? 拗不过她,我们还是请人把老房子简单收拾了。大哥在卧室铺了厚厚的褥子,我买了带轮的便盆和折叠小桌。可第二天一早,我去送早餐,竟看见对门的张婶端着碗豆浆从屋里出来。“你妈凌晨五点就给我打电话,说馋我烙的葱花饼了。”张婶擦着手笑,“她年轻时帮我带大闺女,现在该我还人情了。” 我推门进去,母亲正趴在窗边看楼下,石膏腿直挺挺地伸着,床头柜上摆着父亲的黑白照片。“你爸种的那棵石榴树,今年又冒新芽了。”她指着楼下,声音有点发颤,“去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树也活不成了。”我这才发现,窗台上摆着个小喷壶,壶嘴还挂着水珠——她肯定是趁我们不在,偷偷给窗台上的多肉浇水了。 接下来的日子,张婶每天早上来,帮母亲擦身、热饭,下午就推着轮椅带她在小区里转。母亲话渐渐多起来,跟张婶说当年父亲怎么追她,说我小时候偷摘邻居家的枣被追着跑。有天我提前下班,听见母亲在屋里哼歌,是父亲生前最爱唱的《茉莉花》,跑调跑到天边,却比任何时候都好听。 大哥每周来两次,扛着大米和蔬菜,趴在地上给母亲剪脚趾甲——以前他给女朋友剪指甲都手抖,现在却能顺着趾甲弧度慢慢修,母亲的脚蜷了蜷,他赶紧停手:“弄疼您了?”母亲笑着拍他手背:“傻小子,我是怕痒。” 一个月后拆石膏那天,母亲非要自己走两步。她扶着墙,右腿慢慢往下踩,膝盖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张婶在旁边伸手护着,大哥蹲在前面张开胳膊:“妈,别怕,摔了有我接着。”母亲走了三步,突然停下来,看着我们,眼泪掉在地上:“我总想着,不能成你们的累赘,可你们爸说了,一家人,哪有什么累赘,都是心尖上的肉。” 现在母亲能拄着拐杖慢慢走了,每天早上都要去楼下看那棵石榴树。昨天我带孩子回去,她正和张婶坐在树下择菜,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们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把碎金子。孩子跑过去抱住母亲的腿:“奶奶,等石榴熟了,我要摘最大的给您!”母亲摸了摸孩子的头,又看了看父亲的照片,嘴角弯成了月牙。 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摔一跤怕什么,只要身边有惦记的人,有能回去的地方,那些疼啊难啊,就都成了过眼云烟。就像母亲常说的,人老了,就跟树似的,根扎得深,风再大也吹不倒——因为根底下,都是一家人的念想啊。
“冲动是魔鬼!”上海,女子在二楼冲洗窗台,脏水漏到一楼阳台,遭邻居质问,女子怼一
【7评论】【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