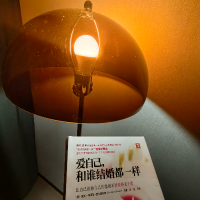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秋月姨的场景。
那年我才八岁,她穿着红围裙站在油锅前,金黄的糖醋里脊在铁勺上滋滋作响。
她当时是“秋月快餐”的老板,她的店是我们整条街上生意最红火的饭店,整条街都飘着她家饭菜的香气。
在我的印象里,她做事总是这么风风火火,利利索索的,邻里关系也特别好,也是出了名的会攒钱。
当年26岁的秋月姨眼睛亮得像黑葡萄,胳膊上还留着烫伤的疤痕,"等姨攒够钱,就把二楼租下来开大酒楼。"隔壁王婶的缝纫机哒哒响:"小秋,流浪猫都比你家男人吃得好!"
那时我还不懂这话里的刺。只记得她记账本上密密麻麻画着星星,卖出一百份糖醋里脊就涂满一颗。
菜场张叔的烟头常把纸页烫出洞:"攒钱开酒楼?先管住你家赌鬼吧!"
1995年的一天,我撞见她赤脚追打煤气贩子。五金店老板娘尖着嗓子嚷:"离得好!那种烂人早该踹了!"
我才知道她老公好赌,欠了一屁股债,秋月姨这几年挣的钱都给他还债了。最后,为了保住房子,实在没办法,秋月姨最终离婚,也算一种解脱。

后来,街坊们都劝她还是得找个伴儿。
秋月姨相亲那天,我蹲在裁缝店卷帘门后啃冰棍。那天来相亲的男人,胸前的税务局工作证闪着冷光。
"我们小秋勤快着呢。"刘主任的瓜子壳落在他新擦的皮鞋上,"就是命苦,摊上个挨千刀的前夫。"
秋月姨盛鱼汤的手抖得厉害,汤汁在红毛衣上洇出暗痕。
没过多久,秋月姨和周叔叔结婚了,没过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生,靠秋月姨的勤劳肯干,他们的快餐店也变成了两层酒楼。

生活似乎越来越好,但命运并没有放过秋月姨。
十年后,再次见到秋月姨,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她还是我认识的秋月姨吗?
她躺在麻将馆的躺椅上,脚边堆着空酒瓶。曾经乌黑的头发像枯草似的,肚子上堆着三层赘肉。
"你周叔现在可是副局长了。"她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冷笑,金镯子滑到手腕骨。
秋月姨说,上周在酒店抓到老周和小三,你猜他说什么?'闹够没有?要不离婚?'",威胁我。麻将牌上的幺鸡被她抠掉了眼睛,只剩两个空洞的凹槽。
她突然掀翻麻将桌,血红的指甲掐进我胳膊:"离?我儿子怎么办?我忍了八年!八年!"碎玻璃扎进她脚掌,她却像不知道疼似的。"
当年他跪着求我关店,说养我一辈子......"墙上的电子钟显示凌晨三点,自动报时的布谷鸟叫了半声就卡住,在寂静里发出诡异的"咕——"。

去年冬天,我去医院看她,她脸色蜡黄、瘦得脱了相,那时的她已经是癌症晚期,却挣扎着要涂口红:"不能让你周叔丢脸。"
我不明白那个伤秋月姨最深的男人,为啥还要在乎他呢。
仪器突然尖叫起来,她死死抓住我:"存折在空调后面...给小雨...别让周家人知道......"眼睁睁看着秋月姨在我眼前离开,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葬礼上,周叔是带着小三来参加的,小儿子围着棺材跑圈。我趁乱溜回老宅,从空调后面摸出存折。
每月18号都存着两千块,整整存了十五年。存折内页用圆珠笔画着小小的红围裙,1998年那页写着:小雨钢琴班押金。秋月姨像无数传统女性,把自己的一辈子捆绑在"贤妻良母"的绳索上,却不知这根绳索早被渣男淬了毒。
那些每月18号的存款,是母亲留给孩子最后的生存课。在失败婚姻的折磨下,唯有经济独立能守住她最后的尊严。
秋月姨的存折密码,或许就藏在她系了三圈的围裙带里,那是被生存重担勒进血肉的,永不松脱的执念。
秋月姨,你这一生值吗?如果可以重来一次,希望你换个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