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号称“洋抖难民”(tiktok refugees)的大批外国人疯狂涌入小红书。
不仅有展示才艺的,还有大批老外和中国用户互相玩梗,恶补中文的。
无论是外国人勇闯中文互联网,还是我们踏进异国他乡,不同的文化语境对我们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怎么才算融入不同的文化?我们融入的语境是否同想象中的一样?
在《美丽、遥远又野性》里,有四十年旅行经历的马蒂亚斯·波利蒂基从他在古巴的见闻写起,思考“何时才算真正进入一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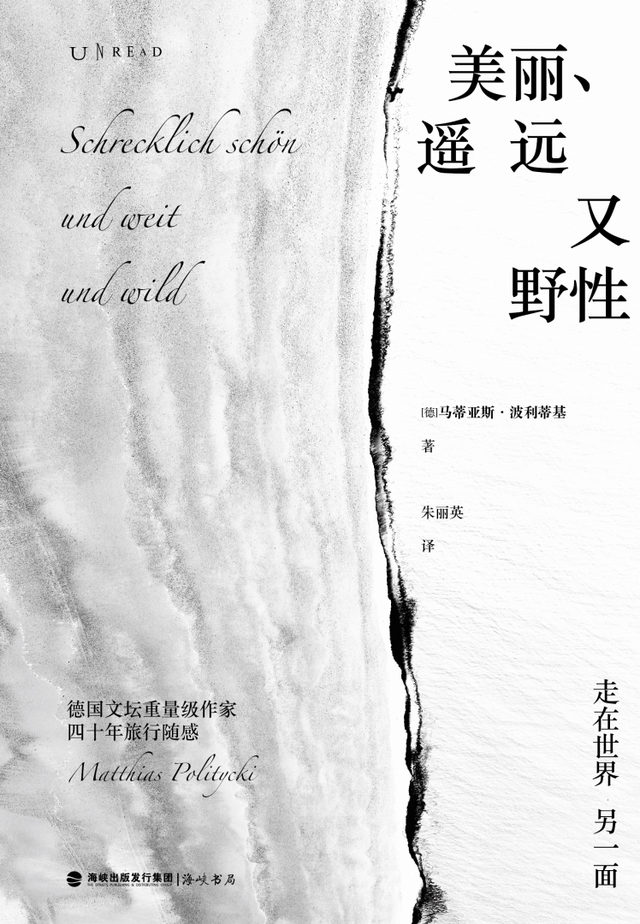 [德]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著朱丽英|译未读·文艺家|出品「一个人离开家乡是因为渴望结交陌生的人、探访不熟悉的地方。」这是我生平唯一融进一个陌生国家的机会。深度融入一个国家,是每个旅行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像当地人一样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平静而娴熟地在那里过着新的生活,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员。实际上,一个人离开家乡是因为渴望结交陌生的人、探访不熟悉的地方。一旦你接受了国外的生活,就想全身心融进这个陌生的社会,很快,你就会发现那里的生活跟你家乡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平淡无聊,也经常遇到令人烦恼的事。到达后不久,原本对当地人的傲慢就转变成了融入他们的愿望。这正是我们想要区别于游客的地方。接受当地人的某些特点,学习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很有趣,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德]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著朱丽英|译未读·文艺家|出品「一个人离开家乡是因为渴望结交陌生的人、探访不熟悉的地方。」这是我生平唯一融进一个陌生国家的机会。深度融入一个国家,是每个旅行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像当地人一样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平静而娴熟地在那里过着新的生活,把自己当作其中一员。实际上,一个人离开家乡是因为渴望结交陌生的人、探访不熟悉的地方。一旦你接受了国外的生活,就想全身心融进这个陌生的社会,很快,你就会发现那里的生活跟你家乡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平淡无聊,也经常遇到令人烦恼的事。到达后不久,原本对当地人的傲慢就转变成了融入他们的愿望。这正是我们想要区别于游客的地方。接受当地人的某些特点,学习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很有趣,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另外,了解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也是一种乐趣——无论你是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往麦片里倒入布什米尔威士忌,还是在西班牙大加纳利岛上品尝添加了甜炼乳的可塔朵咖啡,或者在丹麦品尝接骨木啤酒。在某些时候,你会放纵自己,点上一袋水烟,来一包不加香料的烟草,像当地男人那样,吸上第一口就感到兴奋。或者给自己买一包槟榔、甘草和嚼烟的混合物,就像排队站在你前边的那个男人买的那种,之后你不得不在阳台上紧紧抓着栏杆,好几个小时不停打嗝。与此同时,附近寺庙里好像总有同一首歌传来。
另外,了解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也是一种乐趣——无论你是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往麦片里倒入布什米尔威士忌,还是在西班牙大加纳利岛上品尝添加了甜炼乳的可塔朵咖啡,或者在丹麦品尝接骨木啤酒。在某些时候,你会放纵自己,点上一袋水烟,来一包不加香料的烟草,像当地男人那样,吸上第一口就感到兴奋。或者给自己买一包槟榔、甘草和嚼烟的混合物,就像排队站在你前边的那个男人买的那种,之后你不得不在阳台上紧紧抓着栏杆,好几个小时不停打嗝。与此同时,附近寺庙里好像总有同一首歌传来。「人们最容易首先获得社会底层的联系。」
融入一个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不引人注目的,通常只有在你融入之后很久,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明显的标志是当我开始下意识地低头走路,因为我已经熟悉了这条路上所有的东西;当我形成了购物和乘车的习惯,例如我知道乘坐地铁时,什么时候该从最后一节车厢上车、什么时候该从第一节车厢上车;当我知道在自动扶梯上应该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或者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不假思索地去做的时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每个国家,在同一个国家,又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种姓和等级。人们最容易首先获得社会底层的联系,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出现在汽车站、街头小吃摊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汇集点,这些地方也是旅行者经常光顾之地。 当然,上层社会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性格特点,如果你有机会混入这个阶层——当他们在墨西哥酒店后花园的白孔雀中间喝咖啡,或者在加勒比海圣巴特的名流海滩上沉溺于百加得的酒精之梦——那么你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最固执的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极力躲避旅行者。里斯本、哥本哈根、爱丁堡等旅行目的地,对旅行者来说似乎很近但又很远。即使我在维也纳生活了一年,有意使用各种奥地利词汇,但我在维也纳人眼里仍然是一个德国佬。某些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几乎跟在德国一样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完全南辕北辙。任何细微差别都意味着很多不同内容,一个错误的声调就会暴露你的身份,使你手足无措像个愚蠢的德国人——这正是所有德国人在国外最原始的恐惧!这是不是融入异国文化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因呢?某些情形能够让人最为迅速地融入。比如想成为东京人,就必须了解涩谷那些俱乐部,必须戴上蓝色的隐形眼镜(以便看起来愉悦、目光有神)。男人的穿着、妆容和行为要尽可能地女性化,女人则要尽可能地男性化,用阴暗的配饰一改普遍流行的卡哇伊外观,一个流血的娃娃、一个眼罩、一件印着“死亡”字样的T恤。但是,有谁想以这种方式融入东京,融入一个与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世界呢?
当然,上层社会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性格特点,如果你有机会混入这个阶层——当他们在墨西哥酒店后花园的白孔雀中间喝咖啡,或者在加勒比海圣巴特的名流海滩上沉溺于百加得的酒精之梦——那么你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最固执的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极力躲避旅行者。里斯本、哥本哈根、爱丁堡等旅行目的地,对旅行者来说似乎很近但又很远。即使我在维也纳生活了一年,有意使用各种奥地利词汇,但我在维也纳人眼里仍然是一个德国佬。某些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几乎跟在德国一样的东西,实际上很可能完全南辕北辙。任何细微差别都意味着很多不同内容,一个错误的声调就会暴露你的身份,使你手足无措像个愚蠢的德国人——这正是所有德国人在国外最原始的恐惧!这是不是融入异国文化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因呢?某些情形能够让人最为迅速地融入。比如想成为东京人,就必须了解涩谷那些俱乐部,必须戴上蓝色的隐形眼镜(以便看起来愉悦、目光有神)。男人的穿着、妆容和行为要尽可能地女性化,女人则要尽可能地男性化,用阴暗的配饰一改普遍流行的卡哇伊外观,一个流血的娃娃、一个眼罩、一件印着“死亡”字样的T恤。但是,有谁想以这种方式融入东京,融入一个与自己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世界呢? 「一个人只能进入自己所属的社会。」人的一生中总要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如果你相信女权主义者洁莎·克里斯宾的理论的话,男人和女人的方法是不同的。在她看来,从伯顿到查特文的男性旅行作家,当他们以极限方式“征服”了旅行之国,通常都会采取后殖民主义的态度,一旦进入该国,他们很快就会自视为专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像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这样的女性旅行作家,她们首先审视自己,感受自身的心理状态,观察陌生人怎么对待她们。她们寻求一种超越婚姻和父母身份的真实生活,旅行之地只是她们自我发现的催化剂。上述两种方式都是加引号的融入,是一种极其巧妙的自欺欺人。不仅如此,旅行作家(无论性别)能否被视为普通旅行者的代表,似乎也值得怀疑。有些人,如尼古拉斯·布韦尔,在国外之所以彻底崩溃,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沉迷于幻想,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融入那里的社会生活。他在斯里兰卡的日子里忍受炎热酷暑,忍受当地人以及蚊虫的不断侵扰。他了解得越多,理解得就越少,最后终于匆忙逃离了这个国家。
「一个人只能进入自己所属的社会。」人的一生中总要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如果你相信女权主义者洁莎·克里斯宾的理论的话,男人和女人的方法是不同的。在她看来,从伯顿到查特文的男性旅行作家,当他们以极限方式“征服”了旅行之国,通常都会采取后殖民主义的态度,一旦进入该国,他们很快就会自视为专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像伊丽莎白·吉尔伯特这样的女性旅行作家,她们首先审视自己,感受自身的心理状态,观察陌生人怎么对待她们。她们寻求一种超越婚姻和父母身份的真实生活,旅行之地只是她们自我发现的催化剂。上述两种方式都是加引号的融入,是一种极其巧妙的自欺欺人。不仅如此,旅行作家(无论性别)能否被视为普通旅行者的代表,似乎也值得怀疑。有些人,如尼古拉斯·布韦尔,在国外之所以彻底崩溃,就是因为他长时间沉迷于幻想,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融入那里的社会生活。他在斯里兰卡的日子里忍受炎热酷暑,忍受当地人以及蚊虫的不断侵扰。他了解得越多,理解得就越少,最后终于匆忙逃离了这个国家。 另外一些人,如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在返回他的出生地斯里兰卡后,曾公开感叹,当地人不仅历来将游客排除在外,也将在那里世代居住的欧洲人排除在外。“在那里,巨大的社会鸿沟横亘在本土居民和欧洲侨民及英国侨民之间,他们从来不是斯里兰卡社会的一员。”翁达杰道出的个中缘由,也适用于世界各地:“要么这块土地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在此生息成长,要么我们是陌生人、入侵者。”翁达杰使用“属于”这个词,指的并不是物质的占有,而是原住民和侨民之间的典型对比,他甚至把在斯里兰卡定居的英国人称为“过客”。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进入自己所属的社会。就在我离开古巴圣地亚哥之前,这座城市又给我上了第二堂课。好几天以来,人们都在谈论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又有一艘游轮停靠在码头。整个城市似乎都出动了,人们奔走相告,我也赶到了码头。我发现有些奇怪,那里的人我竟然都不认识,通常情况下,你总会遇到一些人。到了市中心,我跟在从游轮上下来的游客后面散步时才忽然明白:圣地亚哥周围地区的所有轻浮的人,都装扮成了圣地亚哥人,有的怀抱吉他,有的没有,他们都涌进了这座城市,装扮成快乐的乞丐、歌手、城市导游、杂耍艺人,当然还有jineteros和jineteras,他们专门盯着独身的旅行者。大街小巷到处充溢着轻快和欢乐:关塔纳梅拉!“这正是我想象中的古巴,”一位女士兴奋地说,“如此贫穷,却又如此充满生活乐趣!”另一个人说:“古巴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先生们心甘情愿地掏出美元,扔进了今天才出现在城里的很多帽子里。人们磕磕巴巴地说着什么,又跳又唱,互相开着玩笑,每个人都感到满足。当游轮在傍晚起航离开时,所有喧嚣瞬间消散,城市的街道又恢复了我熟悉、喜爱的忧郁和沉闷。我想象着游轮上的客人倚在栏杆旁,喝着“自由古巴”鸡尾酒,庆祝他们愉快的短暂登陆。他们今天虽然没有进入古巴社会,但完全自我陶醉了。我思忖,在旅途中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我真有点羡慕他们了。
另外一些人,如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在返回他的出生地斯里兰卡后,曾公开感叹,当地人不仅历来将游客排除在外,也将在那里世代居住的欧洲人排除在外。“在那里,巨大的社会鸿沟横亘在本土居民和欧洲侨民及英国侨民之间,他们从来不是斯里兰卡社会的一员。”翁达杰道出的个中缘由,也适用于世界各地:“要么这块土地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在此生息成长,要么我们是陌生人、入侵者。”翁达杰使用“属于”这个词,指的并不是物质的占有,而是原住民和侨民之间的典型对比,他甚至把在斯里兰卡定居的英国人称为“过客”。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进入自己所属的社会。就在我离开古巴圣地亚哥之前,这座城市又给我上了第二堂课。好几天以来,人们都在谈论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又有一艘游轮停靠在码头。整个城市似乎都出动了,人们奔走相告,我也赶到了码头。我发现有些奇怪,那里的人我竟然都不认识,通常情况下,你总会遇到一些人。到了市中心,我跟在从游轮上下来的游客后面散步时才忽然明白:圣地亚哥周围地区的所有轻浮的人,都装扮成了圣地亚哥人,有的怀抱吉他,有的没有,他们都涌进了这座城市,装扮成快乐的乞丐、歌手、城市导游、杂耍艺人,当然还有jineteros和jineteras,他们专门盯着独身的旅行者。大街小巷到处充溢着轻快和欢乐:关塔纳梅拉!“这正是我想象中的古巴,”一位女士兴奋地说,“如此贫穷,却又如此充满生活乐趣!”另一个人说:“古巴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先生们心甘情愿地掏出美元,扔进了今天才出现在城里的很多帽子里。人们磕磕巴巴地说着什么,又跳又唱,互相开着玩笑,每个人都感到满足。当游轮在傍晚起航离开时,所有喧嚣瞬间消散,城市的街道又恢复了我熟悉、喜爱的忧郁和沉闷。我想象着游轮上的客人倚在栏杆旁,喝着“自由古巴”鸡尾酒,庆祝他们愉快的短暂登陆。他们今天虽然没有进入古巴社会,但完全自我陶醉了。我思忖,在旅途中不能抱有太高的期望,我真有点羡慕他们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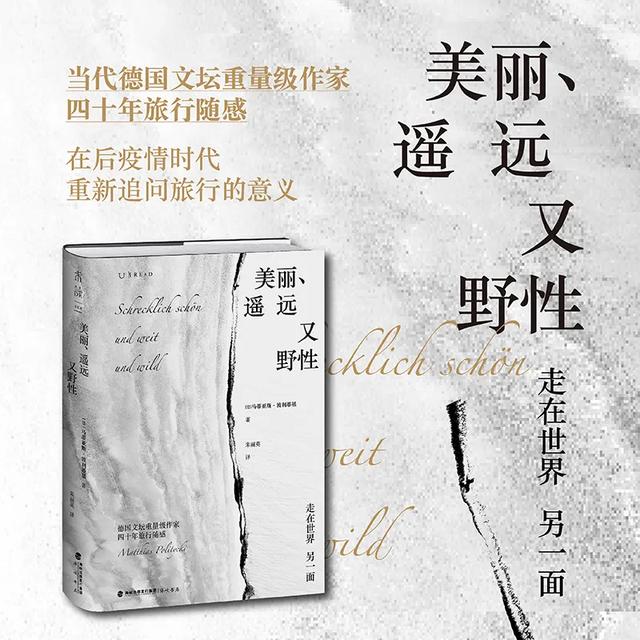 -本期话题-你认为融入另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留言区分享~
-本期话题-你认为融入另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留言区分享~ 编辑|泰若克塔图片|网络
编辑|泰若克塔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