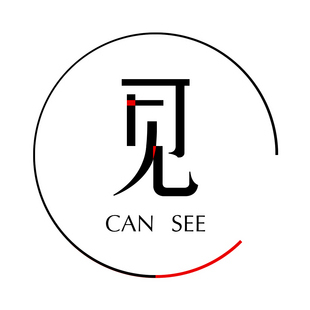始于土,成于火
瓷比玉,宁碎不折
公生明,廉生威
正必德,宁折不弯


江主民
景德镇陶瓷艺术家
相
遇
在昆明碧鸡关艺术园区内的一角,一间毫不起眼的小工作室摆满了各种釉色的瓷器。透过阳光,映入眼帘的是整片未烧制的半成品,仿佛给我一种到了景德镇的感觉。店里没什么人,门却敞开着,我循着小道走了下去,看到一位老师傅正在太阳下看着一个红色杯子发呆。


旁边的炉子内摆满了刚开窑的各种瓷器。他脸上的笑容告诉我:“这窑烧的不错”。走过去交谈一番后得知,这个杯子的釉色是“郎红”。


他和我讲起了“若要穷,烧郎红”的故事,言语中伴随欣喜略带些许顽皮。郎窑红釉是以少量微量元素为着色剂,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极为困难,数百窑亦难烧成一件。便有了“家有郎红,吃穿不愁”一说。



相
知
他叫江主民,是上世纪80年代景德镇陶瓷厂的制瓷师傅,后来在下岗浪潮中出来自己做瓷器。2009年被世界艺术家联合会授予“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说起艺术大师这个事,他只是一语带过:“什么大师不大师的,我只是爱玩泥巴。”说完笑笑便忙活去了。


五年前,女儿安家昆明后,他便把手艺带来了云南。多年在景德镇和昆明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工作室落地云南,取名山南。

泥与火的
艺术
“泥塑火烧,不打包票”。瓷器,是泥与火的艺术,陶瓷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细致的过程。从原料到烧成,任何一道工序的疏忽都会影响成品的质量。

凝聚匠人智慧的七十二道工序,一直在不断改进。在现代工艺的支撑下,现代瓷器的制作步骤简略了一些,也降低了陶瓷制作的门槛。

从练泥、拉胚、修胚、施釉、到烧窑成型,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做到极致。这样做出来的瓷器才能达到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特性。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在完成烧制前的准备后便等来了最为关键的一环——烧窑。


在1320度高温的淬炼下,一件件作品浴火重生,迎来了它们最为光鲜亮丽的一面。


就是
“玩”
江师傅的女儿和女婿深受其影响,带着做瓷的兴趣也参与进来。平时会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与父亲进行交流。新时代年轻人对工匠精神做出的解读是:并不一定完全成为手艺人,可以借由工匠的手艺去实现自己的设计,用玩的态度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尽享有态度的玩味。

工艺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匠人对于艺术的追求。年轻人对于传统手艺的理解,更多的是致敬,想要在传统手艺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自然少不了一阵打磨。而这,也让江师傅犯了难。

景德镇本身的环境造就了一代代最为纯粹的陶瓷手艺人。父辈和年轻人观念的冲突,对传承不一样的看法,对设计不一样的构思,变成了两代人的对话和一个时代背景的缩影。好在江师傅也是学陶瓷设计出身,并不只是单纯的手艺人,在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工作室渐渐奠定了自己的风格。

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他们设计了一系列作品,釉色独特,寓意颇深。谷雨系列釉面青翠欲滴,惊蛰系列表现春雷炸响,给人一种破土而出的感觉。


谷雨系列


惊蛰系列
尽享
玩味
在云南待久了便是家乡吧,做了半辈子瓷器的江师傅在云南有了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给了他一种疯狂。他想用云南的陶土和景德镇制瓷的工艺结合做一点尝试,能否做出新鲜的东西。

也许是年轻人那句“用玩的态度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尽享有态度的玩味”影响了他。年轻人的奇思妙想总能给他带来了新的灵感和新的创作。

正如有一天,江师傅在闲暇之余拿起一坨泥漫无目的的捏,捏着捏着,一个人面像出来了。他说:“当我做出来的时候还想着挺有意思的,感觉它在看着我笑,我也对着它笑,就傻傻地定在哪里。烧制出来后,也给了我一定的惊喜。”


做了一辈子瓷器,每次开窑都保持一份紧张和期待,这是一场人和火的博弈。人生和做瓷一样的乐趣可能就在于没有预知性,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可能就是制瓷的魅力和初心。而对于他来说,永远怀着敬畏之心做好每一个器物,烧好每一次窑,无关乎年龄,做一辈子只是热爱。

手工艺是一个可以从中寻找温暖与幸福的盒子,里面摆满了属于“人”的特性。在手作的世界里,一生只做一件事,用手的温度去触碰这些器物,去感受它们所带来的喜悦感。在手艺人粗糙的手纹,严谨的手艺里,创造力熠熠生辉。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