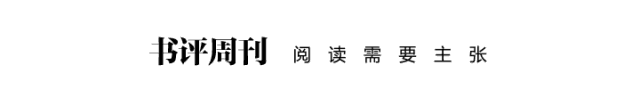 库切在其自传体小说《男孩》中记述了一个场景:在南非开普省的伍斯特镇,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母亲笨拙执拗地学会了骑自行车;一天早上,男孩库切瞥了一眼母亲骑行的背影,她穿着白上衣和深色裙子,头发在风中飘扬,看上去年轻、精神,像个女孩子,还有那么一点诡秘。母亲踩着踏板驶向杨树大街,离开家,逃向自己,这一形象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记忆。在这一场景中,库切从母亲身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形象,之前,母亲就只是母亲,这一次,母亲是个自由独立、充满魅力的女孩,或许比这还要更多。 《陌生的阿富汗》,无论是本书的作者班卓还是书中的内容,都让我想起库切所描述的这一场景,激起我类似的感受。班卓是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但我熟悉的也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部分,而旅行者赛玛、书中的阿富汗,对我来说都颇为陌生,因此,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几乎是把它当作一部小说读完的,而它也的确是一部具有小说品格的游记。做出这一论断,并非意在进行文体类型比较,也没否认它作为游记的真实性和记录性,而是认为作者的笔力使这部游记具有了小说的品格。
库切在其自传体小说《男孩》中记述了一个场景:在南非开普省的伍斯特镇,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母亲笨拙执拗地学会了骑自行车;一天早上,男孩库切瞥了一眼母亲骑行的背影,她穿着白上衣和深色裙子,头发在风中飘扬,看上去年轻、精神,像个女孩子,还有那么一点诡秘。母亲踩着踏板驶向杨树大街,离开家,逃向自己,这一形象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记忆。在这一场景中,库切从母亲身上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形象,之前,母亲就只是母亲,这一次,母亲是个自由独立、充满魅力的女孩,或许比这还要更多。 《陌生的阿富汗》,无论是本书的作者班卓还是书中的内容,都让我想起库切所描述的这一场景,激起我类似的感受。班卓是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但我熟悉的也只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部分,而旅行者赛玛、书中的阿富汗,对我来说都颇为陌生,因此,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几乎是把它当作一部小说读完的,而它也的确是一部具有小说品格的游记。做出这一论断,并非意在进行文体类型比较,也没否认它作为游记的真实性和记录性,而是认为作者的笔力使这部游记具有了小说的品格。
 作者|李忠敏
作者|李忠敏  将我们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游记记述的是发现的旅程,旅人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以自身的经验和眼光打量和体验着这个新世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将之记录下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记录者的选材与记忆过滤。游记中的“发现”好似当下年轻人爱玩的开盲盒,充满着未知、冒险和奇趣。
将我们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游记记述的是发现的旅程,旅人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以自身的经验和眼光打量和体验着这个新世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将之记录下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记录者的选材与记忆过滤。游记中的“发现”好似当下年轻人爱玩的开盲盒,充满着未知、冒险和奇趣。

 写出人的文化特性,也写出人的普遍性 俄罗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经历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转型,东正教文化源远流长,成为塑造其民族性格的主导因素,俄罗斯人将宗教信仰实践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对爱情的理解上,精神层面的共鸣必不可少。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特维尔街成百上千的行人中遇到玛格丽特,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目光中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她眼神中那非同寻常的、任何人都从未看到过的孤独”,大师越过玛格丽特的外貌衣着直接捕捉到了她内在的状态,显然这不是欲望的相互吸引,而是两个个体的精神相遇,一个温柔善意的人才会体恤到另一个人的痛苦和孤独,因此,它也是两个神圣生命的相互体认,这样的爱一旦产生便是共担命运的永恒。 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宗教不只是个人内在的信仰,更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人的精神秩序一致的保障,一切都要符合对真主的信仰,爱情与婚姻也要纳入这一范畴加以考量。《陌生的阿富汗》也提到了爱情,但它既不是西欧式的爱欲邂逅,也不是俄罗斯式的精神共鸣,倒像是虔诚信徒信奉的真主的一道命令。与赛玛一路遇到的其他男子相比,穆利算不上有趣,但他绝对神秘,这种神秘源自宗教信仰、政治使命、自然人性的合力造就而成的混合型特质。穆利是个会说英语、坚持写诗的男子,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他从始至终慷慨无私地帮助赛玛,推荐她寄居在一个美善之家,显示出正直的品格和担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穆利也是个观念性很强的人,他认为赛玛适合做他的妻子,便向她下了一道“爱情”的命令:赛玛需要皈依真主,两人最好一起前行,他好护她周全。穆利不但命令,而且付诸行动,在赛玛还没有应允且有意回避他后,他仍然一厢情愿地办好前往伊朗的签证,等待着与她同行。这种强烈而坚定的意愿就好似真主在督促着他行动,而非其他的驱动力。穆利是一个典型的阿富汗人,伊斯兰信仰不但写在他的诗句里,表现在他的言行上,也刻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以致于他生命的真实内核被包裹在了最深处,没有一条人世的通道可以照亮那里。《陌生的阿富汗》像小说一样以典型人物写出了人的文化特征,文化赋予人多样性和丰富性。阿富汗人对于我们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他们成长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
写出人的文化特性,也写出人的普遍性 俄罗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经历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转型,东正教文化源远流长,成为塑造其民族性格的主导因素,俄罗斯人将宗教信仰实践为对生命神圣性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对爱情的理解上,精神层面的共鸣必不可少。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特维尔街成百上千的行人中遇到玛格丽特,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目光中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她眼神中那非同寻常的、任何人都从未看到过的孤独”,大师越过玛格丽特的外貌衣着直接捕捉到了她内在的状态,显然这不是欲望的相互吸引,而是两个个体的精神相遇,一个温柔善意的人才会体恤到另一个人的痛苦和孤独,因此,它也是两个神圣生命的相互体认,这样的爱一旦产生便是共担命运的永恒。 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宗教不只是个人内在的信仰,更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人的精神秩序一致的保障,一切都要符合对真主的信仰,爱情与婚姻也要纳入这一范畴加以考量。《陌生的阿富汗》也提到了爱情,但它既不是西欧式的爱欲邂逅,也不是俄罗斯式的精神共鸣,倒像是虔诚信徒信奉的真主的一道命令。与赛玛一路遇到的其他男子相比,穆利算不上有趣,但他绝对神秘,这种神秘源自宗教信仰、政治使命、自然人性的合力造就而成的混合型特质。穆利是个会说英语、坚持写诗的男子,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他从始至终慷慨无私地帮助赛玛,推荐她寄居在一个美善之家,显示出正直的品格和担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穆利也是个观念性很强的人,他认为赛玛适合做他的妻子,便向她下了一道“爱情”的命令:赛玛需要皈依真主,两人最好一起前行,他好护她周全。穆利不但命令,而且付诸行动,在赛玛还没有应允且有意回避他后,他仍然一厢情愿地办好前往伊朗的签证,等待着与她同行。这种强烈而坚定的意愿就好似真主在督促着他行动,而非其他的驱动力。穆利是一个典型的阿富汗人,伊斯兰信仰不但写在他的诗句里,表现在他的言行上,也刻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以致于他生命的真实内核被包裹在了最深处,没有一条人世的通道可以照亮那里。《陌生的阿富汗》像小说一样以典型人物写出了人的文化特征,文化赋予人多样性和丰富性。阿富汗人对于我们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他们成长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
 《阿富汗之旅》剧照。 小说不但要写具有文化特质的人,也要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后者使人得以超越国别、民族、语言、文化的隔阂而达成沟通,某种程度上小说构建的是一个聚合性空间,人们在分裂中寻求和解,在差异性中看到同一性,最终走向兄弟姐妹式的情谊。《陌生的阿富汗》最具魅力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聚合性的空间,在其中陌生人之间互相关怀体恤,他们突破文化与生存的防御机制,在某一时刻达到心灵的无碍交流。蹲在白沙瓦老城区幽暗巷子里的阿富汗人,一个住过难民营、走私过鸦片的中年男子,看见黄昏时刻还在巷子里闲逛的赛玛,竟担心她的安危,诚挚地邀请她到家中坐一坐,带她到自己所开的店铺里逛一逛,充满信赖地向她讲述自己复杂的经历。喀布尔市的警察纳维德看到独自穿行在巴扎人流中的赛玛,便决定要保护她,一脸真诚地称“你是我的姐妹”,向她分享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家人的照片,带她到他学习karate的学校参观,甚至爱屋及乌地帮助她同屋的病人史太郎,纳维德最后以照片丢失为由向赛玛和史太郎要钱,是真诚求助,还是有意勒索,意图已无从知晓,但那一路的相随相助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在人性的疑点处留下空白,让人性的光辉闪烁在旅途的黯淡之中。“歌声与少年”中的少年,在短暂的车程中无声而细致地帮助病弱的赛玛,频繁地为她摇下和关上车窗,让她既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又不至于被灰尘袭击;在军事检查站时为她解围;在歇脚的地方,单独为她提上一桶水,让她能够彻底地清洗一番,洗去满面尘灰的疲惫;悄悄地拿给她两个洗好的青苹果,让她在食物单调、胃口败坏的情况下得以饱餐一顿。在作者笔下,少年没有名字,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那无声的温柔与慷慨却如沙漠中的绿洲,温暖着赛玛,也打湿了读者的眼眶。还有那些在路途中随时截住赛玛,或要载她一程,或要她到家里歇歇脚的人们。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
《阿富汗之旅》剧照。 小说不但要写具有文化特质的人,也要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后者使人得以超越国别、民族、语言、文化的隔阂而达成沟通,某种程度上小说构建的是一个聚合性空间,人们在分裂中寻求和解,在差异性中看到同一性,最终走向兄弟姐妹式的情谊。《陌生的阿富汗》最具魅力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聚合性的空间,在其中陌生人之间互相关怀体恤,他们突破文化与生存的防御机制,在某一时刻达到心灵的无碍交流。蹲在白沙瓦老城区幽暗巷子里的阿富汗人,一个住过难民营、走私过鸦片的中年男子,看见黄昏时刻还在巷子里闲逛的赛玛,竟担心她的安危,诚挚地邀请她到家中坐一坐,带她到自己所开的店铺里逛一逛,充满信赖地向她讲述自己复杂的经历。喀布尔市的警察纳维德看到独自穿行在巴扎人流中的赛玛,便决定要保护她,一脸真诚地称“你是我的姐妹”,向她分享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家人的照片,带她到他学习karate的学校参观,甚至爱屋及乌地帮助她同屋的病人史太郎,纳维德最后以照片丢失为由向赛玛和史太郎要钱,是真诚求助,还是有意勒索,意图已无从知晓,但那一路的相随相助却是不争的事实,作者在人性的疑点处留下空白,让人性的光辉闪烁在旅途的黯淡之中。“歌声与少年”中的少年,在短暂的车程中无声而细致地帮助病弱的赛玛,频繁地为她摇下和关上车窗,让她既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又不至于被灰尘袭击;在军事检查站时为她解围;在歇脚的地方,单独为她提上一桶水,让她能够彻底地清洗一番,洗去满面尘灰的疲惫;悄悄地拿给她两个洗好的青苹果,让她在食物单调、胃口败坏的情况下得以饱餐一顿。在作者笔下,少年没有名字,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那无声的温柔与慷慨却如沙漠中的绿洲,温暖着赛玛,也打湿了读者的眼眶。还有那些在路途中随时截住赛玛,或要载她一程,或要她到家里歇歇脚的人们。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
 在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 最后一章“八个镯子的家庭”更是勾画了一个理想的聚合性空间,沙赫伯一家是传统的阿富汗家庭,却具有敞开性和接纳性,能使一个外国人、外族人、异乡人迅速融入其中而没有陌生感,在其中,我们可以象征性地看到本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普遍性、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少年沙赫伯虽尊穆利为精神导师,却似乎比穆利更容易沟通,他带赛玛外出时,也要求她穿上具有本地特色的布卡,刻意与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过分,这只是在让赛玛尊重他们民族的文化习俗,回到家中他和赛玛可以亲如姐弟。母亲纳莉亚一见面便将赛玛视为闺友,盛情款待,闲叙家常,让她穿自己的服装和女儿的鞋子。妹妹德娃则像前面提及的那个少年一样,默然而深情地关注着赛玛,把她当作贴心的姐姐和知己,临别还把自己手臂上的八个镯子脱下来送给她。被艰辛的旅途损耗得憔悴不堪的赛玛正是在这个家庭中得到疗愈。在人类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镯子会碎掉,但氤氲其中的爱意却保留了下来。 《陌生的阿富汗》以简洁隽永的语言勾勒了阿富汗的地理环境、生活场景、人物群像,其中不乏作者对阿富汗历史、文化、现状的独到见解,同时又以诗性的叙述呈现了阿富汗人的精神品格,读来让人既翻涌在思想的浪花上又沉醉在美的氛围里。意犹未尽的是,阿富汗女性的那双眼睛还始终隐没在厚重的布卡的后面,其中藏着怎样的黯淡或火花,有待旅人去与她对视、探寻。 合上书页,思绪飘到了古希腊特洛伊的战场:战争进行到了第十年,希腊一方的阿基琉斯与特洛伊一方的赫克托耳也已完成对决,赫克托耳死去,阿基琉斯将他带到自己的营帐。夜幕降临,白发苍苍的普里阿摩斯孤身来到阿基琉斯的营帐,讨要儿子的尸体,看着他,阿基琉斯想起自己的父亲,两人都怀念亲人,不禁都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响彻房屋”。哭够之后,年轻人搀扶起老年人,“怜悯他的灰白头发、灰白胡须”。他们同桌饮酒吃肉,席间定定地看着对方,普里阿摩斯赞叹阿基琉斯好似天神,阿基琉斯对这位老者也充满敬佩。等他们互相看够了对方,老人请求年轻人赶紧安排他睡上一觉,在仇人的营帐里,特洛伊的老国王美美地安然睡去。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绝伦而在人间难以复刻的场景,但它却会在文学空间、人的心灵记忆中一次次涌现,我想,这也是班卓写《陌生的阿富汗》的意义之一。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忠敏;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在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 最后一章“八个镯子的家庭”更是勾画了一个理想的聚合性空间,沙赫伯一家是传统的阿富汗家庭,却具有敞开性和接纳性,能使一个外国人、外族人、异乡人迅速融入其中而没有陌生感,在其中,我们可以象征性地看到本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普遍性、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少年沙赫伯虽尊穆利为精神导师,却似乎比穆利更容易沟通,他带赛玛外出时,也要求她穿上具有本地特色的布卡,刻意与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过分,这只是在让赛玛尊重他们民族的文化习俗,回到家中他和赛玛可以亲如姐弟。母亲纳莉亚一见面便将赛玛视为闺友,盛情款待,闲叙家常,让她穿自己的服装和女儿的鞋子。妹妹德娃则像前面提及的那个少年一样,默然而深情地关注着赛玛,把她当作贴心的姐姐和知己,临别还把自己手臂上的八个镯子脱下来送给她。被艰辛的旅途损耗得憔悴不堪的赛玛正是在这个家庭中得到疗愈。在人类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壁垒中,唯有善与爱是融通的魔法,镯子会碎掉,但氤氲其中的爱意却保留了下来。 《陌生的阿富汗》以简洁隽永的语言勾勒了阿富汗的地理环境、生活场景、人物群像,其中不乏作者对阿富汗历史、文化、现状的独到见解,同时又以诗性的叙述呈现了阿富汗人的精神品格,读来让人既翻涌在思想的浪花上又沉醉在美的氛围里。意犹未尽的是,阿富汗女性的那双眼睛还始终隐没在厚重的布卡的后面,其中藏着怎样的黯淡或火花,有待旅人去与她对视、探寻。 合上书页,思绪飘到了古希腊特洛伊的战场:战争进行到了第十年,希腊一方的阿基琉斯与特洛伊一方的赫克托耳也已完成对决,赫克托耳死去,阿基琉斯将他带到自己的营帐。夜幕降临,白发苍苍的普里阿摩斯孤身来到阿基琉斯的营帐,讨要儿子的尸体,看着他,阿基琉斯想起自己的父亲,两人都怀念亲人,不禁都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响彻房屋”。哭够之后,年轻人搀扶起老年人,“怜悯他的灰白头发、灰白胡须”。他们同桌饮酒吃肉,席间定定地看着对方,普里阿摩斯赞叹阿基琉斯好似天神,阿基琉斯对这位老者也充满敬佩。等他们互相看够了对方,老人请求年轻人赶紧安排他睡上一觉,在仇人的营帐里,特洛伊的老国王美美地安然睡去。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绝伦而在人间难以复刻的场景,但它却会在文学空间、人的心灵记忆中一次次涌现,我想,这也是班卓写《陌生的阿富汗》的意义之一。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忠敏;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参与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