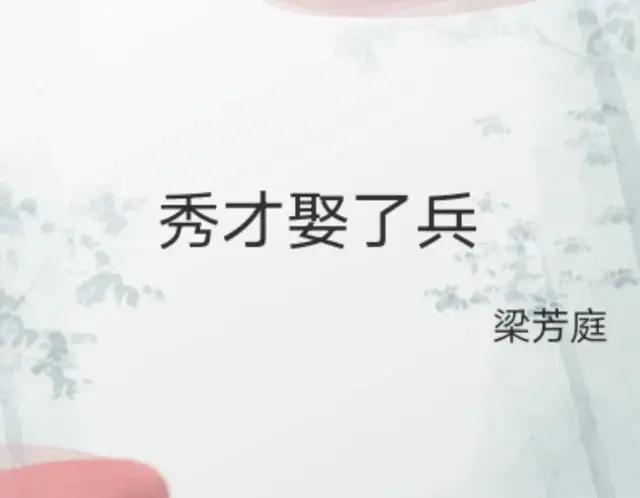《吹彻小梅春》
作者:韫枝

简介:
卫嫱知道,李彻最恨的人便是她。
二人原是青梅竹马,却因为旁人算计,她不得不以一杯毒酒,送了李彻上路。
却未料,他竟能捡回一命。
晋明十五年,李彻于城外起兵。
城门大破当日,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卫家,夺去她清白之身。
那夜灯花零落,她满面湿痕,耳边男人声音恨恨:“卫嫱,这本就是你欠我的。”
“你记住,往后的每时每刻,我都要你身在地狱,日夜求死。”
……
卫嫱看着他夺位登基。
看着曾经跟在自己身后、满眼是她的少年,变成一位冷漠无情的帝王。
李彻将她囚在宫中,日夜磋磨,却要她以最下贱的宫人自居。
于是,原来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一步步学会了洗衣生火,学会了看人眼色。
晋宣二年,帝后大婚。
李彻特意钦点了她前去敬酒。
他身侧坐着当今丞相之女,对方眉目温婉,她垂着眼上前,却因一个不慎,打翻了酒坛。
卫嫱无措跪在原地,看着一身喜服的帝王阴郁起身。
他冷着脸,捏住她的下巴。
如当年一般,将那灼烈的烈酒,强行灌入卫嫱的喉咙。
……
李彻冷漠地看她呛倒在地。
卫嫱满身狼狈,于地上干呕。
半晌,竟呕出一口鲜血。
酒中有毒。
她卧倒在李彻怀里,看着他逐渐慌乱的面色,声音愈发虚弱。
“奴曾奉陛下一杯毒酒,如今……陛下喂奴婢一杯。”
“奴婢与陛下,从此两清。”
大雪纷飞,喜色漫天。
帝王颤抖的鸦睫上,覆了一层寒霜。
李彻原以为自己早已心死。
他的心死在被年少爱人灌下毒酒的深夜里,却又跳动在这满室鲜红的深冬。
此后的每一日,他身在地狱,心痛欲死。
夜风吹彻他犯下的罪孽,此生此世,不得两清。
精彩节选:
风声是前半夜起的,踏踏铁骑声惊鹊,刀剑兵戈相接,乍起的火光将整个皇都都笼罩得通明。
前一刻,卫嫱尚在梦中。
闺阁之中,薰笼内燃着鹅梨香,清冷的薄雾带着甜津津的香气,梦的尽头好似下了一场梨花春雨。
亥时的青梨苑,一贯是安稳而清静的。
垂花屏风上光影晃荡着,“嘭”地一声,门口的铜盆不知被何人惊惶打翻。
“小姐,大事不好了!”
婢女满面泪痕,惊慌失措地闯进来。
“小姐,叛军……入城了!”
睡梦戛然而止,这一声惊呼,令床榻上浅睡的少女支起上半身。那一袭乌发顿然如瀑般倾泻而下,卫嫱娇靥上尚带着恍惚,愣愣地同婢女打着手势。
“叛军?”
“哪里来的叛军?”
手方一放下,卫嫱仿若预测到什么般,一股隐隐的恐慌之感弥漫上心头。
不知从何时起,京中有流言纷纷,道三年前亡故的三皇子“死而复生”,更有甚者,竟言三皇子殿下李彻在西北起兵,剑指皇都。
那九龙宝座,原是他的囊中物。
如若不是当年,那一杯不设防的毒酒……
“轰隆”一声,天际有闪电劈过,横贯夜空,亦将人面上劈得一片亮白。
床头桌上那樽玉佛像闪了一闪。
只一瞬间,她忆起三年前那个雨夜。
卫嫱记得那是个冬日,北风猎猎,她端着二皇子递来的毒酒,于一个深夜,孤身走进李彻的寝殿。
少年立于桌案之前,身形颀长落拓。他本不知是在忙些什么,见卫嫱走来,立马停下手中动作。
“你来啦。”
李彻原本清淡的面颊上浮现一抹笑意。
“阿嫱今日怎来送酒?”往日她送的都是冰糖雪梨粥。
卫嫱已记不清,当初自己是如何笨拙地对着他扯谎,只记得那夜雨声淅沥,一下又一下拍打着竹帘。她鬓发上雨滴尚未干,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呆呆地跪在李彻脚边。
“咣当”一声酒杯坠地,杯盏碎了在周遭,剩下半杯酒水,落了一地的晶莹。
犹如皎皎明月,摔碎于地。
映衬出卫嫱那张满是震惊的脸。
“彻哥哥……阿彻哥哥……”
“我……”
少年骨节分明的手紧攥住她的袖口,待反应过来这是杯毒酒后,卫嫱心中愈发害怕,忙不迭慌张地将他的手挥开。
李彻的手指很冷,冷得她浑身一颤。卫嫱忍着泪,浑身害怕到颤抖。
二皇子与她道,若想救阿爹与兄长,便将这杯酒端入李彻的寝殿。只是她未想到,这一杯竟是毒酒。
酒杯坠地,月华也散落在周遭。温暖的寝殿之中,似乎残存着淡淡的梨花香。
卫嫱瑟缩着双肩,一根根掰开他攥住自己裙角的手指。
对不住。
她一声声说着,对不住,阿彻哥哥。
他的呼吸愈发困难。
月色如水,漫过雕刻着梨花的窗台。卫嫱面色灰白地跪坐在李彻脚边,夜雨声落在耳边,雨点敲打着她的心房。
将李彻最后一根手指用力掰开时,对方似乎张了张嘴。
少年气息未绝,唇边尽是鲜血。那双眼底带着许多困惑,像是想要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亲手喂他这一杯毒酒。
为什么要如此狠心地,置他与死地。
身为太傅之女,她自幼与李彻相识。在旁人看来,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卫嫱甚至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那一份独有的绵绵情谊。
她喜欢蝴蝶,李彻便在琅月宫后院种了满院的花。她天生浅瞳被视为不祥之物,李彻便护在她身前,严词厉色,为她责罚了大半个宫的宫人。
直到很久以后,卫嫱才知晓。
李彻不喜花粉,若长久处之,身上便会起红疹。
那夜大雨滂沱,十三岁的卫嫱跪坐在一片阴影里,边流泪边朝他摇头。
她看着,李彻并未开口唤人。
对方用往日里那双满是温柔与宠溺的眼,神色复杂地盯了她许久。
那日北风呼号,犹如今夜。
卫嫱回过神,只见天际寒芒一片。清泠泠横劈于床头的玉佛上,折射出令人心悸的光芒。
这些年,她以为李彻死了。
之后又未有多久,二皇子的另一杯毒酒,夺去了卫嫱全部言语,让她成为了一个哑巴。
或是忏悔,或是愧疚,或是以求心安。卫嫱于床头供奉了一樽玉佛,神佛低眉,面容慈善,那一双眼静静注视着她。
仿若千般罪行在这样的目光中,都得到宽恕。
猎猎的风声吹得她面色发寒,卫嫱垂下眼帘,在心中祈祷:
莫是他,叛军千万莫要是他。
如若他起兵打入皇都,倘若这一战他胜了……
她打了个寒颤,不敢再往下去想。
然,婢女青桃的话语在雨声中显得尤为可怖,也尤为清晰。
青桃颤抖着声回应道:
“二小姐,西……西北,是西北。”
“轰隆”又一道惊雷,却将周遭劈打得一瞬无声。少女蜷长的眼睫轻微一颤,面上一片雪白。
然,根本不容得她反应,院外已传来嘈杂之声。
“打进来了!叛军打入京都了!”
“叛贼李彻领兵,打入皇城——”
星火点点,风雨似要破门而入。
兵戈之声裹挟着寒风凄雨,犹如一把锐利的尖刀,将夜色中的皇城扯出一个巨大的口子。
满城风雨倒灌进来,支摘窗的牖页也被风声吹打得砰砰直响。
电光晃耀,晦雨弥天。
骤冷的长风一如她摇晃的心事,波澜不平。
待李彻攻入皇都,卫府岌岌可危。
青桃早已经慌了神。
卫嫱佯作镇定,先是命青桃取来一件低调的布衣,又往脸上涂抹了些碳灰。眼下之计,便是先带上众人趁乱离开卫府,待撑到兄长自珵州归京,再与他商议下一步的打算。
就在刚刚,她算好了时辰——李彻是自西门打入皇都的,而卫府恰在京城之东北,只要她动作快些……
琉璃瓦上,风雨如磐。飞檐上挂着浓黑的残云,这一场变乱便要倾轧下来。
青桃跟着她,虽心有惴惴,却不敢多言。
正思量着,一行人越过青梨苑,再往前便是与前院相通的垂花拱门。知晓她喜欢梨花,兄长于卫府之中种满了梨树,而今梨花未开,树枝却被风霜捶打得些许破败。
便就在卫嫱欲迈过垂花门时,自府门那头忽尔传来兵戈之声。
卫嫱脚下一顿,侧耳。
[什么声音?]
似有铁骑踏踏,不知从何处而来。
突然,有人哭嚎出来。
“不好了!叛军将宅子全都包围起来,我们、我们一个都出不去了!”
此一声,彻底让众人都失了主心骨。黑云压城,顷刻之间,门外的叛军更是将整个卫府围了个水泄不通。
整个卫府陷入绝望。
“三殿下有令——”
马背之上,有人厉声道,“卫府上下,皆须安分本分,不得擅出。若有违令私逃者——”
“杀无赦!”
这一声令下,叛军登即如一张大网,朝着卫府裹挟而来。
寸寸逼近之时,似乎在刻意搜寻着什么人。
密不透风的浓云,使得人连大气也不敢出,卫嫱躲在长亭之侧,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她要逃。
她要逃去珵州找兄长,她不能在此刻被李彻抓住,她……
青桃也护着她,悄声:“小姐,这边。”
大雨倾盆,砸落在卫嫱裙角之处。她的鞋袜尽湿,却不敢有分毫的停歇与喘息。
即在拐过那湿漉漉的院墙时——
猛然一道寒光袭来,利剑迅猛,便要直取她命门!
几乎是同一时刻,又是一道箭矢破空,“唰”地一声,两道寒光相撞,利器铮然一声,坠于卫嫱脚步之前。
距离她仅半步之遥。
“三殿下!”
“参拜三殿下!”
周遭冷不丁响起跪拜之声,那一句“三殿下”,犹若横空生来的一根刺,狠狠扎进卫嫱心里。
她脚步顿住,苍白着一张脸,身上僵得厉害。
“啪嗒,啪嗒。”
雨滴声不知衬着何人的步子,寸寸朝她逼近。
那步履极轻,似是踩着水,步步迈过地上的水洼。今夜的月色不甚皎洁明亮,灰蒙蒙的一层光,蒙在卫嫱后背上。
后颈生起凉意,卫嫱紧抿着冻得发紫的唇,不敢回头。
“三殿下——”
“退下。”
她屏着呼吸,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去捡掉落在地的骨伞。
夜雨湿淋淋地落在她身上,顷即间,卫嫱身前已被雨水打湿。
鬓发湿润,黏在少女发白的面颊两侧,她打着抖,敛目垂容,看着那一袭黑氅落在她身前。
再往上,是一张久违的脸。
四目相对的一瞬,卫嫱有刹那间的失神。
果然是他。
月影重叠处,男子孤身而立,他右手握着一把弓,一双眼中落着清霜,蜷长的鸦睫轻垂。
似是胜券在握的猎者,放肆地打量着自己的猎物。
半晌,卫嫱听见了他的笑声。
他说,
“卫二小姐,好久不见。”
……
卫嫱踉跄着朝后倒退了两步。
夜雨弥天,李彻身后亦有夜潮翻涌。暗涌的波澜将整座卫府包裹,亦将她单薄的身躯裹挟。
她在害怕。
她紧咬着下唇,明显是在害怕“死而复生”的李彻。
男人将长弓递给身后随从,仅又对她扫视了一眼,而后冷淡朝后吩咐:“传令下去,即刻搜查卫府前后院落,若有异状,立马上禀于本王。”
他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却带着一种上位者独有的冷漠与威严。
“尤其是青梨苑。”
淡淡的一声,令卫嫱的眼皮跳了跳。
她仰起头,尽量克制着双手的颤抖。另一侧,有人高声问道:“敢问三殿下,为何要搜查卫府?”
如今他乃叛军,他才是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又有何资格前来搜查卫府?
“为何?”
李彻冷笑了声。
“因为本王想。”
“本王的人已打入皇宫,日升之刻,便是这天下易主之时。本王听闻,卫府包藏祸心。卫二小姐,你说,本王该不该带兵扫清前朝余孽?”
他垂眸,目光饶有兴致地划过她挂满雨珠的面颊,那一双凌厉的凤眸中,挟带着几分玩味。
他这是在报复。
他这是赤.裸.裸的报复!
大雨倾盆而下,卫嫱未打伞,单薄的身子任由雨水冲刷着,不知是因为寒冷,或是因为惧怕,少女双肩不受控制地颤抖。
她紧咬着发白的下唇,抬起被雨水淋湿的脸。
他今日,带着兵马前来,便是要在荣登大宝之前,血洗卫府。
李彻撑着伞,衣肩平整,未染任何霜寒。
“卫嫱,看你这眼神,似是在哀求本王。”
“想要本王放卫家一马么?”
“好啊。”
他唇角噙着笑。
那笑意森森,分毫不达眼底。
“卫二小姐打算如何求本王?”
仅愣了一瞬间,卫嫱心一横,双膝磕地,伏身于一袭氅衣的男人面前跪下来。
少女乌发披肩,面容低垂着,原本清澈明亮的一双杏眸,此刻正带着几分前所未有哀色。
夜光渺渺,雨水清冷。
男人垂眸,于她身前不远处,居高临下地睨着她。
因是低着头,卫嫱根本看不清对方面上神色。她只觉得今夜的庭风格外冷,冷得像是一柄锋利的尖刀,拂于她面上。
一寸一寸,割刮着她全部的尊严。
卫嫱伏身,浑身湿透,长跪于夜雨中。
她本就身子弱,畏冷,如今手脚冰冷,近乎于晕厥。
从前,她是娇生惯养的卫家小姐,无论府里还是府外,卫嫱从未受过半分委屈。平常惹出什么事,大错小错,皆由兄长替她抗下。
即便,她只是卫家的养女。
爹爹呵护,兄长怜爱,仆从敬畏。
还有……
琅月宫那位明目张胆的偏宠。
自双膝传来隐隐的刺痛感,冷意从膝盖处袭来,令她双腿冻得僵疼。
卫嫱紧咬着牙关,泪水在眼眶之中打转。
耳畔两侧是锐利的夜风,她的身形无处可藏,溽湿的袖摆,亦啪嗒嗒朝下滴着水。
她听见李彻的脚步声。
一步,两步。
他行至她身前,忽然伸出手。
脖颈上一重,从前对她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的男人,如今竟伸手掐住了她的细颈。李彻不知使了多少分力,只见其手背青筋爆出,那虎口紧贴着她的下颌。
竟直接将她掐着自地上捞了起来!
卫嫱呼吸一滞,下一刻已足尖点地。
对方袖口终于沾染了雨珠,冰冷冷地拍打在她面上,她艰难地张了张嘴唇。
“殿……殿下……”
她未发出任何声音。
李彻的身形倾压下来。
如同夜雾沉沉的天色,倾覆,压迫。李彻的大手攥握住她的腰身,登即将她逼至墙角。
后背狠狠撞上冰凉的墙壁,她尚未来得及呼吸,唇上忽然覆下一物。
周遭似响起一阵倒吸之声,围观兵卒赶忙低下头,不敢看他们。
少女惊恐抬眸,杏目圆瞪。
李彻一手掐住她的脖子,伏身凶狠咬住她的唇。
与其说这是一个吻,倒不若讲,这是一个满带着占.有与侵.略的啮咬。男人的牙齿凶恶咬过她的唇.舌,不过顷刻,便掠夺去她尽数呼吸。
她下意识想要反抗。
他这是放肆,是侵.犯。
“啪!”
清亮一道耳光声。
周遭又一阵吸气。
李彻的脸被扇歪了些,片刻后,他回过神,手指慢条斯理地拭了拭嘴角。
旋即,男人的眼底闪过一丝凶恶。
李彻勾起唇,阴恻恻沉声:
“卫二小姐,本王看你真是活够了。”
忽尔又有暴雨倾盆而下,她的身形被人打横抱起,径直朝内院而去。
[三殿下,李彻——李彻!]
[你……你放肆!李彻!!]
“嘭”地一声,李彻踹开她闺房的房门。
这从未有外男踏足之地,就这般轻而易举地被他侵.占。
她用手推了对方一把:“你不可……”
尚未来得及反抗,她被男人扔在榻上,床帘掀扯。
支摘窗被冷风吹掀,夜雨倒灌,连带着院外呼啦啦的风声。外间的将士屏息凝神,皆知晓二人在屋中行何事,却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出。
李彻扯去外氅,一手自腰际抽出一根军鞭。
他的力道极大,立在榻边,极轻松地用鞭子将她的双手绑起来。
军鞭粗糙,勒得卫嫱手腕生疼。男人于她身侧,阴沉道:
“卫二小姐若是再动,本王不介意用军中那些手段来对付女人。”
卫嫱拼命摇着头,又似乎在低声下气地哀求。可是她的喉咙里如堵住了棉花,少女发不出来任何声音,只能用通红的一双眼望向他。
[李彻,李彻,你放过我……]
旧事如潮,同夜风一道迎面。
“卫嫱。”
对方并没有发现她的异样,他闭上眼,无端笑了声,“这是你欠我的。”
她如一头倔强的小鹿,泪眼婆娑,清亮的杏眸满带着惊惧。
听了这一声,她的心头又笼罩上莫大的耻辱感。
羞愤欲死。
一瞬间,一个绝望的念头自她脑海中闪过。
除非她死……
似乎察觉出她的想法,李彻动作一顿。他缓缓支起上半身,凝望向少女眼底颤抖的光影。
月光在她清澈的瞳眸中,像是碎掉的菱镜。
“卫嫱,你这样看着本王,是想要求死么?”
“好啊。”
清凌凌一声,李彻径直截断了她的思绪。
“卫二小姐是想咬舌,割腕,还是撞墙?”
正说着,男人冷漠丢来一物。
卫嫱定睛一看,
正是一把小巧的尖刀。
刀未出鞘。
卫嫱愣了一瞬,而后抬起头。
她一双眼里凝结着些许水雾,夜光掠过,月影摇晃,似有什么东西于她眸间颤了一颤。
下一刻,她忍住眼底晶莹,在男人的目光下握住刀柄。
刀柄很凉。
他的目光更是冰凉如水,冷幽幽落在她身上。
对方的眼神里没有分毫感情,仿若她只是个极为无关紧要的人。
她或生,或死。
都无法牵动他眼底的波澜。
卫嫱将刀架于脖颈,绝望闭眼。
两只手因是被军鞭绑着,卫嫱架刀的动作有些困难,脖颈转瞬覆上一层冰凉,她深吸一口气,手指一寸寸收紧。
她的右手开始颤抖。
今夜的雨仍未停。
风声小了些,愈烈的是越发作响的雨势,犹如倒灌的天泉,将天地间冲刷得一片银白而干净。
听着雨声,卫嫱脑海中忽地闪过爹爹与阿兄的脸。
她只是爹爹收养的孤女,身上并未流着卫家的血。旁人却常常说,无论是样貌或是性情,她与兄长都是极像的。
就好似,他们生来就该是兄妹。
阿兄离开京都那日,卫嫱依依不舍,缠了他许久。前去珵州的马车便停在卫府前,兄长无奈弯身,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发顶。
清俊儒雅的男子,唇角也带着不舍的笑意,温声哄她道:
“阿嫱乖,在府中等兄长归来。”
她不能死。
卫嫱握着刀柄的手一顿,强烈的求生欲自心底燃烧起来。
蜷长的睫羽翕然一颤,卫嫱抬起一双眸,四目猝不及防地相撞,缓神之际,她想要在李彻眼底看出半分不同的情绪。
然,男子一双凤眸冷彻,狭长的眼尾只向上微挑着,漆黑的眸底不带有任何异样。
寒风吹拂,对方反倒是饶有兴致,似乎在等待着她下一步的动作。
“怎么,又不想死了?”
李彻望向她僵硬的右手。
冷风扑闪在刀光之上,月色入户,折射出清冷而刺目的光芒。
见状,男人唇角缓缓勾起,他噙着哂笑,忽尔一冷声:
“卫嫱,装什么呢。”
那声音太过冰冷。
卫嫱一怔。
转瞬之际,他迎上前来。
虽是踏着刀光剑影而来,李彻身上却没有沾染半分血腥气。相反的,男人身上倒是带着几分清冽的冷香。
淡淡的香气与李彻的身形一同逼近,顿然将卫嫱周身环绕。少女忍不住朝后缩了缩身子,后背紧贴上冰冷的床栏。
李彻冷眼看着她,话语之间只剩下嘲弄与冷漠:
“这么多年了,你还跟从前一样虚伪。”
令人生厌。
果不其然,听了这话,少女面色一僵。
灰白的面庞上是一双萦着薄雾的眸,她的鬓发未干,就这样黏在耳边。因是淋了一场大雨,卫嫱身上衣衫湿透,素色的里衣紧贴于身,恰恰勾勒出少女玲珑曼妙的身形。
她紧咬着牙关,努力抑制情绪的涌动。
即便如此,泪水依旧十分没有出息的涌上眼眶,她红着眼,避开身前之人的视线。
是啊,她不想死。
更不敢死。
她还未见到兄长,她还未等到兄长归京。如今即便身死,死在李彻身前,最多不过是让这叛乱夜徒增一具尸骨。
一句旁人根本不在意的尸骨。
还有,她怕疼。
冷冰冰的刀光,让人望之生畏。
而如今,身前男人的目光更像是一柄刀,一柄锐利的、无情的尖刀,于这个大雨瓢泼的冬夜,划开她全部的尊严。
“为何不说话?”
卫嫱泪花闪烁,眼底一片晶莹。
右手僵硬地攥着刀柄,冷到连膝盖都在打着抖。
“卫二小姐,是本王的这些话刺痛到你了么?”
下颌处忽然一紧,卫嫱的下巴被人抬起。
对方修长的手指于其上摩挲着,指尖轻轻,慢条斯理划过她的肌肤。
紧接着,男人的手指落在她的锁骨上。
卫嫱浑身湿透了,她伏跪于榻,被李彻抬着脸,呼吸起伏不平。
“啪嗒”一声,她手中的尖刀被人打落在地。登时,少女伏下身去,只余一张雪白惊惶的脸颊抬着,一双眼湿漉漉地望着他。
她张了张嘴唇,发出无声的哭泣。
“三殿下。”
夜潮翻涌如海,一层层衣料坠地。窸窣的声音打断她的话语,又迫使她张了张嘴唇。
“求求你……”
放过她。
再或者,哪怕用其他的方式来折磨她。
李彻未听见她的声音,只当她不愿放低身段来哀求他。
是了,她曾经也是太傅千金,天之骄女。
又怎会发出如此低声下气的言语?
卫嫱的唇被人堵住,千般话语吞咽入腹,又被他的唇齿咬烂,啮成絮絮的啜泣。
泪水自她面颊滑落,埋藏入湿润的发隙间。
李彻的手指亦埋入她的发隙。
对方并未解开她手腕上的军鞭,鞭身寸寸磨着她手腕的肌肤,磨出一道红痕。长夜漫漫,他倾下身,仿若在她耳边低语:
当初你喂我那一杯毒酒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天这一日。
他率兵打入皇城,又在破城而入之时,单独率领一队兵马,第一件事便是去了当初令他魂牵梦萦的卫家。
从前,这是他千方百计找借口,想要靠近、却又怕唐突冒犯的地方。
如今他还活着。
叫她失望了。
男人声音低沉,萦绕在耳边,似是一张大网,将她紧紧包裹、缠绕住。
她无法逃遁,艰难呼吸。
卫嫱只用眼泪回答他。
手腕间的磨痛愈甚,钝钝的痛意,又在顷即间蔓延至少女周身。害怕,绝望,痛苦,耻辱……万般情绪在一瞬间犹若酒坛被打翻,氤氲着潮雾,游走在她的四肢百骸。
她拼命躲避,眼底闪烁着晶莹。对方的大手拽过她纤细的腕,硬生生将她拉扯下来,拉扯到那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少女的声音哑了。
她张开口,却发不出声,说不出话。
喉咙间的棉花似乎鼓胀起,想要发出“呜呜”的声音,却又被他的虎口死死掐断。
仅是喘.息之刻,李彻又咬上她的唇。
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
“卫嫱,这是你欠我的。”
她的眼泪滑下,湮没于未干透的发。
四年前所有的怨愆,在这一刻似乎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又似乎完全忘记了那些哀怨,心中只剩下了不绝的恨意。
只剩下冷漠。
不知过了多久,雨终于小了些。
窗外一片压抑,除了李彻,所有人都缄默着不敢出声,包括暖帐中的卫嫱。
少女面上挂着泪痕,看着他冷漠地抽身。
卫嫱蜷缩在床榻之角,两手虽被禁锢,却依旧倔强地护在胸前。她的泪已经流干了,身侧的男人慢条斯理地站起身子,将衣裳一件件重新穿得妥帖。
全程,对方的目光凝在她身上,放肆地打量着这具身体。
在先前的对峙中,被褥已被扔在地上,卫嫱无从遮掩,更无路可逃。他的目光像是熊熊炬火,烧得她五脏六腑皆生起火辣辣的烫意。
少女披散着乌发,混沌的眸间掠过一道恨意,长长的指甲嵌入掌心之中。
李彻根本不在乎她这微不足道的恨。
似是嘲弄,他轻蔑笑了笑。转瞬,门口传来一声通报:
“殿下。”
“说。”
“启禀殿下,属下在前厅搜寻到了一物。”
李彻轻飘飘扫了她一眼,而后起身,自房门口取过。
隔着一道屏风,卫嫱看见他身影掠过,待对方再来到床前时,手上多了一样东西。
——阿嫱亲启。
她下意识支起上半身。
是兄长寄来的信!
原本黯淡无光的一双眸,见之立马亮了亮,她只看着李彻手里攥着兄长的家信,缓步重新走回榻边。
【小妹,展信佳。】
只瞥了一眼,男人便转过身,他捏着信件将其置于床边银釭之上。信纸登即被烛火点燃,看得卫嫱欲想惊呼。
她扑上来,竟直接徒手去抢。
手腕被军鞭桎梏,她的动作略有些笨拙,像一只莽撞的鹿。李彻蹙眉,眼疾手快地将她扯开。
“你做什么?”
火光落入卫嫱眼底,映出她眸底的晶莹。
李彻低下头,匆匆看了她一眼——方才她冲过来得着实莽撞,右手竟不管不顾地捞入火光中,如今手指有些烫伤。
虽如此,她却浑然不觉得疼痛,一双眼紧盯着他手中信札。
阿,阿兄……
看出她眼底神色,李彻面色微微一变。
然,那情绪仅掠过一瞬,转瞬即逝。
李彻一手扯住她,另一只手再度将信纸贴近那银釭。
信纸遇火,燃烧出一阵火焰,卫嫱听着那呲嗞的声响,眼睁睁看着,
兄长寄给她的信件就这般一点点燃成灰烬。
拍去手中积灰,李彻轻悠悠丢下一件雪白的衫。
卫嫱这才反应过来遮挡身子。
手指被火焰灼得疼痛,愈发痛的是她酸涩的身体。见状,身前男人冷嗤了声。他唇角边似带着嘲弄,清冷矜贵的眉眼之中,却又写着几分餍足。
门外有将士前来禀报军况。
彼时李彻恰恰重新系好衣带,闻声,他连头都不回,抬步走入门外那一帘风雨中。
今夜山呼海啸,风声未曾停歇。
李彻离开时的风带走最后一点烛光,自他走后,卫嫱周遭又陷入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她身上披着那件单薄的衫,手上军鞭还未被解开,一个人抱臂坐在床边,呆呆发愣了许久。
久到她听见门外李彻撤兵的声音。
兵戈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大雨湿淋淋地朝下落,风雨声连绵不绝。
她听见门外有人犹豫道:“屋里……屋里头那名姑娘怎么办?”
“要不,将她带进宫里头去?”
“可是……三殿下他也没说要……”
再往后的话卫嫱听不真切了。
回过神,少女低下头,接着月光看见身上布满的红痕。
今夜雨势滔滔,当下月色却十分清亮。如银纱一般的光亮穿牖而入,映照出她身上凌乱的印痕,以及床榻之上,那一点氤氲开的、鲜红的血迹。
卫嫱再也忍不住,脸颊埋入双臂中,悲恸大哭。
似乎是听见了屋内的响动,门外的将士终于安静了些。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也哭累了,余光瞥见一直绑在手腕上的鞭绳。
李彻离开时,并没有解开绑住她手腕的军鞭。
她胡乱抹了一把泪,而后抽泣着低下头,一点一点,将手上的军鞭用牙齿咬开。
地面覆着月纱,凉得瘆人。
卫嫱踩在地上,捡起坠了一地的衣衫,默不作声地、一件件穿好。
里衣,袄裙,外衫,鞋袜。
重新穿妥帖,她坐回床边,像一个破布娃娃般倚靠着床栏,愣愣地发着呆。
终于,有人敲了敲门。
“卫姑娘。”
士卒一身银甲,在房门外唤她,“卫姑娘,请上马车。”
令对方意外的是,屋内的姑娘并没有拒绝,更没有问去哪儿。
她浑浑噩噩,犹如一具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
庭院外很冷。
她受了寒,还淋了雨,如今面色更是潮.红。
马车缓缓驶动,卫嫱昏昏沉沉,脑海中忽尔闪过一些零碎的片段。
年幼时,她曾发过一场高烧,半只脚迈进了鬼门关,急坏了爹爹和兄长。
待她醒来时,发现右手手腕处系着一根红绳,绳上绑了一块玉,一块通体莹白的暖玉。
后来卫嫱才知道,这那高高在上的三皇子,一步一叩,跪了整整九十九阶,于菩提神像前为她求得的一块护身玉。
那天晚上,李彻淋了雨,也生了一场病。
所幸病情并不严重,他并无大碍,只是落下了些病根,咳嗽了许久。
那段日子,卫嫱便一直为他炖冰糖雪梨粥。
当她将汤勺送至少年唇边,对方明明苍白着一张脸,却还同她嘴硬。
“我主要是前去拜拜神明,顺便给你求得这枚护身玉,没想到还真有用。”
少年李彻坐直了身子,凑上前,勾了勾她的手指。
“阿嫱,以后你这条命就是我的喽!”
他的手指很凉,轻轻擦过她的肌肤,却让她面上生烫。
小姑娘脸一下红了,“三殿下胡说什么。”
风铃响动,锦衣玉带的少年郎轻笑出声:“哪里是在胡说,我不管,阿嫱,你这条命便是我的。从此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
说到这儿,少年一顿,忽然开始不自然地咳嗽起来。
卫嫱坐在一侧,看他咳嗽得脸上红一阵青一阵。她只低着头,不敢再多言语。
少年人的心思总是很难猜测。
像是捉不住的一阵风,穿堂而过,唯余风铃在心中响动,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心窗。
卫嫱记得,那时候的李彻,突然问了她一句话:
“阿嫱,你喜欢皇宫吗?”
没来由的发问,引得小姑娘一怔,她抬起一双清澈的杏眸,不解地凝望向身前之人。
马车之外,北风怒号,大雨冲刷着整座皇城,前朝的沉疴仿若要在这一场夜雨中被洗刷干净。
马车摇晃着,卫嫱脑袋昏昏沉沉。
她耳边回荡着从前那句稚嫩的、小心的、满带着试探的问询。
“阿嫱,你喜欢皇宫吗?”
皇宫。
她喜欢吗?
这一回,不容她任何回答的机会。
马车渐缓,越过堆积如山的尸骨。
不容反抗地,她就这般被抬入朱红色的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