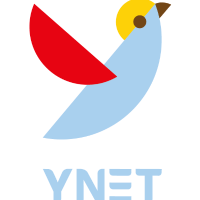徐皓峰


主题:红色电影里的传统世界
时间:2022年11月16日21:30-23:30
地点:网上直播
嘉宾:徐皓峰 作家、导演
史航 编剧
叶三 媒体人
蒋璐霞 演员
看老电影如晤故人
史航:徐皓峰的《光幻中的论语——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这本书,在我心目中是个“坚果”,就是有很硬的壳的,像核桃、胡桃那种坚果,不是直接的核桃仁、胡桃仁。光看这书的封面和目录,可能只知道他要谈“十七年”(1949年-1956年)时期那些主旋律红色电影,想不到它里面是这么生动、这么深入浅出的内容。所以今天要把这个“坚果”砸开一点,让更多人知道这本书可能跟自己有点关系,有点意思。
先严肃地问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徐皓峰:我早年学美术,有一个老师叫许云龙,他当年带我们这班,最看好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我。到我们过了40岁,这个老师开始跟我们俩兄弟相称。等于原来都是小孩,跟着一个40岁的老师,后来老师步入老年,就跟学生兄弟相称。这其实是明清书院的一个传统。我这代人基本不知道书院是怎么回事,但就发现生活里边还有它。而且随着我父亲、我爷爷辈这一批中国式的男女逐渐谢世,就剩下我这一代人。我这拨人从小西化,说话的方式、仪态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看老电影其实是满足我童年、少年时代的一个回忆,等于原来我眼前都是那样一些人,后来生活里见不着了,就有的时候看看老电影。这是一个缘起。
史航:确实,我因为你这本书又看起一些老电影的时候,也偶尔会想起以前什么样,比如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在包场的时候怎么看这个电影,当时感兴趣哪个坏蛋说的哪句好像很坏的话,大家就学这句话,整个电影都忘了。但现在又看见整个电影的时候是一种沉浸。这两天我在手机上列了一个文件,叫《可惜皓峰没讲》,比如说《林海雪原》《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战上海》,就列了好多。我想的是书中讲这8部电影我都拉完片之后,我不管皓峰讲没讲,我很有兴趣再看看那些老电影。我记得李雪健老师在《少帅》中演老帅张作霖说的那句——“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其实我们说这个红色电影的传统世界,也是要讲讲不同人理解的人情世故的东西。
叶三: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六经注我”的这种写法,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其实是带着很多疑问去读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电影的文脉它到底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到现在还存在不存在?那些人——过去的人,过去的观众,过去的导演,过去的演员——是怎样生活的?过去的观众是怎样去理解这些作品的?这些作品是怎样和他们的生活发生关系的?这些其实是我最近这一两年在想的问题。它跟创作有关,也跟接收有关。还有一个更形而上的问题,我怎么样从其他人的创作中去吸收养料,去解决我目前面临的精神问题?
这一两年是非常明显的,我的知识结构、我所有对世界的理解,已经不足以去对付现实生活给我的压力和困扰。其实上一次跟皓峰导演聊他说了一些,他说他写这本书,一部分也在解决中年危机。我觉得有时候人到中年,是会有这种往回看、再去重新建设自己后方的冲动。这一两年我在读的书、在看的电影,都是大概10年前甚至20年前已经看过的东西。所以这本书里的老电影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那种很纯净的遥远的眺望感
叶三:书中还有关于电影理论、关于电影本身,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八卦,包括塔可夫斯基和《小兵张嘎》,这两个东西居然能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些就是徐老师平常的积累。
我读的第一本皓峰老师的书是《刀与星辰》,第一感觉很惊艳,之前从来没有读过那样的影评。但读到后面就觉得徐老师是不是写飞了,就不太跟得上。而这本《光幻中的论语》没有这个问题,它是很渐进的,我能够看到作者他的结构、他的思维在慢慢一步一步纵深,是一个很理性的组织方式。我现在还在追皓峰老师在《上海文学》上的专栏《红楼梦中的导演课》,那个我也特别喜欢。
史航:对,皓峰在《上海文学》那个专栏,导致我哥要到处去找报刊亭。但即使在我的故乡长春也基本没有报刊亭了,他就去邮局找这个杂志。后来还真都找到了,他又拿手机一篇篇拍下来发给我。就是我们重新因为他的专栏开始关注一本杂志,我觉得是很奇妙的缘分。
刚才有一个网友说他最近被隔离,临走就抓了一本《刀与星辰》。如果《刀与星辰》读完隔离还没有结束,他可以跟着看这个《光幻中的论语》。
我看这本书很大乐趣在于弥补了一个遗憾——我其实没有机会听多少皓峰的课。我就听过两堂,去他们电影学院。一次是我去太晚了,我在门外听的,我就没见着他,因为人太多。那次他讲的是《邦妮和克莱德》。还有一次我特别早去占教室,中午就去,带着吃的,第一个进的。结果下午来的人太多,把我挤到墙角了。完了皓峰在另外一个墙角,在那儿讲,我们俩中间隔着投影,讲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杀手里昂》)。这是我听的两次,但是我都不满足,在于他讲的都是外国电影,虽然有好多东西我现在还记得。
我其实特别想听皓峰讲华语电影,因为它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祖国的影片,它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外国电影比如你讲《教父》,我肯定不会认为小时候我们长春街头巷尾有什么人跟教父有关系。但是你讲任何一个华语电影,我想想“哎,小时候我们邻居好像也有个这样的人,或他说过这样的话”,就刨根问底华语片是能刨出来东西的,但外国片子你只能是眺望。
蒋璐霞:年龄问题,《光幻中的论语》讲的8部电影确实离我太久远,印象中我只在儿时听过《小兵张嘎》的名字。读完书我立马去做了功课,看了《小兵张嘎》《革命家庭》《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前看电影,我只能解读电影的表面,比如看演员怎么演戏、动作导演怎么去设计武打动作。但是看皓峰导演的书,完全已经是跳出电影本身了,涉及哲学、心理、历史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读皓峰导演的书,可以收获很强大的知识补给,关于当时的文化,也关于皓峰导演自己的那个世界。
史航:听璐霞这么一说,那种很纯净的遥远的眺望感,很打动我。
突然想起不相干的一件事,有一个电影,黄建新的《埋伏》。它是一个抓坏人的电影,犯罪集团头目是已故演员牛振华演的。他最后被公安人员盯上的时候,是在一个古老的影院,他一人坐那儿看一部电影叫《英雄儿女》,看到最后他热泪盈眶,满脸是泪,完了警察慢慢围拢他,他就没有动,在那儿被抓了。就一个犯罪分子,他心目中有这么一个角落是放着《英雄儿女》。我们知道后来张艺谋也拍过跟《英雄儿女》有关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有很多人,看电影的跟放电影的人。所以老电影,也许它每次被重温,就能给别人带来收获。《光幻中的论语》是一本讲老电影的书,但恰恰是写这书的也不老,看这书的也不老,彼此之间荡漾着很多情绪的东西。
感觉被爱的小孩儿记忆力会好
史航:为什么选这几部片子?因为其实每一个可能都能找出另一个同类项,比如说,你没有用《祝福》,你用《林家铺子》。
徐皓峰:因为从一个导演的角度,他看一部电影其实更专注导演有没有风格,还有电影本身的这些镜头组接、剧作有没有达到水准线之上。像水华导演、崔嵬导演,他们的视听语言都是比较好的,在那个时代。所以我研究那个时代的电影就先挑这个。其间为决定到底写哪一部,也重看了一些电影,确实感觉到每一个时代其实懂视听语言的导演并不太多,大概是4%-6%的一个比例,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好莱坞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先挑对电影本质有理解的这些导演的片子来讲。
史航:确实你这8部电影中,三部是水华导的,《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有三部是孙道临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家庭》和《早春二月》。每一个统计起来,也是挺好玩的事儿。
我印象很深的,你书中夹杂两个非常早期的影评经验。多早期呢?应该是你小学或者学龄前的那种。一个说《革命家庭》,于蓝演女主角母亲,她在父亲被捕后仓促找上了一个党组织的人。但这个人演戏比较浮夸,跟孙道临、跟同剧组其他人不太像,怎么抽烟,怎么喷烟,怎么拧那个劲儿,就那种演法相对生硬一点。你说小时候看就特别紧张,怀疑他是个叛徒或者特务,或者是个人贩子,可能会把母亲给出卖了。
还有一个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演的李侠要从延安离开,去大上海做地下工作。送行的人中有一个他的同事,送行的背影是两手插兜。一般小孩会觉得两手插兜不是个正经的大人,因而觉得他是不是一个特务,正经的共产党人怎么两手插兜?但其实人家也不是,你后面解释了。
这俩事我特别感兴趣,就你记得自己小时候可能偏执、可能幼稚、可能标签化的一个概念。我们也会有、也会记得,但你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你能分析出小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这是特别重要的。
徐皓峰:我们当时的小学教育是每周要看一次电影。其实这个看电影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幼儿园也是基本一周到两周就要看电影。
我的童年记忆为什么那么深?其实也是小学的时候遇到两个好老师,后来都是实验教学的名师。一个叫赵新春,赵老师的特点是他不搞“题海战术”,他把一般人很忽视的课外兴趣小组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上完主课就鼓励小孩去画画、搞音乐、做手工。没想到小孩玩了这些之后,他的数学和语文自然地就很好,它是“功夫在诗外”。另外一个王家贤老师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推崇爱的教育,修炼得自己有双大慈大悲的眼睛。所有的小孩上他的课都觉得他很爱自己,全班笼罩在慈悲的氛围里。他也不玩“题海战术”,但是小孩觉得自己受关爱,他的智商就高,他文化课自然就好。
王家贤老师,我年过半百之后去看他,当年我给他写的字、送给他的照片,他还都留着。他这种心理学的爱的教育实践,其实是临近退休之前他搞的实验,他也就是搞了几个班。那几个班有的同学都五六十岁了,还一直有几个节假日都待在他家,挺大岁数了,今天来了明天还来,一待待一天。可能是小的时候王老师给过他们爱吧,这种爱成年之后在别人那儿得不到,所以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跟小孩一样,节假日赖在老师家,而且是一大批。在这种小学教育里,小孩他精神上很宽松,所以他记忆力就很好。
人年轻的时候得多磕头、多拜老师
史航:你又做影评又讲电影,当你看别人拍的一些电影觉得拍得轻重缓急不对、层次分寸不对,当你看一些电影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仍需再忍”的时候,你心理活动都什么样?不是在拉片课上,可能是在一些首映礼上。
徐皓峰: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如此庸俗呢?其实它跟咱们的大脑是对应的,就是我们自己平时个人的好主意也不多。一天里边其实咱们大多数的想法也都很庸俗,包括写作也是。比如我工作时长今天有6个小时,这6个小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平庸的想法,好的想法可能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上电影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就得面对大量烂片,因为其实每一年好电影没有几部,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你一年级必须要有很多的量去看。那时候我们老师就教给我们,你在电影院里就边看边改,你意识到这个地方烂了,其实对你是好事,说明你在进步。然后脑子里你就想,要把它怎样它就不烂了。所以我们学电影,烂片是很好的教材,看烂片的时候你才会动脑子。看好电影的时候更多是它一下把你抓住了,你就没有动脑子的风险了。只有好电影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把你玩进它的境界里去。
史航:明白,皓峰的回答就是他没有像我这样庸俗地有任何心理反应、生理反应,人就进入了一个紧张缜密的批改作业的过程,这个我完全理解。
蒋璐霞:我听说皓峰老师是过目不忘地读书。想问这么海量的知识储备是如何做到的。
徐皓峰:其实我写《光幻中的论语》还是有“口传”的。一般做文章,为了让你阅读或者为了卖书,他是一定要娓娓道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把重点告诉你。“口传”就不一样了。我当年进入《论语》是找一个老师跟他学别的,当时30多岁,老师一看我对传统儒家这块儿非常含糊,“这不行,我得给你讲讲。你把这个理顺了之后,你才能再学我的东西”。我说“哎呀,那我得看些书”,“我直接告诉你就完了,你就别找书看了”。所以后来就到他家去,他就讲儒家怎么回事。
而他好多“口传”的东西得来,其实是在年轻的时候陪着自己的老师,住在马一浮家。马一浮是民国儒家的代表人物。等于是听马一浮自己的子侄、学生聊,因为他晚辈人嘛,马一浮肯定不会给他讲的。他就是在人家里待着聊着,然后得了点“口传”,这事其实就通了。后来就跟我这样讲,我当时听他说一些事儿,其实也没看那些书。我是为了写《光幻中的论语》,把我听闻的这些东西再去找那些人的原著给它对上。所以这学习起来就快捷、占便宜。
所以年轻的时候得多磕头、多拜老师,这样能缩短你学习的时间。
你看李连杰,他年轻的时候五六年时间拜了七十几个老师。不单是竞争体育类的,江湖的东西、军营的东西、特种兵的东西,他都会。他为什么行?老师要是不想教你,让你正经去学,那每一个相当于都是一个大学四年。如果他真想教,“我把这个要点告诉你,你自己去修行就完了”。武术界是这样,其实读书人也是这样。有些读书人说“我一辈子拜了200多个老师”,其实可能有的老师教的就是一个下午,跟他聊了两个小时天儿,要点15分钟说出来了,这样他就可以去自我学习、自我补充。
《儒林外史》才是中国电影的正脉
叶三:您从《刀与星辰》开始写中国武侠片,自己做导演拍的也是这一类电影。您之后还会一直拍这种题材吗?您觉得中国的武侠片它还会继续往下走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往下走呢?
徐皓峰:我自己再拍别的呢,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一般频率两年拍一部电影的话,我现在已经50岁了,到70岁满打满算也没多少了。所以这人老了之后,就尽量只干自己熟悉的事儿。可能这辈子就是一直拍武打片下来了,因为人生有限。你再开拓新领域,让年轻观众跟着你着急,给他们添堵,我也就不做这样的事,能把熟悉的东西再有所提升,其实也就行了。
那中国的电影传统,或者中国的正脉是什么呢?其实“四大名著”是50年代,为给中学生们做文学推荐才搞出的概念。在晚清民国其实一直是“五大名著”,还有一个《儒林外史》是跟《红楼梦》它们并列的。为什么后来不推荐这个给中学生?中学生阳光嘛,社会的黑暗面晚几年再接触。所以“四大名著”是专对中学生的。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其实一直是“五大”,就是说你成年之后一定要看《儒林外史》,它那个就是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
而且《儒林外史》这一脉,跟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导演搞的那个社会问题电影,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什么是中国的大众娱乐?中国的大众娱乐就是社会问题揭露。所以你看中国第四代导演他们拍的好多片子,80年代,可不单单是《少林寺》万人空巷,当时《邻居》《人到中年》,包括《巴山夜雨》,这些电影都是万人空巷。大家都很关注,说“你在谈现实了,你批判现实了,那我有必要进电影院看电影”。所以这个是中国电影的正脉。
其实我这一路武侠,它跟这个《儒林外史》是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为什么?发明武侠小说的这个人,平江不肖生,他在写武侠小说之前是《儒林外史》派的,他的代表作是《留东外史》,就讲中国的年轻人到日本留学,然后有种种问题。等于人家是这样一套下来。
史航:《师傅》之后你这些电影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说说,让我们期待期待的。
徐皓峰:这个都能说呀。《刀背藏身》是我完成一个心愿,因为我二姥爷的师傅尚云祥,他是把形意的刀法挑了几招教给宋哲元的抗日部队。把这个电影拍了,也是等于留一套刀法。
然后《诗眼倦天涯》是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缘分。当时我籍籍无名,赶上张国荣过世。本来从任何角度都轮不到我去评张国荣,结果当时就莫名其妙,一个电视台找我,去跟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的京剧老师和京剧戏装的化妆师一起谈张国荣。那个时候我对张国荣的认识仅止于看过他的电影,觉得是很有灵气的人,一个电影演员能演出文人气,很难得。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缘分,后来每到祭奠张国荣的日子,大陆这边都会把我当年做的对谈又拿出来一遍,所以我觉得我起码得看看这个人的视频吧。
后来网上也开始有一些视频,一看,哇,完全逆转我的旧有印象,竟然发现生活里的他好像一个武夫一样,非常果断,非常能扛事的这样一个气质。你看他的各种访谈,他竟然是一个和他电影里的形象完全相反的,甚至是身上有鲁莽和豪迈气的这么一个人。我说这个很奇特。后来选演员的时候一下碰上陈坤,我发现陈坤身上也有这种特点,就你觉得他是很灵秀、很细腻的,但是他身上又有果断、粗豪的这一面,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所以跟陈坤见了几次面之后很快就确定下来,由他来塑造刀客夜摩天。所以我也是有的时候感慨,一些你推测和想到的东西,上帝会以一个你想不到的方式让你看到。
现在正在做后期的《门前宝地》,则是基于我骨子里的摇滚基因。当年最早的摇滚乐队唐朝他们,都是在美院的教室排练,等于摇滚乐来自美院。然后我的高中同学又都是窦唯胡同里的邻居。拍《门前宝地》,我用了“野孩子”乐队的郭龙,用了“五条人”,算是我摇滚基因的显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