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孙雯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这一句,是春日里最容易被想起的古诗。不过,很多人如我,只见春韭与黄粱,不去细究整首诗中那些在时光中的离别与重聚的悲喜。
那就继续说说春日的味道吧。
1
韭菜的吃法
近日读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刷新了我对老杜这一句诗的惯常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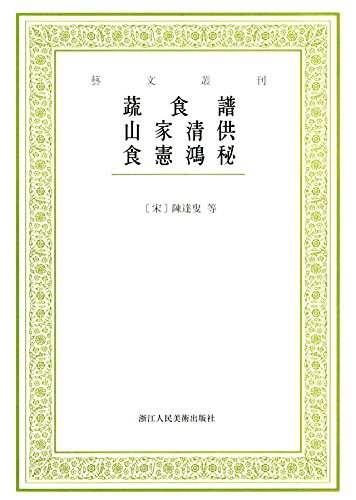
抄录一条“柳叶韭”——
杜诗“夜雨剪春韭”,世多误为剪之于畦,不知剪字极有理。盖于煠时必先齐其本,如烹薤“圆齐玉箸头”之意。乃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竖汤内,少剪其末。弃其触也,只煠其本。带性投冷水中,取出之,甚脆。然必竹刀截之。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滴醋拌食,能利小水,治淋闭。又方:采嫩柳叶少许同煠尤佳,故曰“柳叶韭”。
大意是说,杜甫以诗记下的那个夜晚,二十年未见的友人相见,他并未冒雨到畦间割韭菜,而是做了一道凉拌韭菜——将韭菜码齐整,左手执叶梢,将其焯水,取出后剪掉叶梢,过冷水,再切段,用姜丝、酱油、醋凉拌。
至于段末的疗效,只能听林洪一说罢了,且不细究。而“柳叶韭”是否是韭菜与柳叶为伍,我也有一点怀疑,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名字更像是形容春韭新发,肥嫩,阔如柳叶。
但这一道春天的时令菜,口感还是独特的,它和我的老家鲁东南一带的凉拌韭菜吃法十分类似。
小时候的记忆仍然在——韭菜用热水焯过,攥去水分,切段置于盘中,以蒜泥与酱油凉拌,讲究的撒一把虾米,再早些时候,虾米是以油条碎代之。
十几年的杭州生活,作为“葱省”来客,在市场见到肥嫩的韭菜,会买回一把,简单焯拌。其实,它算不上美味,在江南的氛围里,还有些黑暗料理的感觉,在南方的友人看来,这样的食物,简直是洪水猛兽。
看到林洪所写,才宽慰下来,原来它竟然还有些很热门的“宋韵”味道。但由此,我也知道了,宋人的生活比今天要讲究,比如,韭菜的叶梢是要裁掉的,这就是林洪诠释的“剪春韭”。确实,韭菜的“本”,水分充足,相比而言,“末”就有些燥涩。
2
江南味道
《山家清供》虽为林洪的“菜谱书”,但其中有很多惊艳之处。
还是以“柳叶韭”为例,不但为杜甫的诗提供了新解,还让“酱油”二字首次出现。那几滴酱油,是“柳叶韭”的点睛之笔。在我不多的做饭经验里,调料仅为油盐酱醋以及葱蒜。买酱油的时刻,多是我想到要凉拌一小窝韭菜之时,那种微微的咸鲜,实在不是加点盐就能实现的。
在北方的少年时,酱油只是酱油。到了江南,也一直模糊于生抽、老抽,以及各种酱油名目的缘由。

直到去年看潮季,在钱塘江边一路往东,在海宁的长安镇转入了徐志摩家的酱油厂——裕丰酿造——它的前身是裕丰酱园,由徐志摩的祖父徐星匏创立于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周青是裕丰“徐宅”酱油的品牌创始人,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各种酱油在厨灶间最为妥帖的用处。
其时,恰好在读英国美食作家扶霞的《鱼米之乡》,这部书中,她以江南菜呈现出鱼米之乡的一种妙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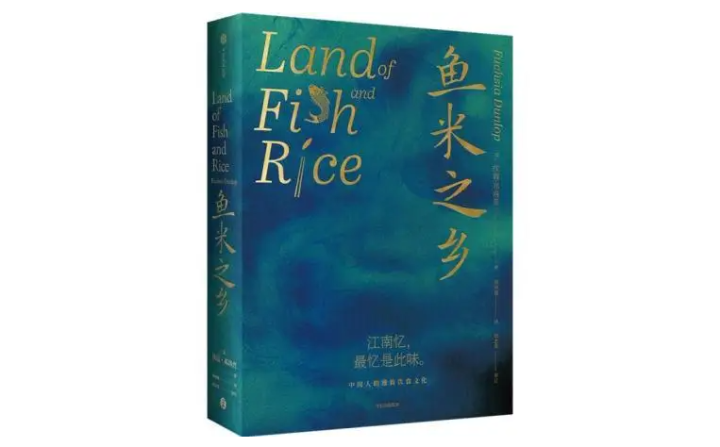
扶霞说,在这本书出炉的前十年,她开启了自己的江南之旅,扬州、杭州、苏州、宁波、绍兴、上海……恰恰是在杭州,她决心写一本江南食谱。
那一天,当她“在杭州城郊穿过一道月洞门,走进龙井草堂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庭院中时”,这个决心下定了。因为,十年江南行旅,江南菜肴中那些自然与人工巧手完美结合所抵达的健康与愉悦的平衡吸引了她,时光里的一粥一菜,竟可回溯传统,又能通往未来。
3
酱油的来处
江南厨师经常使用的重要调料并不多,扶霞以一个外乡人的视角,第一眼就看到了酱油(老抽):取其咸味和浓郁的颜色,在红烧菜中不可或缺;调料之外,也可以作为单独的蘸料。
正因如此,《鱼米之乡》里的江南菜,必不可少的一味调料便是酱油。
糖醋里脊,干菜焖肉,鲞蒸肉饼,荷叶粉蒸肉,嫩姜炒仔鸡……江南人家餐桌上的家常菜,生抽或老抽,或隐或显。4月里的清蒸鲥鱼,如果没有那淋在鱼身上的酱油晕染开来,就少了味道与风景。
因为这本书,以及去年9月看潮的偶遇,我就真的就去找了13世纪才见于书面材料的“酱油”二字,究竟来自哪里。
一堆堆资料看完,扶霞的又一本书《寻味东西》出版了,其中有一篇“敢问酱油从何来”几乎囊括了我半年“所学”,而且总结得十分简练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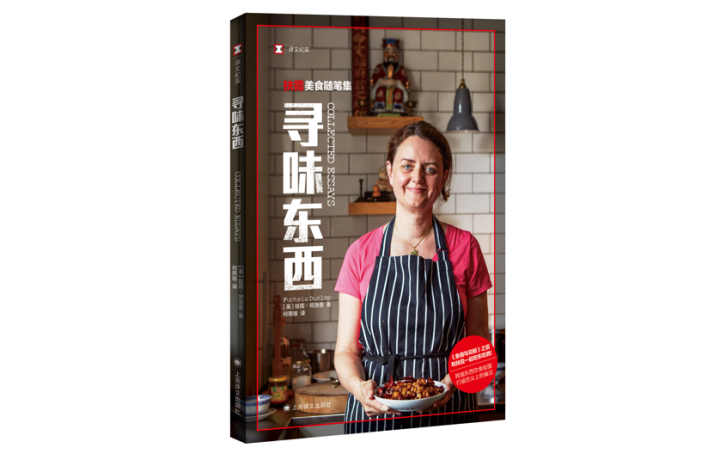
酱油从何来?其实是先有酱,才有了酱油。
酱即将,将领的将,中餐调味品中当之无愧的首领。早在孔子之前,已有了它的身影,古代典籍《周礼》中就提到一百种不同的酱。
酱的原料本以肉类为主,它与酒、盐、曲混合发酵,成为具有独特风味的配菜或佐料。在先民漫长的实践中,大豆成为制酱的主要原料。
那么,到底是谁灵机一动,将大豆在盐卤中发酵后产生的液体过滤出来,从而让酱油在这一千年的餐桌上独领风骚?没有确定的答案。还好,南宋的林洪写下了“酱油”二字,让它与韭菜、春笋、蕨菜相伴,也让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宋时的春天,那些市井间的烟火味道。
扶霞爱江南菜,所以,她说,酱油也是整个“红烧”家族的灵魂调味品。抄录几句她在《寻味东西》里的所遇——
资深大厨董金木(现已退休)是红烧艺术的大师。他教我如何把胖头鱼巨大的鱼尾变成“红烧划水”,这是一道经典杭州菜,鲜嫩多汁的鱼尾浸润在一汪闪着光泽的深色酱汁中,让唇舌感觉到奶油般的柔滑。包括这道菜在内的红烧菜的秘诀在于,将浓郁的传统酱油与绍兴黄酒、糖混合在一起,再加上葱姜增香提味。
4
叫花鸡
想来只有扶霞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美食家,无论身在何处,她总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种食物的味道中去。
像我这样的北客南来,虽然也爱江南菜的清淡,却一直未能习惯其“浓墨重彩”的地方。比如红烧、糖醋而成的各种鱼肉,似乎那些浓厚的味道,总叫我的味觉发起反向攻势。
如同叫花童鸡这样江南菜,我却愿意一试,君子动口又动手。
同样是读金庸,六神磊磊读出一个饭碗,而我记得最牢的是叫花鸡。

最近,又去翻阅书中所写——
黄蓉用蛾眉钢刺剖了公鸡肚子,将内脏洗剥乾净,却不拔毛,用水和了一团泥裹在鸡外,生火烤了起来。烤得一会,泥中透出甜香,待得湿泥乾透,剥去乾泥,鸡毛随泥而落,鸡肉白嫩,浓香扑鼻。

扶霞也写了叫花鸡的做法,是家庭版的。照着这个做法,我去超市买了一只鸡,生抽老抽涂抹腌制一番,包裹它的是西湖捡来的某颗莲子发出的荷叶,最后,再用加盐的面皮包住,放进烤箱。很成功,只是这只鸡本身的质地有些菜。后来,换了乳鸽,又试了一次。
《鱼米之乡》里展现了叫花童鸡的做法,而《寻味东西》有更多鸡的做法,更重要的一点,是寻味的过程中,扶霞对生活的热爱,有东有西。
5
林洪这个人
林洪也是这样的人吧。
一本《山家清供》收入一百多种宋时吃食。说它是菜谱,又记下了朋友间的往来,做菜与品菜的举止行为以及情绪,往日的传闻掌故,自己与他人的诗吟。山家,清供,不是盛宴,但精神饱满。
不过,当我去翻找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却没找到太多材料,大体归纳来只是个读书人,却没有混上个一官半职。
他自己说是林和靖的七世孙,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那个梅妻鹤子的林逋。不过,有人质疑他蹭流量,梅妻鹤子的林逋怎么会有后代?但又有人说,林逋是妻子逝后未再娶,再说他应有兄弟,那么,是他的后人,似乎也未必全然是乱说。
林逋隐居,林洪云游,虽然方式不是,但总是殊途同归,心是自由的。
林洪记“梅花汤饼”,用今天的话来讲,大抵是馄饨做成梅花状,但和面讲究,其水浸过白梅、檀香末,馄饨就有梅的味道。友人为此留下的那句诗,说明林洪对西湖真是有感情的——恍如孤山下,飞玉浮西湖。

因林洪,4月中,我去中苕溪边采到一把水芹菜,又在鸬鸟镇四岭水库下的大河里采了一把水芹菜。河岸上,与它相似的植物那么多,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它,这大概是春天的召唤吧。
水芹菜的做法有很多种,林洪就记下了几种——作菹,为羹。
看不太懂。
于是,烧锅热油,爆炒,最后来几滴生抽,春天的味道,有了。
林洪在“冰壶珍”里写道:食无定位,适口者珍。似乎,这也是江南菜肴追寻的味道,它在寻找最大范围的“适口”。
春天里读林洪,如同春天里读扶霞,也是一份治愈。

嬉笑藏真知
酱油不是广东人发明的,但是广东人把酱油分成三个层次,食不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