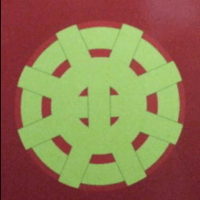张道辉
水是生命之源,水不会像草木一样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而变幻着色彩,让人赏心悦目。但是,随着温差的变化,水的波光灵动仿佛也是有灵魂的。
淮安地处淮河下游,境内有全国第二大淡水湖洪泽湖,更因为淮安四水穿城,被喻为飘在水上的城市,是古代运河四大名城之一,所以淮安是个很有灵气的城市,这是淮安人引以为傲的。
我80年代初从航运学校毕业分配到淮安来工作,定居在淮安已经30多年了,与水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老家在灌南乡下,一个非常闭塞的小地方百禄镇,鸡鸣三县(响水县、涟水县和灌南县),那时候灌南还属淮阴市。小时候我的文科成绩特别好,我的理想是长大做一个语文老师,在莘莘学子的目光中,背着手,昂着头,在讲台上来回踱着步,把一篇古汉语讲得透透彻彻,淋漓尽致。可惜上世纪八十年代简陋的乡下中学没有文科班,只好在理科班里复读几年,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当时只想一门心思地跳出农门,那时候一个农村孩子填志愿两眼一抹黑不知道什么学校好,误打误撞地上了航运学校,还偏偏是船舶驾驶专业,这与我当初的梦想相去甚远,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

1983年8月3日,我一个人背着行李独行来淮阴报到上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淮海北路两边的雪松长得非常茂盛,树身特别矮,树冠特别大,郁郁葱葱,当时很好奇,水泥地上会长出这么高大的树木。公交车穿过里运河,婉然娴静的里运河玉带一般碧水清清,让我眼睛一亮,莫非就是在这条河上行船?下了公交转了三轮来到南港才知道真正的大运河是什么样子的。
上了船成了一名船员,过起了水上漂的日子,大部分航线是从徐州装电煤到淮阴、扬州电厂往返,尤其是在北方港口装煤非常困难,码头上下煤的漏斗位置是固定的,而漏斗下装煤的驳船要经常向前或向后移动,这样才能保证装上船的煤垛子一字排开,才能保持船体平衡,而扯着缆绳把驳船前后移动的脏活累活只能是我们这些刚上船的年轻人干,风平浪静的天气还好,如果碰到刮风下雨,上风头的煤屑子直往脖子里灌,一条船装下来,人真成了非洲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也笔耕不辍。在别人喝酒打牌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就着昏暗的灯光读书写作,耳边是轰隆作响的机器,头顶是人走过甲板划过的刺耳声音,天道酬勤,付出终有回报,在船上干了不到两年,领导看我有写作才能,就把我调到机关做文字工作。这段飘在水上的宝贵经历,成了我以后文学创作的非常难得的一笔精神财富。

最初几年我都是以改革开放初期的运河航运为背景和题材创作了一批散文。那时候淮海晚报刚刚创刊,结识了卫华、桂军、向明等一批
做
编辑的青年才俊,他们真正是意气风发,诲人不倦,给了我不少的帮助。主编田林高先生高高的个子,总是黑着脸,佝着背,不苟言笑,烟不离嘴,在编辑们的屋里偶尔碰到他,大家对他也是恭敬三分,他当时还是有名的杂文家,读他的杂文真的像匕首、像刀枪,好过瘾。他还曾送我一本他的杂文集,叫《正风集》。可惜英年早逝,让人好不伤感。与我交往最多的是向明先生,因当初他编交通运输史我编运河航运史而相识,他的长相酷似过去有一幅画叫《毛主席去安源》穿长衫拿雨伞的青年毛泽东。我在他手上发过最得意的一篇散文叫《弄船的女人》:“船多拥挤时,女人不得不拿起船篙子,一篙子下去,船头兀自不动,女人把篙梢子抵在肩胛窝里,身体俯下去,腿用力向后蹬,于是女人身体的曲线更加明晰起来,该鼓的地方完全凸出来,该陷的地方自然更加凹进去,力与美的造型巧妙地定格在瞬间。”弄船的女人也爱美,但条件不允许,穿不了高跟鞋,穿不了花旗袍,绾起少妇髻,插一朵小红花,日头高照时,爱俏的女人不忘拿一把小花伞,以水为背景,女人便多了几分诗意,顿时在清淡的河面上增加了几分亮色,惹得国有集体船队上清一色的男人们眼热心跳,齐刷刷赤裸裸的目光刀剑一样射过来,挑逗性的口哨吹起来,间或还能瞄见卫生间里洗澡的男人裸露的上身探出来,弄船的女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抑或是无奈,抑或是宽容,风里浪里,弄船的女人就是这样晃晃悠悠、平平淡淡地抛洒自己的青春。”后经向明先生推荐,该散文在1994年10月17日在《扬子晚报》的“繁星”副刊上登出。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鼓励发展个体运输船,打破了国有集体航运企业的垄断,于是一批农民从田间走入运河,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船民,掘得了个人财富的第一桶金。它们鲜明的生活特色就是船上不光有老人小孩,还有小猫小狗。
向明先生还是个书法家,记得有一年国庆,他牵头组织一批书画家到运河航运与企业员工联谊,当中就有德高望重的市国画院著名画家吴夕兴先生,瘦瘦高高,长发稀疏过耳,话不多爱沉思,也许在淮安这个水城被水腥味浸淫多年,他的画大多以淮安水乡为背景,了了数笔就能勾画出一幅情趣盎然的水乡生活图。他当时给我画了一幅题名为《归心》:其时,夕兴先生略一沉思,便泼墨挥毫,不一会儿,层次分明、浓淡相宜的湖荡滩涂便跃然纸上,铁划银钩般的寥寥几笔便呈现出秋风劲草,翻滚乌云,秋风瑟瑟,暮气沉沉,渔人早抛了锚而人去船空,天地间唯两只水鸟振翅高飞,成为画面中唯一有生命的亮点。我在淮海晚报上写了一篇赏析:“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身体和心灵的归宿,无论是那些在灯红酒绿中潇洒自在的达官贵人,还是那些在寒冷的冬夜里为生计而奔跑的三轮车夫们,最终都是要回家的,一颗归心对家的情感满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人海茫茫,红尘滚滚,快点回家去吧!让疲惫的心灵在家的港湾里静静栖息。”夕兴老看了我的赏析说:“这个人是懂我的画的。“我心甚慰。如今这幅精心装裱的画随我搬了几次家,总是挂在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段佳话和情谊,历历在目。算起来夕兴老也该耄耋之年,不知斯人养老何处。
向明先生后来辞去晚报编辑之职到宿迁筹办书画院,我还特意去宿迁道贺,那天也算是高朋满座,好不热闹。再后来听说他去北京发展,就失去了联系。这么些年了,不知在他乡可安好。

说起运河航运这个单位,老淮阴人不会陌生,五六十年代淮阴地区轮船公司作为国有单位非常有名,容纳了市区好多人就业,一个人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大量的私有船舶并入国营,运河航运最高峰时轮船站遍布苏北地区,那时候交通落后,出门不便,人们出行大部分选择坐小轮船,直到80年代初客运航线才停掉,企业高峰时有职工5000多人。斗转星移,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行业衰败,船员不好找对象,人们思想开放,谈恋爱讲究情调,老百姓说“世上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好女不嫁弄船郎”,就连当时的清江棉纺织厂的女工也不愿意嫁船上人。当时,江苏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片,叫《水和尚圆舞曲》,反映新一代船员的苦闷和彷徨,没起到好的影响,尽是负面的宣传作用。后来在城市里已经招不到船员,只好到农村去招工,用工性质叫农民合同制,简称农合工,男人进城了,必然拖家带口地进城,没有这么多的公房,选择在南港运北西路征一片农田盖了一批简易房让他们安家。30多年了,这批简易房还在,成了拥挤不堪的棚户区,仍然处在城市的边缘,成了这个城市的“伤疤”。有人因此而得福,就是这批船员的后代们,他们或上学远走高飞,或在这个城市成家立业,完全摆脱了父辈的贫困,真正融入这个城市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八十年代后期国资撤出航运业,加上这样老式的国企负担重,负债多,竞争不过个体运输,让这个在淮阴地区风光几十年老企业不堪重负而艰难前行。前几年因为里运河文化长廊建设的需要,拆除了轮埠路1号老运河航运的办公楼,那可是五六十年代淮阴地区非常气派的办公楼,座落在花街最东头,若飞桥闸塘边上,门前有十几层台阶的老式三层楼,灰蒙蒙的,早已失去往日的风采,一直租给人家搞经营。因城市建设需要而拆除,也算是对这个城市最后的贡献。最近拆除了又一幢楼就是港口路18号楼,共五层,是80年代初建的办公楼,拆了以后开发房地产,成了拯救这个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后浪总是推着前浪,在这个城市的西南方一座新的港城拔地而起,运河里也见到了集装箱运输的身影,淮安交通运输一水独大的局面早已不再,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以及高铁的加入,形成了淮安交通运输新格局,人生不必为过去而伤感,而要为今天这个社会点滴进步而欣慰。
我在2002年离开了运河航运,19年的青春抛给了运河,从青年到中年,从血气方刚到两鬓斑白,见证了国有航运的衰微和多种运输形式的兴起;见证了她经过不断拓宽,边坡不断渠化,成为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管道,一泓清水不但养活了淮安人,还源源北上,过了黄河。这是一条淮安人的母亲河,在她的身边每天都演绎着人生的悲欢离合,那些人、那些事……。
编辑:苗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