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后深圳女生谢文蒂,
是一个用玻璃来创作的艺术家。
6年前,她辞去体制内的工作,
一个人、一辆车,
开始全国到处跑的“游牧式”创作。

她的作品非常细腻、有灵气,
她将工厂阿姐缫丝的手势“植”入玻璃泡,
来思考女性隐形的劳作;
把老照片、翻绳游戏叠烧到平板玻璃上,
来探索家庭关系的亲密与疏离……




谢文蒂在驻地创作
谢文蒂曾是国内第一批玻璃专业学生,
当年她硕士毕业回国,
国内创作环境几乎是“荒芜”。
如今,玻璃艺术有了更多公众认知度,
也有更多驻地和委任机会向之敞开。
谢文蒂享受眼下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
“我让自己流动,看看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述:谢文蒂
编辑:陈 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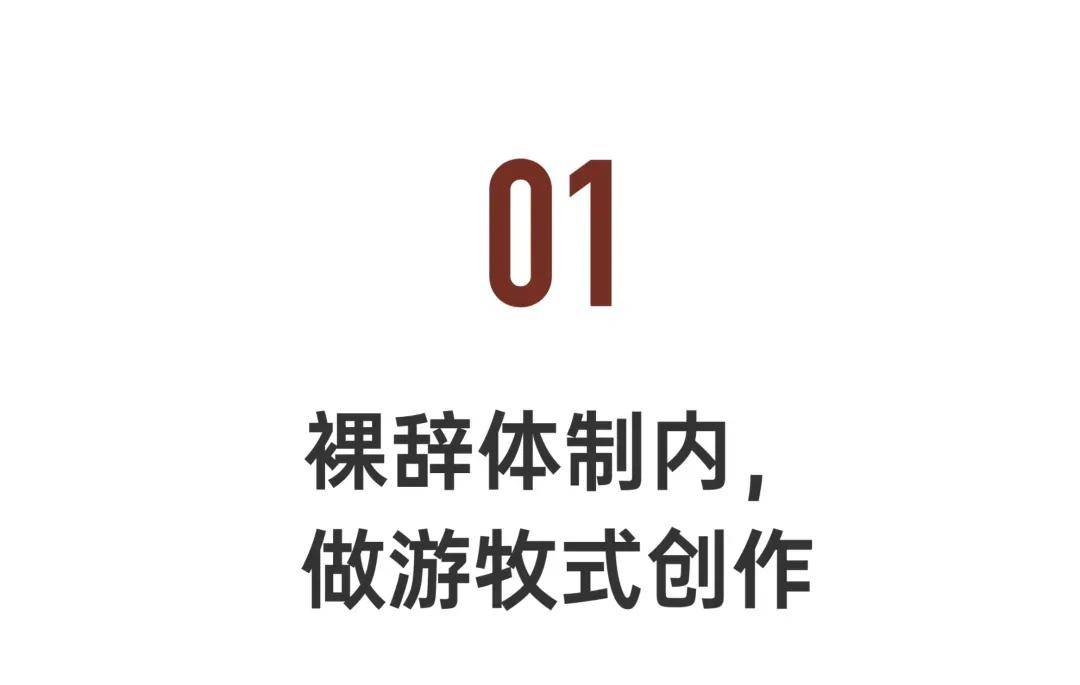

11月,谢文蒂在山东淄博博山的玻璃厂
天色几乎暗下来,我们在淄博博山玻璃工厂见到谢文蒂。玻璃师傅们已经下班了,工厂冷清至极,只有巨大的玻璃熔炉冒着火光和热气。
工厂深处,一张污迹斑斑的木板搭出来的桌子上,摆着几件她刚翻好的模具。创作时她总套上一件白大褂,已经穿到发黄,看上去很像一个实验室研究员。

熔炉里流动的玻璃液
谢文蒂经常用玻璃吹制工艺来创作,吹制工艺指的是用高温将玻璃熔化(保持在1200度),再用工具将熔炉里的玻璃料取出来吹制塑形。此时玻璃呈液体蜂蜜状,晶黄闪亮,格外诱人。

谢文蒂的代表作“游丝”系列创作过程
“但也最费事,费设备、费电、费气、费材料、费人,虽然国内到处都有玻璃工厂,但能满足创作需求的五个手指头应该能数得过来。”谢文蒂告诉我们。

这几天,早上9点她就进工厂做模具、翻模,将就一顿午饭,晚上赶去另一处吹制工作室吹玻璃。有时要跑去不同的地方找材料、做金属焊接、找铁艺师傅改造物件……她要随时在脑子里演练,不让某个环节掉链子。不久后她在北京重美术馆有一个橱窗展览,时间很紧张。
半月前,她独自从深圳开车来淄博,全程2100公里,早上10点出发,开到太阳下山,日均开8小时。
一个人,一辆车,她称自己是“游牧式”工作方式。每次驻地或去玻璃工厂做创作,都要辗转腾挪,跟搬家似的。一辆红色的SUV ,几年下来已经开了11万公里。

她喜欢开车时那种“旷远”的感受,看风景、听播客,经过未曾料到的大江大河,会忽然惊呼震撼。
沿途或日常所见的有趣事物,是谢文蒂的灵感源头。很难说她的作品有一个聚焦的主题,她想保持住那种即兴的东西,于是腾挪、流动,到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可利用的材料和现成品。

谢文蒂在作品《拂过》前
2018年,她辞去体制内的工作,开始全职做艺术创作,玻璃是她最喜欢使用的材料。
但玻璃有它的脾气,操作不当或者退火不当都很容易破裂,需要耐心呵护。谢文蒂觉得自己跟玻璃很像,看上去轻盈,但又有真实的重量。高温时玻璃是液体,柔软,流动,但冷却下来以后很硬,“我也挺倔的,比较有韧性”。
谢文蒂和玻璃打交道已经接近20年,作品曾在英国、美国、德国、捷克、挪威展出。这几年,她才开始更密集地驻地与创作。

谢文蒂在最新展览“太阳底下无新事”现场
毕业后很多年,她在美术馆做遍各种工作,又持续做了好几年流浪猫公益救助,偶尔做一些公共艺术,潜意识里把最难的“成为职业艺术家”排到最后面。
直到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必须要面对那隐秘、但绝不消逝的创作渴望。那时她问自己,“如果现在不开始,是不是就不会开始了?”
以下是谢文蒂的自述。


佛山南海丝厂女工在工作中

缫丝的手势细节
2022年,我参加了大乾艺术中心的驻地“河流计划”,沿着珠三角水域探访一些制造业工厂。
在佛山南海丝厂看到女工们站在几大排机器前,将蚕丝从蚕蛹身上剥离出来,熟练地将比头发丝还细的蚕丝分离、打结,她们手指翻飞的动作特别吸引人,很有力量感,当时我就想用吹制玻璃把她们的手部姿势表现出来。

流动的玻璃液
我说服丝厂的女工阿姐们参与到我的创作中,给她们缫丝动作的手势翻模,再用玻璃吹制的工艺,将手势定格在透明玻璃泡里。因为驻地住在酒店里,没有工作室,只能在酒店的厕所翻模。我的车也成了临时移动仓库,用来搬运材料、模具。


“游丝”
第一个版本叫《游丝》,展出时,我把它们悬挂在一个高十几米的空间里,玻璃泡仿佛悬浮在空间中,让钢丝绳、玻璃和手势形成一股张力。
你能看到玻璃泡里有一只手,连纹路都清晰可见,但玻璃里什么也没有,是空的,这种隐形的关系正像是我在女工的劳作中体会到的。


“双手练习”系列
缫丝看上去轻巧,实则需要长年累月的经验和手部的巧劲。女工们告诉我即使这么细的丝,也会割伤手指。我和女工阿姐们一起工作了好多天,去年重新做这件作品时又去找她们,作品的名字就是她们的名字,阿梅、阿珍。
在和她们的交往中,我切实地感受到生活的重量,疫情后丝厂效益不好,她们都要打数份工兼职,家里还有小孩子要带,生活很不容易。但她们都非常勤劳,乐观。


《在她的身体里-阿梅》在挪威展出,谢文蒂在讲解作品
新做的版本《在她的身体里》,都是红色系,有点暗示了女性的身体,“她”既指女工也指代玻璃,玻璃的身体也被一只手戳了一下。在最新版本里把自己做作品的手也放了进去,某种意义上我也很像一名女工。

谢文蒂在景德镇驻地
我一直对分形很感兴趣,分形在自然里随处可见:树枝、动物的角、闪电、火焰、细胞分裂、人的肢体等等。
2021年在景德镇驻地的时候,我通过剪加热的玻璃让玻璃泡分裂出很多尖端,形成一个个“角”。


陶瓷、玻璃、金属结合的作品《镜像(角)》
这七组雕塑里,上半部分是陶瓷做的,有很粗粝的表面肌理,模拟公鹿的角和树根,但故意做成粉红色,看起来很像珊瑚。底座是一块呈90度角的做锈的生铁,映照往下伸出的一根玻璃角,它像陶瓷的镜像,也像个幽灵。


谢文蒂在做玻璃版画
玻璃版画系列是我将图像叠烧在几层平板玻璃上,来探索家庭和亲人关系里的亲密和疏离。
家庭的老照片、翻绳游戏、雏菊的花和种子、树影,因为叠烧,平面图像之中产生了一种空间感,使图像可以错位或者重叠,有点像是胶片曝光的感觉。

国内第一件在地铁站里的镶嵌玻璃作品
我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是落地在深圳机场地铁站的《美丽新世界》,使用了传统教堂窗花玻璃的镶嵌玻璃技术。由于作品体量变大,也直接影响了我对于空间的考量。后来我做作品时,会更因地制宜和考虑作品与建筑或公共空间的关系。


“追气”系列
“追气”系列是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做的公共艺术作品,这是一件可以融进环境里的作品。
我用玻璃就像是“给空气描边”,在荷花池的岸上立了一个3米高玻璃立柱,里面是互相挤压形变的几个大玻璃泡,仿佛空气在密闭空间里的胶着状态。荷花池里有很多游鱼、青蛙,我做了一个浮在水面,有呼吸、沸腾感觉的玻璃泡泡装置。


“太阳底下无新事”右窗
今年11月,我的橱窗个展在北京重美术馆开幕。在两扇大窗户里,我放置了十多件装置作品。窗户引人窥视,我想要给观众带来一场寻宝体验,通过绳子的线索、镜子的反射去发现这些“调皮的”物件。


谢文蒂在吹玻璃
我上大学是2006年,当时中国美术学院的玻璃专业还是新开设的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连老师也是从其他专业调过来组成玻璃工作室。
我们上学的时候只学过窑制玻璃,有点像是传统雕塑,先做泥塑,然后翻模,最后让玻璃在窑炉里成型,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热玻璃,只在生产玻璃高脚杯的工厂见过吹杯子。

2012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本科感觉没学明白,属于半生不熟,本着中国人学一行爱一行的传统美德,研究生我就去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继续学玻璃,当时学校里的中国人很少。
去了英国后,我才接触了当代艺术,对玻璃这个材料有了更多的理解。当时只弄清楚一件事:我不想成为玻璃艺术家,而是想做一个用玻璃材料做作品的艺术家。


“了不起的骗子”系列
玻璃可以做得非常透明,很轻盈,像个泡泡,也可以做得不透明,像块石头,这种伪装性很有意思。在创作上第一次找着点感觉,是研究生二年级的系列作品“了不起的骗子”,我用黑白两种颜色,来混淆视觉惯性给人的关于轻重的判断。
后来我发现,玻璃在中国古代常常作为替代品出现,比如用来仿玉和修复陶瓷。中国人重玉器和陶瓷,更喜欢不透明的东西。没出国留学前,我也倾向做不透明的磨砂玻璃。

《另一个我》

《旅程》
后来我还读到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了解到东方人对阴翳之美的喜好,和西方人的审美很不一样。在西方,玻璃是光明之物。比如站在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下,会让人有如沐神光的感受。在理解东西方审美的这层差异之后,也有了后来的《另一个我》和《旅程》等作品。

谢文蒂在美术馆上班时期
2012年毕业回国,我也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艺术家,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国内的玻璃创作环境等同于荒芜,做玻璃太需要设备了。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艺术学生,也没什么钱,要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我就选择了一份看似相近一点的工作,通过事业单位考试进了深圳美术馆上班。
我在深圳美术馆什么工作都做过,策展、写评论、策划组织公共教育活动、讲座工作坊、写公众号宣发等等。同时,几乎每年都攒好假期到美国去上工作坊,学习玻璃的技术。



“相遇”系列
“相遇”系列是我在美国上玻璃工作坊时创作的作品,我在美国西雅图的森林里做了一组装置,它们像是森林里窃窃私语的小生灵。



个展“漏气”
2017年底,我白天在美术馆上班,晚上去驻地,也是那时候学会了开车。在深圳市内跑,3个月开了8000公里,做了个展“漏气”,重新找到了一点做艺术的感觉。
“漏气”的名字来自于展览的英文名form form form,连着读就成了漏气的声音。这个展览主要是我对于形状的探索,我把四个透明玻璃球挤在一个玻璃缸里,形成一种微妙的张力。捡来的手推车被我贴上黄黑警示胶带,顶上插了两个玻璃球,像在博弈,却又彼此支撑。
决定辞职之前,我处在一种压抑和自我否定的状态。这些扭曲的、有洞的、裂口的形状,和我当时的状态也有关系。我想表达一种对尽美尽善的抵抗,人应该允许自己松懈一点,有地方“漏气”才有办法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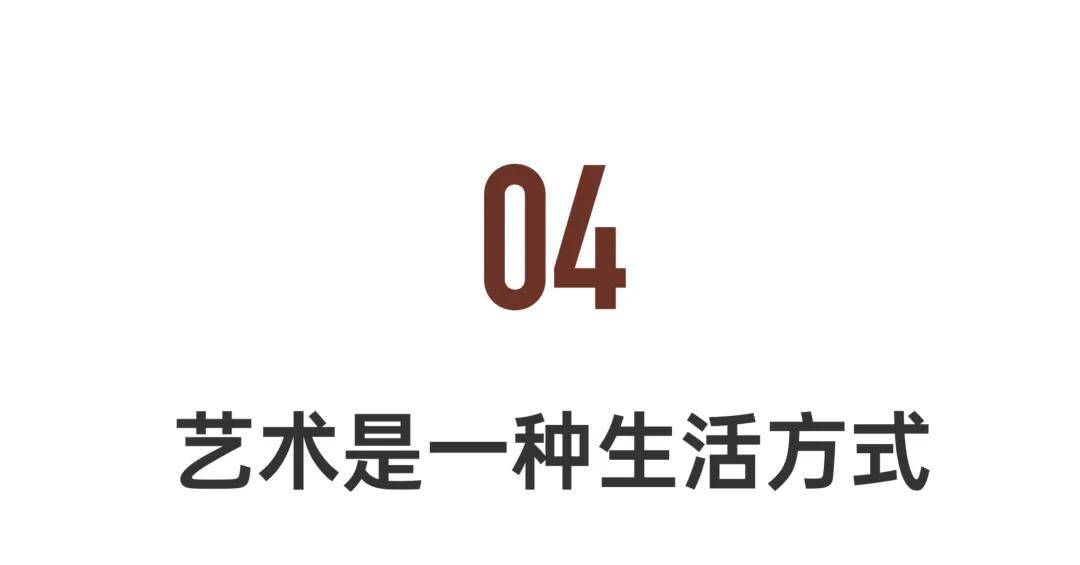

其实做艺术生存还是蛮难的。我现在主要靠画廊展览卖作品和委任作品,偶尔有一些设计项目的收入生活。委任作品基本只能cover材料和制作费。驻地基本没钱,只提供住宿和工作室,但驻地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今年夏天在重庆器空间驻地,巧的是它坐落在重庆北碚一个废弃的玻璃工厂里面,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北碚的玻璃产业在上世纪曾经非常辉煌。

在重庆的玻璃厂探险
我每天都在玻璃工厂废墟里探险,有一次在一个没拆完的机械车床前发现了一个凝固的向下流淌的玻璃,就这么悬停了10年之久,我摸了摸它,感觉触摸到了时间。我还找到一些熔炉底的原料,准备熔掉做些东西。
常常有人说,你做作品很折腾,都很远,我挺享受开车的过程,尤其是开长途。我一天可以开八个小时,只需要在加油和上厕所的时间停一两次。开车的时候思绪乱飞,经常灵感和体悟爆棚,有一种大地辽阔任我行的豁达感。

谢文蒂在重庆驻地时的环境

在驻地期间的临时住所
2025年,我计划去浙江龙泉做一个陶瓷的驻地,之后还要回重庆器空间完成驻地和展览。
艺术家对我来说不是一顶帽子,可能更像一种生活方式。我感受到我仍然不断在成长,现在我仍然会有很多的困惑、问题、情绪,但我想,就像我做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我生活的意义也是解惑的过程。
我希望可以一直做点有意思的事情。

不喧哗自有声
有钱有闲有梦想的生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