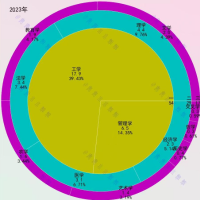本篇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当地历史事情为背景虚构创作。
万历二十三年秋,云南布政司的差役李昭带着一封烫金的密信,穿过乌蒙山脉的瘴霭来到威宁。当他站在凤山寺斑驳的山门前时,天色已近黄昏,最后一缕夕阳正将七层飞檐上的青铜铃染成暗红色。信封上的火漆印是半枚残破的傩面,与他怀中那枚从父亲遗物中找到的另一半恰好合拢——这是二十年前钦天监在安顺平塘失踪的"观星傩面"。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李昭恍惚看见三个戴青铜面具的身影正在殿前舞动。领头的"阿蒙"戴着缀满银铃的牛头面具,左手握着画有星辰的铜铃,右手却端着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两个随从"阿者"和"阿朵"的面具分别是虎头与羊头,他们手中摇动的骨笛发出类似风中呜咽的声音。
"外乡人可识得这戏?"阿蒙的声音像是两块石板相互摩擦,面具眼眶里的青金石在暮色中泛着诡异的光。李昭刚要回答,却发现喉咙像被无形的手攥住,只能僵硬地点头。刹那间,殿内烛火齐灭,长明灯骤然暴涨三尺,照出梁柱上密密麻麻的彝文咒符。

当光明重新降临时,三个傩面人已不见踪影,唯有殿角的青铜鼎仍在袅袅升烟。李昭凑近鼎身细看,发现内壁刻着他再熟悉不过的星图——这竟是钦天监失窃的《天罡北斗阵图》。他忽然想起临行前首辅张居正的嘱咐:"威宁凤山寺里藏着前朝龙脉秘钥,务必要在冬至前找到..."
子夜时分,李昭摸黑溜回寺院。山风裹挟着某种古老语言的吟唱从后山传来,他循声攀上陡峭的岩壁,藏在松树后的窥视让他浑身发冷——月光笼罩的祭坛上,三个傩面人正在围着一具漆黑的棺椁跳祭祀舞。阿蒙手中的铜铃突然调转方向,清越的铃声竟与北斗七星的运转轨迹完全吻合。
"这不是普通的傩戏。"李昭颤抖着掏出罗盘,指针疯狂旋转指向棺椁顶部。就在这时,棺盖缝隙中渗出一缕青烟,在空中凝成个身着明代官服的女子虚影。女子脖颈间挂着的玉佩与密信上的火漆印如出一辙,她幽幽开口的声音像是百十个声音叠加:"他们困了我两百年,连撮泰吉的最后一折《赎魂》都没能让我的魂魄解脱。"
原来嘉靖年间,威宁知府夫人苏氏因私藏前朝玉玺被东厂追杀。她在凤山寺自焚前将玉玺藏进青铜鼎,却被东厂暗卫掘墓时误触机关,导致整支护陵部队被埋在地下。苏氏怨气冲天,化作厉鬼依附在撮泰吉戏班中,每逢冬至便借戏魂索命。那些失踪的钦天监官员,实则是前来破解龙脉秘密的受害者。
李昭望着祭坛上熟悉的北斗阵图,终于明白父亲当年为何要带着半枚傩面逃亡。他解开腰间玉佩,将两面残缺的观星傩面合二为一,青铜面具中顿时射出道道金光。随着《赎魂》的旋律响起,三个傩面人手中的法器开始共鸣,棺椁中的青烟缓缓聚成苏氏的模样。
"不是所有执念都要以鲜血偿还。"李昭将玉玺按在阵眼,三百年前被东厂斩杀的将士虚影从地底升起。他们手捧白幡,用生前的官话唱起安魂曲,苏氏的衣袍渐渐褪去血色。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时,祭坛上的青铜鼎自动飞向后山,那里沉睡了两百年的明代将士终于得以安息。
从此威宁的撮泰吉戏班在冬至夜都会多出三个戴青铜面具的"演员",他们跳完最后一曲便会消失在晨雾中。当地老人说,偶尔在深山里能听见身着明代官服的队伍唱着古老的歌谣走过,但当追上去时,只剩满地闪着微光的青铜铃铛,和风中飘散的彝语唱词:"星归北斗,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