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各地法院对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认定情况并不一致,出现了不少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规定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明确排除了“非不可抗力”因素。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即将施行的《民法典》第533条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已经明确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规定。
通过两个法律规定的差异可以看出司法界已经就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原则之间的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不可抗力的发生可以引发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
然而,虽然《条文说明》第26条的规定《劳动法》中的客观情况是指不可抗力或者其他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情况。

但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或者之后的其他情况进行规定。
这些其他情况具体是指的什么情况呢?对于此各地的规定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
北京的规定:受政策性搬迁、政策性的资产转移或者停产、转产、转(改)制;具有特许经营性质的用人单位的经营范围等发生变化。

广东省规定: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经营性搬迁,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陕西省虽然未对“客观情况”进行明确规定,但是规定有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情况发生了变化。
且该变化足以导致原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先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合同,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湖北省、克拉玛依市规定用人单位停产、转产、分立、合并或其他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时不应当是解除合同而应当是变更合同。
宁夏回族自治区规定政策性变化或者用人单位的经营发生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变更劳动合同。
此外,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下达了很多规章和政策,虽然里面没有明确提到疫情导致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履行上的困难能否适用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也提出了很多灵活用工的方式,为用人单位在遇到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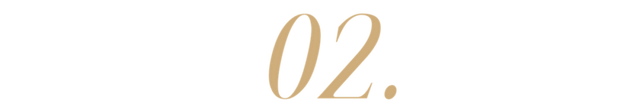 “客观情况”的理论基础
“客观情况”的理论基础为了体现司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准进行统一。
而对其标准进行统一前,我们应当厘清什么是“客观情况”以及“客观情况”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脉络,这样才能更好的对其标准进行明确。

不少学者认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就是情势变更原则的在劳动合同法中的适用,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能够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合同法解释二》中明确指出情势变更的原则的适用前提是作为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或环境的客观事实发生了异常或重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发现即将施行的《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对于情势变更的原则的规定将“客观情况”变更为了“合同的基础条件”。

参照《德国民法典》中对适用情势变更规则除了规定客观法律行为发生基础障碍外,还规定了主观法律行为基础障碍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德国的合同履行中当被作为合同签订基础的重大观念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可以适用情势变更的相关规则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者解除。
我们可以认为《民法典》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可能已经不仅限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具体适用还需等法解释予以明确)。

在订立合同时的主观法律行为的错误可能也会被认定为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适用该条款的前提必须是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虽然与《民法典》中的合同基础条件出现了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但是也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并且二者都是出现了在订立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时无法预见的较大变动而引发的。

这种变动可以是影响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如疫情的影响,在民法中可能就是导致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断裂,导致的企业之间的合同履行基础变更;
在劳动合同中可能就是导致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无法继续维持导致的劳动合同履行基础的变更。
也可以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小的情势变更。

如限购政策的出台导致购房者继续履行购房合同会支付高额的代价或者相关政策的出台导致用人单位无法继续与没有相关资质的劳动者履行合同的情况。
第二,无论是民事合同还是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是依据合同订立时的基础条件对合同进行的磋商谈判。
合同之所以能够成立是以订立合同时的基础条件为前提的,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成立的。

如果劳动合同或者一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或基础条件在当时已经发生变化,说明合同当事人是能够意识到该变化及该变化带来的相应后果的。
他们订立的合同是考虑了变化情况及结果的,是不能以情况变化为由要求对合同进行撤销或者解除的,故而在此情况下是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或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所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和情势变更原则一样都是需要以变动事实是在签订合同以后发生的为前提条件的。

第三,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观要求是当事人对于发生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且不能预见。
学界对于“预见性”一直存在争论。
有的学者主张采用主观标准,认为判断是否能够预见应当以遭受不利影响一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为准,这种主张的理由是结果更加精确并且贴近现实。

有的学者主张采用客观标准,认为应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对能否预见进行判断,理由是判断更加简便易行、避免个人的臆断。
对此,笔者更倾向于适用客观标准。
因为,虽然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才是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实际情况更加了解,站在他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判别在合同订立时,其是否能够遇见到即将发生不利于他履行合同的情况。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否预见,以及能预见的大小。
在确实发生了不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变化时,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坚称其不具备预见变化的可能性。

虽然情势变更原则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因此遭受不利影响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不公平。
但是从主观标准出发或多或少的都会偏向于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可能会导致过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相应的,若从客观标准进行判定,以一般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实际是引入第三方中立标准对于不可预见性进行考察能够更为客观、真实、公平。
并且最高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明确要求应当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法预见”的主张并且无法预见应当以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进行判断。

也是基于客观标准进行的认定。
将该标准放入到劳动合同关系中同样适用。
适用第四十条第三款的是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在当时无法预见的变化而提出的,在这时候用人单位处于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受不利影响当事人的地位中。

相较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而言,用人单位在信息搜集、情报处理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若以主观标准来适用的话会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用人单位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找到各种理由说明该变化是不可预见的,或者抹灭其已经预见的证据。
所以,对于预见性而言,“客观情况”和“情势变更”都以客观标准予以判断会更加公平。

第四,《指导意见》中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当注意利益分配,做到利益分配公平合理。
因此,情势变更的实质要求是为了平衡继续履行合同导致的对一方明显不公平,避免利益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严重失衡的情况,是契约严守原则的一个例外。

作为情势变更原则的核心要件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继续履行将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标准。
在劳动合同领域中,从案例整理中可以看到适用了第四十条第三款的判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若用人单位继续按照原合同的标准履行劳动合同,将会导致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明显增加。
在劳动者仍旧提供相同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支付的成本严重超出了订立劳动合同时的预期。

虽然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中并没有等价有偿的原则,但是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明显对用人单位不公平的情况下也违背了劳动合同法上的公平原则。
也与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初衷相违背。

鉴于劳动合同中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劳动合同法》中对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是由于劳动合同是关系契约的一种,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人的有限理性、履行过程中的客观情况的变化等原因。
签订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双方不可能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措施。

并且由于劳动合同的履行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应当需要保证一定的弹性和自由。
所以便有了设立第四十条第三款的必要,在一定情况下应当赋予用人单位在发生订立合同时不一样的重大变化时变更合同内容的权利。

为用人单位在过失性辞退外提供了一个例外情形。
这与情势变更原则作为民法中严守契约原则的例外的具有实质性的相似性。

第五,有些学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以下简称“《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在个案中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都应当通过高院或最高院审核的规定。
举轻以明重,作为天生具有倾斜保护劳动者属性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解除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该更为严格。

所以认为将第四十条第三款定位为情势变更原则会过分的限制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
对于此笔者不能认同,理由如下:
首先,虽然劳动合同具有保护劳动者的倾向性,在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上应当更加严格。
但是第四十条第三款设立的基础是为了解决虽然劳动者在工作上并无过失但是用人单位基于用工条件发生的变化只能通过与劳动者解除合同才能更好的进行企业管理或者企业运行。

如劳动者无法提供劳动,劳动者无法胜任工作以及一些客观条件的情况。
本来就是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而设立的。

故而并不能当然的推定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当采取举轻以明重的原则。
其次,所谓第四十条第三款系情势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法中的适用是指该条与情势变更原则具有一定的共性,符合情事变更原则的客观条件的要求,适合应用。

而不是机械的套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所有要求,《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中提到的是适用需要经高院或最高院审核是对个案的要求。
对于劳动合同法中直接规定的适用应当属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对于类似案件的“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