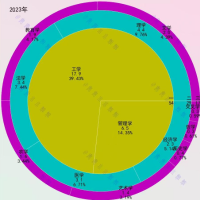本篇以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得名由来为背景虚构创作。
汉初,文安县境,沃野千里,百姓安居,但县名尚未定夺,只以"文安"称之,寓"文治修明,天下安集"。
而县中有一处碑林,石碑半埋在荒烟蔓草间,不知年月,无人识得刻文。百姓只说夜深人静时,那些古老石碑会隐约发光,仿佛隐隐透出墨迹,隐隐可闻其中低吟古韵。
县令刘穆是儒生出身,一心想以文教治国,将文安县打造成礼义昌盛之地。

这晚,他因政务劳累,披星戴月回县衙,路过碑林时,忽然听见低沉的声音从碑间传来:
"兴礼乐,弘道统;方安县,万民同。"声音似有若无,却震得他心头一震。
他猛然停下脚步,仔细端详那些模糊的碑文,却只见苔痕遍布,石面斑驳,什么字迹也无。正狐疑间,一阵微风吹过,碑林深处竟有隐隐烛光浮动。
他循光走去,发现碑群后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穿过荒草地,灯火通明处竟是一座无人看守的石亭。
石亭正中摆着一座未刻字的巨大石碑,四周散落几卷古籍,书封用篆文写就"治道集"、"礼治策"等字样。这些古籍像是刚刚摆放于此,封函无损却散发着墨香。
刘穆翻阅古籍,发现内文多是未流传于世的治县良策,如"县无争诉,必先风化;民有仁心,乃可安居","礼义为先,不矜不伐"等劝学劝民之语,字字珠玑。恍惚间,书卷中似有低语:"以礼治县,万世之基......"
亭侧忽现一人影,却非血肉之躯,而是半透明的儒士模样,宽袍大袖,气质端方,自称是"前朝礼官遗民"。
他指着一卷摊开的古籍,对刘穆缓缓道来:"古来县治之名,关乎万民心志。'方安'二字蕴意深远。'方'者正也,以治道方正为本;'安'者定也,民心安定为要。县境虽治,民心未稳,何以为安?唯以礼教化人,方可名副其实。"
刘穆恭恭敬敬问道:"请教礼官前辈,何以见得'方安'二字乃本县真名所在?"
儒士淡然一笑,挥袖从袖中取出半块玉圭,道:"此物原是秦代令尹所用礼器,曾传诏令于边县,凡以礼乐治世,皆可刻碑立名,'方安'便是秦令所题,后因战火失传,石碑藏于文安碑林之中——
然礼教兴废,关乎治运,你可知汉家初兴,礼教不立,四境百姓尚武好战,唯文安县民性温厚,若推行礼教,实可为此地正名也!"
言罢,儒士忽化作缕缕清光,散入石碑之中,石碑随即发出柔和光芒,将"方安"二字映在夜空之中。
从那夜后,刘穆便决定以"方安"为县名,他召集百姓,在碑林前正式立碑,将两卷古籍命名为"方安治道策",刻在石碑背面。
他依照古卷上的礼教之道,召集乡贤,开设小学教习礼乐,以诗经《关雎》为启蒙之篇,以《鹿鸣》为宴饮之则;又制定乡约,每逢十五夜,召集村民在碑亭前共读经书,以礼为本,以和为尚。
他还命工匠将县名镌刻于全县门牌,以正县治威仪。
次年,文安县呈现前所未有的祥和之象。文风大盛,民风日淳,邻县百姓听闻刘穆以道化民,无论争讼田产还是婚嫁迎娶,亦渐渐效仿文安县民,以诗礼相待。
文安县竟成了周边几个郡县争学效仿的典范,甚至连远在中山国的儒者听闻后,也称此"方风初兴,四境皆颂"。
一日,刘穆独自再访碑亭,见石碑周围苔痕已散,字迹如刀刻般清晰,赫然题着:"先秦遗训,以礼为邦,方安之道,万世恒长......"
正当他抚碑自语,碑顶忽然放光,恍见亭中立着方才的儒士身影,但开口却是温和如故友:"大治之道,自古通彻,礼教为先,万民心正,县名定夺,自此无忧耳。"
光影渐散,儒士不语,石碑却不复光芒,只留下"方安"两个篆文,透着温厚的苍劲之气,绵延千年。
自此,刘穆将"礼乐立民,以文化邦"奉为施政宗旨。他还在县中设立一座"方亭礼学院",专门教化乡野童蒙。
县民为了感念他,将"方安治道策"编为县学课业范本,每当有官员赴任,必在方安碑前拜读。县民甚至有言:"不识方安碑,不入文安县。"
后来,有文人撰写《方亭文正录》追记此事,将那夜儒士化作的光影传说称之为"方安礼魂",更将刘穆推举为"文安开化之范"。
千年之后,仍有文人官宦途经方安县时,驻足碑亭前,总见苔痕间似有字影浮动,恍若又闻吟诵之声:"方安者,万民心,一县治......礼者道,文者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