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2日,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高朋满座、俊彦云集,钱仲联、程千帆、唐圭璋等古代文学大师级学者和300多位南大师生共同见证了莫砺锋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二天,我国首位文学博士诞生的消息上了《新闻联播》。那一年,莫砺锋35岁。
时光流转,2023年6月2日,已经74岁、刚刚正式告别三尺讲台的莫砺锋又出现在《新闻联播》里。作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他以《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为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所有成员的神圣职责,阅读古典名著从而汲取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也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向全社会普及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最有效的手段,孔子、朱熹等历代优秀学者都视此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理应继承孔子、朱熹的精神。既要精选某些价值最高的经典介绍给社会大众,又要对它们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及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让古典名著脱离学术象牙塔的束缚而走进千家万户。”
从首位文学博士,到唐宋文学的普及者,莫砺锋拥有过很多身份,其中不乏世人羡慕的头衔,但几十年来,他一直是那个“读常见书,乘公交车,吃家常饭”的莫砺锋。他是象牙塔里的一流学者,更是走向大众的“师者”。谈及这些,莫砺锋却云淡风轻:“我的一生里充满了偶然,学文是偶然,搞普及也是偶然。”
因为十年浩劫,那个曾经意气风发、与同学相约“不学文科、不考师范”的少年,失去了当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后,莫砺锋报考了安徽大学英文专业,转年又考入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成为程千帆先生“唐宋诗歌”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2年初,南京大学开始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从28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资格的博士生导师中选出程千帆等10位先生,每人限招一名博士研究生。莫砺锋由此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2002年,又是偶然的机会,莫砺锋的讲座《杜甫的文化意义》走进了百家讲坛。后来他又应邀录制了多期节目,还出版了多本古典文学普及作品,其中包括印册高达10万的畅销书。面对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的读者、观众来信,莫砺锋意识到他不经意间打开了另一扇门:经典著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它们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专供学者研究,更应该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精神滋养。
曾有些深居简出、少与人交往的大学者,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本本普及读物占据了他更多的写作时间。今年5月中旬,莫砺锋在四川眉山三苏祠以“风雨人生中的人格典范”为主题讲苏东坡,在成都杜甫草堂讲“杜甫和传统文化”,两场讲座线上线下听众均在200万左右。6月初,两本普及诗词的新作《小学生必读诗词112首》《中学生必读诗词125首》出版……那些曾陪伴、抚慰、激励他的唐诗宋词,赋予了他抗拒随波逐流、保持精神独立的力量,如今他希望能给予更多人。
宁钝斋中一老翁
初次看到莫砺锋的名字,绝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宝剑锋从磨砺出”,但事实恰恰相反。莫砺锋每次谈及这个话题都会笑起来:“别忘了我姓莫,当年父亲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不露锋芒。他还给我女儿留了一个名字,叫莫杞,杞人忧天的杞。”
理解了名字的本意,就会恍然大悟莫砺锋的书斋为何叫“宁钝斋”。这里还有双关之意,“一是宁愿的意思,我宁可钝一点,不要锋芒毕露。另外,宁也指南京,我是住在南京城里的一个比较愚钝的老翁。”坐在宁钝斋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莫砺锋说,“我想我一直是遵照父亲的遗愿的,一辈子都是这样,要求平一点、平庸一点。”
时至今日,他仍然会搭乘地铁去学校。2018年,因为总打不到车,莫砺锋买了手机,他戏言这是“生计所迫”。在那之前,他是没有手机的,理由也很简单:他通常不是在图书馆或教室里,就是在家里,前两个地点是不能接听电话的,在家里有座机就行了。这个习惯即使是在2004年当中文系系主任期间都没有变过,为此还有人吐槽这位系主任“有些难找”。
系主任当了一年多,莫砺锋迅速辞了职。说起那段往事,莫砺锋笑言其实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1年零4个月中间,我一篇论文也没写成,心里面很乱,就开始写随笔。”这些随笔后来结集成书,就是大受读者欢迎的《莫砺锋诗话》。算起来,这也是莫砺锋走向普及之路的一次“偶然”。
如果从1978年成为程千帆先生“唐宋诗歌”专业硕士研究生算起,45年学术生涯中,莫砺锋从未踏出“唐宋文学”这个领域。“我的才能和悟性有限,范围太大了也做不好,而且唐宋600多年的文学非常丰富,我一辈子都研究不透,所以就一直在里面。”莫砺锋的这番话,很多人会认为是谦虚。但想到程千帆的老师黄侃曾得章太炎先生评语:“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这是师道传承,更是一脉相连。
这份“愚”,还体现在虚怀若谷的谦虚上。莫砺锋的学生、目前已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杨曦至今还保留着2018年莫砺锋发给他的邮件:“请问同学中有谁玩华为手机比较熟练,请他到我家来面授一课,主要想学会用手机打车及扫二(维)码付费。”记者接触到多位莫砺锋的学生,他们回忆说,这些年为了手机、电脑等的使用,他们都没少被莫老师请去“面授一课”,还经常能收到赠书作为答谢。
关于手机的轶事还有不少。有次给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上选修课,莫砺锋严肃批评了两位坐在前排、一直低头摆弄手机的同学。课间他了解到,两人其实是在用手机看课件。第二节课一开始,他就当众承认自己错怪了两位同学,并诚挚地向他们道歉。
如今,手机也已成为莫砺锋的生活“必需品”,但他还是会叮嘱记者:“要是发微信说一声,我不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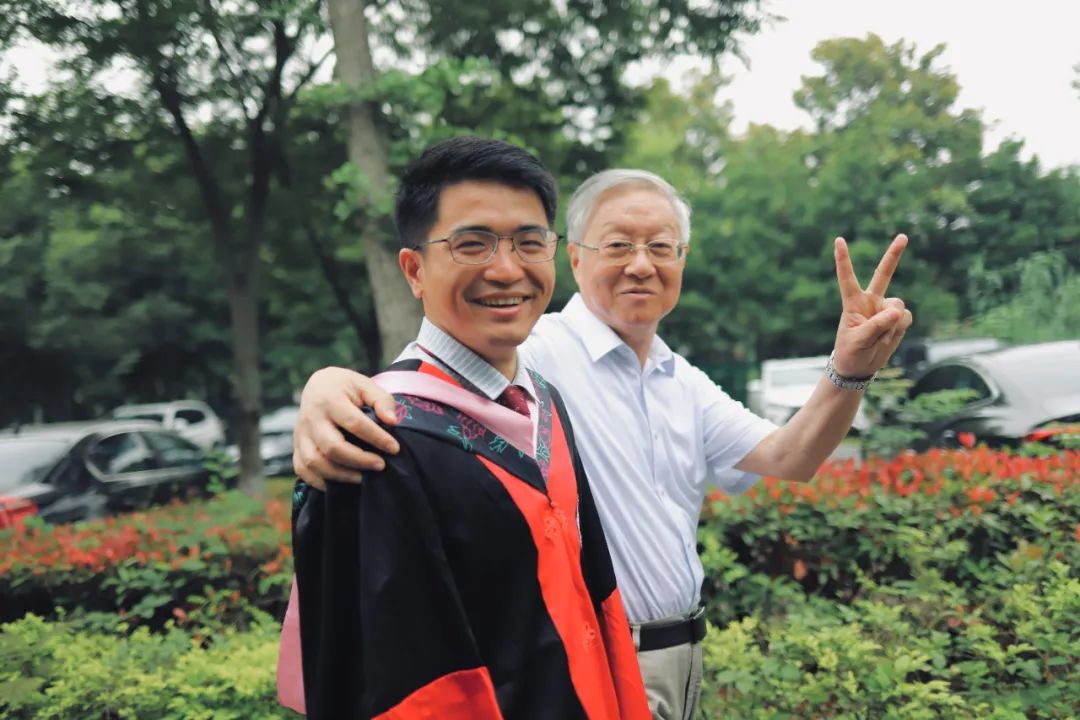
读书是一生大用
初次到莫砺锋家拜访,门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客厅的书柜。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大家,书籍汗牛充栋其实在情理之中,但记者还是忍不住一排排看过去,意图把握一些大师的读书密码。
颇有些意外的是,书柜中不仅有各类学术专著和古籍,也有不少散文、小说等通俗读物。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有一段饮不同酒需用不同酒具的精彩描写,在莫砺锋这里,读书亦然——
学术类书籍需在书房正襟危坐地读;若是躺在客厅沙发上,多半是读闲书;在餐室里独酌时,则常左手持一册诗词选本,右手轮流拿筷子与酒杯,读到好句子时,抿一口酒也别有滋味;枕边书通常只有一本,经常会换;还有“登厕之书”:短篇小说、散文集、科普读物等都很合适,报纸杂志也可充数,纵不能如欧阳修在厕上构思文章,手捧一本有趣的书如厕也是不亦快哉。
他的博士生蒲柏林还记得另一个小细节。“有次到莫老师家里设置电脑,其实没几分钟就需要他来输入一些东西,就这样,我偶一回头,发现他拿起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窗边读了起来。”
于莫砺锋,阅读已是刻入基因的习惯,也是把一切“偶然”化为“必然”的点金石。他说:“是文学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少年时期,莫砺锋是家乡远近出名的高材生——但并非是文科,而是理科。1962年上初二时,他代表学校参加江苏太仓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作文名落孙山,数学却是满分第一名。中考前夕,琼溪镇中学的教导主任动员他报考名闻遐迩的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他一考即中,成为全镇人的骄傲。高考填报志愿,前三个志愿依次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数学力学和自动化控制,他的目光里满满都是理科,梦想里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梦还没开始就碎了。高考取消让莫砺锋的理工梦戛然而止,1968年秋,闲了两年的莫砺锋到太仓县璜泾公社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知青生涯。
时代大潮关上了一扇门,莫砺锋用十年苦读打开了一扇窗。说是苦读,其实是有什么读什么,少年时“好读书”的习惯不仅没有湮灭,反而愈发枝丫繁盛、旁逸斜出。马列著作、中外小说、古籍史料、诗词古文……一本《新名词辞典》也津津有味读了好久,连《气象学教程》都囫囵吞枣地读完了,甚至开始自学英语。
相交多年的王一涓曾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为题,记述她眼中的莫砺锋:“在学习没有任何动力、任何功利的10年中,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成就了莫老师。”
回忆当年,莫砺锋说:“毕竟正在生命力旺盛的青春时代,生活再苦也能扛得住,最让我难受的是缺少书籍。”那时候的他,想必经常会梦回童年,一本《唐诗三百首》是全家人的挚爱。夏日夜晚里,小河边乘凉的莫家兄弟姐妹,与爸爸比赛背诗,颇有些“赌书消得泼茶香”的趣味。
身处困苦之中,青年莫砺锋更能真正体味到那些诗句的力量。1973年秋天,他住了5年的房子屋顶被狂风刮破,重铺屋顶要好几天,“那天夜里,我缩在被窝里看着破屋顶外满天星斗,寒气逼人,四周漆黑一片,正在心里难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温和、苍老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一刻,莫砺锋第一次对杜甫这首名篇中的力量感同身受,一切也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受。“暂将好诗消永夜”,苏轼的这句诗或许正是那无数个夜晚里莫砺锋的心情写照。
斗转星移,重视读书、推崇知识的社会风气早已重新成为主流,那么又该如何读书?
莫砺锋用自己博士第一年作比。虽然是唐宋文学方向,但程千帆先生开出的必读书目却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没有一本是唐朝以后的,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的基本功”。
他还提到大卫·丹比,“在功成名就之后回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发现对他人生最有用的一门课是讲西方文化经典的,于是他回去重读了这个课程,写了一本《伟大的书》,就是介绍这些西方典籍。它们和我们的古代典籍一样,看似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但就像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诗歌尤是如此。
“在当代社会里,诗歌其实是精神上的清凉剂。”几十年过去了,莫砺锋给诗词的定义依然是精神家园,可以给身处钢铁丛林的当代人以精神的桃花源。“其实远方和近处是一样的,所谓诗意的栖居不必走去远方,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这是一种生活的意境,一种境界的追求。”

做人是第一要务
“感谢南大的同学至今没有把我轰下讲坛,使我完整地走完了教学生涯。”5月23日,在最后一课后,莫砺锋说,“作为老师,我觉得自己一直还是兢兢业业的。”
《论语》里写:“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蒲柏林说,跟老师读了6年书,感觉这三句话简直就是他的写照。诚然,包括记者在内,很多上过莫砺锋课的学生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严肃”“不苟言笑”。蒲柏林还记得刚入师门时的惴惴不安,提问时都紧张得牙齿打架,怕问题太幼稚被批评或忽视,“老师会说问题没有好坏,无论是成熟的还是浅近的问题,他都会认真作答,有时甚至还把我们逻辑层次不清晰的问题掰开揉碎讲一遍。”今年毕业的蒲柏林也将走上讲台,在他心中,莫砺锋就是他为师的榜样。
师道确实是可以传承的——每当提到老师程千帆先生,莫砺锋总是津津乐道。
当年,正是了解到程先生也是“弃理从文”,莫砺锋才暗暗下决心全身心投入古代文学研究。读博的两年多是莫砺锋至今仍深切怀念的时光,程先生带他有点像“手艺人带徒弟”,还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先生为助手,四人一起对他“施加友善的压力”。虽然“被压得九死一生”,但总算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学博士。
博士生周斌用“德不孤”来形容追随莫砺锋学习的感觉,“很多道理是可以体悟的,但如果你能看到身边的人就是这么做的,那么自己的信念就会格外坚定,老师给我的就是这种信念。”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莫砺锋的学生们跟记者聊的内容里,学术占比极低,更多是关于做人的言传身教。“纯粹”“简单”“勤奋”“简朴”……周斌甚至还背起莫砺锋写给夫人的诗句,羡慕他们情比金坚的爱情。
莫砺锋应该很开心。因为在他的教育理念里,首先就是做人。他的学生很多都记得,他一直提倡“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如果没有学会做人,那学问做得再好也没有意义”。面对记者的采访,他直言:“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
如今,莫砺锋还是南京大学梅庵书院院长,3年前书院成立时莫砺锋曾说:“更大的意义可能是人格的培养。我们在人格方面要有一种坚持,要有一种操守。将来大家到了社会上,也许有各种力量把你们拉向随波逐流的泥潭,但是我们要有抗拒的力量。”
在莫砺锋眼中,人格提升是一辈子的事情,学校只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头”“培养一种好的倾向”。这也是莫砺锋过去这些年里在社会“大讲台”上大展手脚的缘故,他希望这些东西可以陪伴大家一生,成为人生道路上的指引。

记者手记
追“锋”
2000年坐在南京大学教室里聆听莫砺锋先生讲课时,万万想不到23年后的自己会坐在莫先生对面,完成一次似乎冥冥天定又有些“坎坷”的采访。
5月底在出差途中看到莫先生告别讲坛的消息,心里默默想,这是多么值得采写的一个选题啊。不承想,没两天就接到了《新华每日电讯》的约稿,编辑部还特意强调“想找一位听过莫老师课的记者来写”。
于是,我这个有幸听过几天莫先生讲课,但实际上早已忘得七七八八的不肖学生,幸运地得到了这个美差。
初次给莫先生打电话,是颇做了一番心理建设的。印象中的他不苟言笑,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当年作为本科生,也没有多少主动向老师请教的自觉和勇气,事实上,除了听课,我与莫先生并无交集。
早就听说莫先生不用手机的“典故”,所以得到一个家庭固定电话号码时,倒也并不惊讶。电话那头的莫先生很和蔼,但不巧的是,“这一周我都没空,可能要到下周了。”
那个周末,莫先生出现在《新闻联播》里。原来他是去北京参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了,而且还是发言代表之一。
6月3日,也就是座谈会后第二天,我就在高铁站“堵”到了刚回南京的莫先生。但由于时间缘故,没能进行深入交流,只是简短采访了他参加座谈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想。
莫先生和记忆中的样子没有太大变化,74岁的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一如在课堂或讲座上侃侃而谈的样子。
我则非常忐忑。全然忘了几天前和他的学生们聊天,一群博士生让我不要惶恐:“莫老师变化挺大的,现在都会比‘V’拍照了。”
后来谈及变化,莫先生笑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可能我早年做老师的时候比较严肃,年纪大了以后,可能更放得开一点了。”
好事多磨。莫先生回来以后采访、讲座、报告、座谈不断,我的采访不出意料地延期了。其间甚至有一次已经约好,但因南大中文系有个会,虽然再度和莫先生见面,采访却依然没能进行。
但我也要感谢延期。这段时间里,我翻阅了大量莫先生的自述作品和讲座、讲话,以及一些友人、弟子的文章。再加上和他的学生们聊天,渐渐地,忐忑的心情减退,对于从何处落笔也有了一些眉目。
采访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完成了。一向时间观念极强的莫先生说:“我只有一个小时,你控制一下时间。”所幸,我没让这位“时间管理大师”失望。采访结束后问他如何做到上课、讲座都能精准控制时间、分毫不差时,他笑着反问:“你们喜欢总拖堂的老师吗?”
此刻我已完全放松,答曰:“好老师的课,怎么拖堂都可以。”
但显然,莫先生有自己的原则。采访结束闲聊了几句后,莫先生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差不多了,我要端茶送客了。”
那一刻,我大概也理解了为何他的学生们喜欢用《论语》中那三句话来描述老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同时我也想用另一句《论语》中的话来形容莫先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授业”“解惑”相比,“传道”才是第一位的。对学生,他的要求首先是做人。对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的一言一行,对身边人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传道”。他的学生们一辈子都会记得,毕业那天,白发苍苍的老师带着他们到两个校区拍照,去各个标志性建筑门口打卡,甚至还学年轻人摆比较新潮的姿势,一拍就是一天。
表面是拍照,核心却是仪式感,是“礼”。毕竟,他是希望追随孔子、朱熹等古代先贤和自己恩师程千帆等老一辈先生的脚步,为文化传承做出自己贡献的。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约这就是莫先生现在的状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