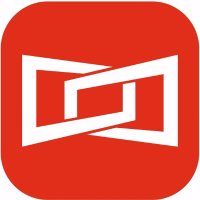文丨罗南·法罗
编者按:2017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以多篇文章揭露了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Weinstein)对数十名女性的性骚扰、性侵行为。记者罗南·法罗(RonanFarrow)在《纽约客》发表的报道,让这本杂志获得了2018年普利策新闻奖“公共服务奖”。法罗后来撰写了《捕杀》(CatchandKill)一书,全面回顾自己调查、报道这些性骚扰、性侵事件的过程,以及遭遇的阻挠、威胁和监视。整个过程扣人心弦、跌宕起伏,揭示了被称为好莱坞“上帝”的韦恩斯坦是如何利用权力与财富来掩盖罪行并让众多媒体噤声的。
该书中文版近日由理想国推出,以下摘自第二部“白鲸”,讲述了NBCNews的新闻主管奥本海姆如何扼杀罗南正在操作的韦恩斯坦选题。这位主管拿出的理由,竟然来自罗南的家庭丑闻——他妹妹指控父亲伍迪·艾伦性侵。
1
我在日落大道东头的一家餐馆见到了艾莉·卡诺萨。她坐得笔直,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就像韦恩斯坦故事中的许多当事人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她的美貌都会引人注目,但这只是在好莱坞工作的一个标准而已。
卡诺萨不确定该怎么办。作为为韦恩斯坦工作的条件,她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她还在努力成为一名制作人,害怕遭到报复。韦恩斯坦可能会让她失业。除此之外,她还表现出任何性暴力幸存者都会有的犹疑态度。她强迫自己的伤口结痂,学会继续前行。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的父亲或男朋友。“我不想再受折磨。你能理解吗?”她对我说道。有一次,她鼓起勇气向心理治疗师提起了这件事。“我在一部韦恩斯坦参与的电影的首映式上见过她,”卡诺萨说道,“我发现她是哈维的一部电影的制作人。”
在10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卡诺萨经常见到韦恩斯坦,当时她在会员制俱乐部苏荷之家(SohoHouse)的西好莱坞分店担任活动策划人。她为韦恩斯坦公司组织了一次活动,他发现了她,盯着她看,然后递给她一张名片。一开始,韦恩斯坦几乎是在跟踪卡诺萨,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见面。当她因为“吓坏了”,没有回应的时候,他强迫她做出回应,借口讨论另一项活动,通过苏荷之家安排两人正式见面。
在蒙太奇酒店,两人的午间会谈转移到了酒店套房,韦恩斯坦先是熟练地对她的职业发展做了一番承诺,然后开始性暗示,向她展开攻势。“你应该当演员,”她记得他这么说,“你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当他问道“你不打算亲亲我吗?”,她表示拒绝,仓皇离开了房间。
她一直尽力想忽视他,但他坚持不放手,她担心如果拒绝他,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同意再次见面。他们在酒店餐厅吃晚餐的时候,餐厅播放了伊娃·卡西迪(EvaCassidy)演唱的《秋天的落叶》(AutumnLeaves)。卡诺萨谈到了卡西迪的人生故事,韦恩斯坦提议由卡诺萨参与协助拍摄一部关于这位女歌手的传记电影。晚餐结束后,他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抵在餐厅外面台阶的栏杆上,狠狠地吻了她。她吓坏了。
但事后韦恩斯坦“极力表示歉意”。“我们可以只做朋友,”她记得当时他对她说,“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拍这部电影。”他给自己的一位资深制作人打了电话,他们很快就跟版权所有者安排了见面,并就剧本事宜交换了意见。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第一年,卡诺萨曾多次无视韦恩斯坦的示爱行为。在一次有关卡西迪电影的会议上,他漫不经心地对她说,他得去酒店房间拿点东西。“当时大约是下午3点,所以,我没有多想。”她说道。但他们到达酒店房间时,他告诉她他要洗个澡。“你愿意跟我一起洗澡吗?”他问道。
“不。”卡诺萨答道。
“只是跟我一起洗个澡。我甚至都不需要——我不想和你上床。我只想你跟我一起洗个澡。”
“不。”她再次回应道,然后走进客厅。韦恩斯坦在浴室里大声宣布,无论如何他都要自慰,然后也不管浴室门还敞开着,就自顾自地动起手来,她则迅速移开了目光。随后,她不安地离开了韦恩斯坦的酒店房间。
还有一次,韦恩斯坦开会时落下了一件夹克,叮嘱她别扔掉那件夹克。她在夹克口袋里发现了一包注射器,搜索后得知那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用的。他在开会前就为上床做好准备的行为让她大为震惊。
那时她正忙于韦恩斯坦制作的电影,她的职业生涯一直以他为中心。他们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即使这种友谊因为双方权力的不平等和韦恩斯坦的非分之想有所扭曲。那年夏天,在一次与同事共进工作晚餐的时候,他为迪士尼将要出售米拉麦克斯公司而落泪。他又一次要求她去他的酒店房间。当她拒绝时,他就朝她咆哮道:“我哭的时候别他妈的拒绝我。”她心软答应了,那一晚什么也没发生。他只是不停抽泣。“我从没快乐过,”她记得他这么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你这么忠诚。”
她希望这段友谊宣言意味着他清楚她的界限。但她错了。
“后来,”说到这里她开始哭泣,“他强奸了我。”第一次是在一家酒店开完另一次会之后。当时他们在讨论卡西迪的项目,他说剧本里的一个场景让他想起了一部经典电影,然后让她到他的房间去看一个电影片段。在这之前,韦恩斯坦已经多次为他的求爱行为道歉,而他毕竟还是她的老板。“我当时觉得,我能处理好这种情况。”她说道。韦恩斯坦酒店房间里唯一一台电视在卧室里。她坐在床上看电影片段,感觉不太舒服。“他开始动手动脚,我对他说‘不要’。他接着动手动脚,我对他说‘不要’。”她回忆道。韦恩斯坦开始生气,变得咄咄逼人。“别他妈装傻!”她记得他说了这么一句。他起身去了洗手间,几分钟后他回来时,身上只穿了件浴袍。然后,他把她推倒在床上。“我一直说不要,他强压到我身上,”她叙述道,“我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的行为明确表明:我不想这么做。而他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
卡诺萨还在思考当时她是不是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当时我脑子里反抗的力量好像不够强大。”最后,她不再说不要。
“我只是麻木地躺在那里。我没有哭。我只是盯着天花板。”直到他离开后,她才开始抽泣,而且无法停下来。韦恩斯坦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几个月前,他告诉过她他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
但她害怕他可能会把性病传染给她。她想把这件事告诉男朋友,但又实在难以启齿。“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拽着一边挣扎一边尖叫的自己直奔警察局。”
卡诺萨继续为韦恩斯坦工作。“我的处境很脆弱,我需要这份工作。”她告诉我。后来,她失去了在另一家制片公司的工作,就跟韦恩斯坦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为电影《艺术家》和《铁娘子》(TheIronLady)策划颁奖活动。
在她忙于拍摄奈飞剧集《马可·波罗》(MarcoPolo)的时候,韦恩斯坦来到马来西亚探班,给她造成巨大伤害。在一次为导演和制作人举办的晚宴上,他当着她的同事的面要求她去他的酒店房间。当她试图回到自己房间时,他的助理们开始对她进行短信轰炸:“哈维想见你,哈维想见你。”有时候,当她躲避他的尝试失败时,会遭受更多攻击。后来的法庭文件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通过强迫及(或)原告由于身体上的无助而无法同意的方式,与原告发生口交或肛交。”
卡诺萨身边的种种迹象表明,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那次探班《马可·波罗》的时候,韦恩斯坦还去一名女演员的化妆间待了15分钟,“那之后的一周时间里,这名女演员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卡诺萨觉得有义务做些什么,但是,韦恩斯坦表现出的报复心让她感到害怕。“我很多次看到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或是他们的妻子受到威胁,或是他们的名誉受到威胁。”她摇着头说道。
我想对卡诺萨坦白这次报道的不确定性,以及她的参与对这次报道的未来的重要性。我对她说,决定权在她手上,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诉她,我真心实意地相信,把这些事说出来能改变很多人,那年夏天我说过很多次这样的话。
2
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工作的这些年,三楼新闻主管办公室外等候室的家具布置几经变化。那年8月,等候区摆着一把矮椅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本几个月前的旧杂志,起到装饰房间的作用。其中有一本《时代》杂志,漆黑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大字:“真理死了吗?”我看着这个封面,然后走到奥本海姆的助理安娜身旁,闲聊了几句。“我猜你们正在做什么大事。”她说道,然后朝我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承诺保密的微笑。
我走进奥本海姆的办公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站起来或挪到沙发上坐着。他看起来有点紧张。“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我问道。我手里握着打印出来的备选新闻选题单。奥本海姆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身体。“嗯,”他拿起一份脚本说道,“我们有一些匿名消息来源。”
“我们正准备重点报道一个女人,我们会拍她的脸,会听到她的声音。”我说道,我指的是古铁雷斯。
他的呼吸声听起来带了些怒气。“我不知道她的可信度有多高。我的意思是,他的律师们会说,他们是在公共场所,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
“可是他承认以前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些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很具体。”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他想摆脱她。无论如何,你在这里写了”——他翻到脚本相关部分——“她的可信度有问题。”
“不”,我说道,“我们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来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说她可信。”
“这份获得批准的脚本上这么写的!”他说道。
“诺亚,我写的脚本。我们正在公开她的经历。可是地方检察官,警察——”
“地方检察官不会同意的!他会说她是个妓女——”
“好,那我们就公开所有东西。我们让公众听一听,然后做出判断。”
他摇了摇头,再次看向脚本。
“这——这东西有多真,说真的?”他问道,我们每次谈话他都会提到这一点。
当我看着他目光下移看向脚本的时候,我觉得他在这个报道受到批评时表现出来的脆弱,一部分是出于一种真诚的信念: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某个在苏荷和戛纳闻名的好莱坞恶霸越界了而已。
“我说过,还有第三名女性指控强奸。诺亚,她快要答应出镜了。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更多人证,我会找到更多人。”
“等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做这些之前是否需要得到法务部门确认。”他看起来有点沮丧,他原本以为事情会更容易解决。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泛着狡黠的光,就像他听录音时那样。
“这就是问题所在,诺亚,”我说道,“每次我们想得到更多,你们就会驳回。”
我的话好像激怒了他。“这些都不重要,”他说道,“我们有个更大的问题。”他把一张打印好的纸拍在桌上,然后向后靠去。
我拿起那张纸。那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哈维·韦恩斯坦同意发行伍迪·艾伦的电影。
“哈维说你牵涉巨大的利益冲突。”奥本海姆说道。
我抬起头。“哈维说?”
奥本海姆的目光又移到一旁。“你知道的,”他说道,“哈维告诉了里奇·格林伯格。我从没跟哈维说过话。”
“但我们都知道,”我疑惑地说道,“格林伯格、麦克休和我搜索发现他跟我父母都合作过,他跟好莱坞的所有人合作过。”
“他在伍迪·艾伦遭人唾弃的时候跟他合作!”他提高声音说道。
“很多发行商都跟他合作过。”
“这不重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姐姐遭到了性侵。去年你在《好莱坞报道》写了有关好莱坞性侵的报道,才引来了这盆脏水。”
“你在说什么?”我问道,“家庭成员遭受性侵的人不能报道性侵问题?”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道,“这直接关系到你的核心计划!”
“你觉得我在谋划什么,诺亚?”我又产生了跟格林伯格谈话时的感觉——我必须单刀直入,因为这是挖出藏在他愿意暗示和愿意说的话之间的东西的唯一方法。
“当然不是!”奥本海姆说道,“但我了解你。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公众的看法,大家会认为‘我让刚成为性侵斗士的罗南·法罗憎恨他的父亲——’”
“我们都清楚他会想办法抹黑我,”我继续说道,“如果这就是他的撒手锏,老实说,我松了口气,你也应该松口气。”
“如果他找到的是你在浴室或其他地方做爱的视频,我会更开心。”他激动地说道。我们之间的友情本可以让我对这个同性恋笑话翻个白眼或哈哈一笑,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现在只是我的老板和新闻网负责人,我为此感到气恼。
“疯了!”乔纳森后来因此发了一通火,“他那么认真地摆出那篇文章,真是疯了。他不是认真的。这不是真正的反对。这可真他妈的虚伪。”后来,我咨询过的每一个记者——奥莱塔,甚至是布罗考——都说不存在什么利益冲突,这不是个问题。
奥本海姆的脸上闪过一丝近乎恳求的表情。“我并没有说证据不够多。这是篇不可思议的,一篇不可思议的《纽约杂志》报道。你清楚你想把它送去《纽约杂志》,听从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的旨意吧。”说完他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动作。
我看着他,好像这一刻他疯了一样,然后我问道:“诺亚,这个报道被毙了吗?”他又看向脚本。从他的肩膀上方望过去,我看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克菲勒广场的装饰风格建筑。
我想到了我姐姐。五年前,她第一次告诉家人,她想重启对伍迪·艾伦的性侵指控。当时我们站在康涅狄格州家中的视听室,手里拿着一堆褪色的录像带。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好好生活。”我对她说道。
“你可以选择这样!”她说道,“我不行!”
“我们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把这件事抛在脑后。我现在正努力做一些严肃的东西,大家都在为此努力。而你想要——想要彻底重置时钟。”
“这跟你无关,”她说道,“你难道没看到吗?”
“不,这跟你有关。你很聪明,有才华,你还有很多其他事可做。”我说道。
“可是我不能。因为过去一直没过去。”她说完哭了起来。
“你不需要这样做。如果你这么做就是在摧毁你的生活。”
“去你的。”她说道。
“我支持你,但你得放手。”
3
奥本海姆抬起头。“我可以站回你们这一边。但现在,我们不能播这个。”
我脑海中响起艾伦·伯格沙哑的声音。“优先处理能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说“好”,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着眼于未来。事后看来,结果不言而喻。但当时,你不知道一则报道会有多重要。你不知道你据理力争是因为你是对的,还是因为你骄傲自负,渴望获胜,不想坐实其他人的想法——你还年轻,经验不足,没法控制好自己。
我看着放在膝头的选题表。我把它抓得太紧,它皱成一团,而且被汗浸湿了。“看起来就像邦德电影中的反派老巢”这些字偷偷看向我。在我视野之外,曙光闪动。
奥本海姆在打量我。他说在NBC新闻的羽翼之下,不能再进行任何工作。他说:“我不能再让你接触任何消息来源。”
我想起电视灯光下的麦高恩说“我希望他们也足够勇敢”,内斯特在阴影中追问“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吗”,古铁雷斯听韦恩斯坦说“我经常干这种事”,安娜贝拉·莎拉对我说“抱歉”。
我凝视着奥本海姆。“不!”我说道。
他看上去有些不高兴。
“什么?”
“不,”我又说了一遍,“我不会照你说的做。停止接触消息来源。”我把手里的纸捏成一团。“很多女性冒了很大的风险说出这一切,她们现在仍然冒着很大的风险——”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提高音量说道,“你关心过头了。”
我思考了一下是否真的是这样。奥莱塔曾说过,他对这个报道有一种“痴迷”。我猜我也是这样。但我同时追问过这些消息来源。我抱持着怀疑的态度,随时准备追随事实真相,不论它们会把我带往何处。我很想征求一下韦恩斯坦的意见,但不被允许。
“好。我关注这件事,”我说道,“我也关心任何进展。我们有证据,诺亚。如果有机会在这种事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之前曝光它,我就没法收手。”我想让我的话听起来铿锵有力,但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如果要我走人,这是你的新闻机构,你说了算,”我继续说道,“但你得告诉我。”“我没让你走人。”他说道,但他再次看向了别处。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他朝我淡淡一笑说道:“这可真有趣。希望我们能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毒水事件上,行吗?”
“行,”我说道,“我猜也是这样。”我站起来向他道谢。
我走出诺亚·奥本海姆的办公室,走进电梯间,途中经过巨大的NBC多彩标识——一只孔雀在说:“NBC现在有颜色了。你能看到彩色的NBC。难道不觉得很神奇?”的确如此。当真如此。我穿过《今日秀》新闻编辑室的格子间,爬上四楼,我嘴里泛着酸,因为紧握拳头,指甲嵌进皮肤,掌心满是红红的指甲印。

——完——
题图PhotobyChaloGallardoonUnspla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