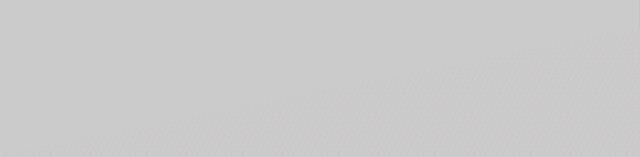
文|文史探索家
编辑|文史探索家

17世纪的海盗被认为是发展中的欧洲大西洋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18世纪的海盗则被边缘化,成为一个与陆地社区几乎没有联系的孤立群体。
这些评估强调了18世纪国家权力对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展,并因此忽视了海盗如何继续与在整个大西洋公域有争议和无人认领的地区活动的殖民行为体互动。
在任何关于大西洋海洋活动的讨论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大西洋公域,因为帝国间、殖民地间和跨国界殖民行为体正是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聚集的.

十八世纪的海盗航行正是在这一公域内通过强制获取补给、通过掠夺货物的市场,以及在探险结束时分散在陆地社区的机会。18世纪殖民地居民和海盗之间的持续联系迫使人们重新评估海盗的孤立性,将他们置于更广泛的沿海商人、旅居海员和边缘殖民定居者群体中.
这些人既存在于国家和殖民中心所支持的帝国框架内,也存在于帝国框架外。最终,这对欧洲国家在船只驶离已建立的殖民地港口、超出帝国当局实际管辖范围时管理海上交通的总体能力提出了质疑。
1720年2月,苏格兰阿盖尔郡的治安官、斯通菲尔德的詹姆斯·坎贝尔报告说,一艘未知船只在阿盖尔海岸中部的克雷尼什湖故意搁浅。更令人怀疑的是,船员们已经离开了船,分开,沿着几条不同的道路分散。

坎贝尔立即派出搜索队寻找船员,同时亲自前往搜索船只。除了一些食物外,他在船上发现的都是一本故意撕烂的日记的碎片。从该杂志幸存下来的笔记中,坎贝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这艘船来自北美新英格兰海岸。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约13名船员在克雷尼什和杜农之间被围捕。坎贝尔写道,除了围绕这一事件的特殊之处之外,每个人身上都发现了莫迪奥雷币——一种葡萄牙金币。被俘船员被关押在因弗雷监狱接受审问。另外八名船员后来在阿盖尔和格拉斯哥之间的不同地点被抓,并被带回因弗雷。
起初,囚犯们声称他们是从达特茅斯开往纽芬兰的,但在他们的“鹰”号船在风暴中受损后,他们被迫驶入克雷尼什湖。坎贝尔写道,除了这些基本细节之外,每个人的叙述都完全不一致。
这背后的原因很快就被揭开了,因为在第二次检查中,一些船员承认自己是海盗,他们在豪厄尔·戴维斯和巴塞洛缪·罗伯茨的指挥下航行,在整个大西洋犯下了数起海盗行为。

这些船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加入了探险队,他们的十九份幸存供词详细描述了1718年9月在伊斯帕尼奥拉海岸附近的一艘小型贸易单桅帆船上发生的叛变引发的海盗航行。
随后,海盗在佛得角、非洲和巴西抢劫了船只,随后一部分船员在沃尔特·肯尼迪(的指挥下离开,前往爱尔兰北部海岸。抵达爱尔兰后,机组人员打算分散并返回爱尔兰和英格兰各地的家园。
然而,在他们的返航途中,一场风暴使他们偏离了航线,这些见解挑战了对18世纪早期海盗行为的主要理解。
17世纪和18世纪大西洋海盗的活动激发了无数的通史,这些通史集中讲述了17世纪中叶加勒比海盗的崛起、1690年代红海海盗的出现以及《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后大西洋海盗的蔓延。在这些研究中,海盗被定位为“他者”

海盗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如果不与一般历史交织在一起,海盗拒绝社会和文化规范以创建替代社会秩序的观点延续了这种“他者”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曲解了海盗在大西洋世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相比之下,将海盗行为置于英属大西洋世界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的学者揭示了海盗与陆地殖民社区的广泛同化,以及这些联系对17世纪殖民发展和帝国政治的后续影响。通过研究殖民地官员、商人、定居者和海盗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些研究表明,海盗在殖民地社会的边缘活动,而不是反对或抵抗殖民地社会。
虽然这项研究坚定地将海盗重新塑造为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里,海盗航行在殖民地港口得以实现并得到支持,但1716年至1726年期间海盗的兴起和衰落并未受到同样程度的审视。
相反,有人认为,18世纪的海盗在一个敌对的大西洋世界里活动,不再支持非法的海上掠夺。

从这个角度来看,海盗活动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国家的操纵使和平时期的商业掠夺失去了合法性,摧毁了海盗,并刺激了对海盗活动的殖民赞助的减少,描绘了英国殖民地从海盗巢穴转变为生产力和自我维持的社区的过程,这些社区拒绝了非法的海上掠夺,并进一步与大都市联系起来。
这一转变发生在殖民商人获得合法进入市场的时候,这些市场以前曾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处于垄断控制之下,特别是非洲奴隶贸易。
汉娜认为,这些变化的结果是,海盗不再是大西洋经济的一个必要和被同化的部分,无法维持下去,汉娜为殖民地支持是帝国政策总体成功的核心这一论点提供了新的证据,因为英国政府从未能够有效地对其大西洋领土实行中央集权管理,虽然很明显,随着殖民地社区在本世纪初与大都市紧密结合,一个更加连贯和联系的不列颠大西洋帝国出现了。

但重要的是不要夸大这一点。尽管殖民地接受国家权力使已建立的港口城镇进入了一个更为连贯的框架,但这种权力不能也不可能延伸到殖民地中心附近的海岸之外。
在17世纪和18世纪,无论是国家还是殖民地中心都无法有意义地支配大西洋的海洋活动和贸易。
在18世纪早期,国家权力扩展到许多殖民地港口,大西洋贸易继续受到大量个人交易的驱动,这些交易仍然是分散的、自我组织的和机会主义的,由跨大西洋和跨帝国市场和联系推动,而不管国家重商主义政策如何。

与每个殖民地中心的服从和同意对于跨越大西洋的国家权力的延伸至关重要的事实类似,海上活动对殖民地中心权威的服从主要取决于个人行为。
殖民主义者经常选择在这些中心所支持的法律商业框架内和外部开展活动,因为无论是大都市国家还是各个殖民地都没有可用的资源来巡逻和管理整个大西洋的海上活动。
帝国对海洋空间的权力扩展仅限于特定的海上航道,而不是广阔的海洋区域。事实上,由于严重缺乏国家提供的海上防御,即使是已建立的殖民地的直接邻近地区也难以防止海盗袭击和非法贸易,当船只越过殖民地海岸航行时,几乎没有能力监管海上活动。因此,交易者经常违反重商主义的限制,以获取利润和机会。

这种特别的海上活动发生在无人认领或有争议的国家以外海域,特别是在大加勒比地区,那里没有欧洲帝国官员居住以执行帝国政策和限制。
贾维斯称之为大西洋公域。在这里,水手们定期航行,有时定居下来,以便耙盐、打捞沉船、捕猎海龟、收获海洋资源和走私货物。
海盗也利用了这些空间。然而,海盗利用的公域不仅存在于大加勒比有争议和无人认领的地区,也存在于北美未受保护的海角、非洲脆弱的海岸线、整个大西洋的欧洲外围前哨,甚至大西洋水手聚集的印度洋海域。
为了解释这一点,贾维斯的公域框架在这里被广泛地用来指代欧洲帝国权力没有延伸但欧洲臣民相互作用和聚集的主要沿海地区。

这些公域虽然完全融入了分散和自组织的大西洋经济,但却超出了国家或殖民地官员的监管范围,因此在大西洋世界的考虑中经常被忽视。
考虑到18世纪的海盗行为,这些空间也被忽视了。例如,在考虑海盗巢穴的改造时,汉娜表示
“在那些曾经给予海盗合法性或至少是容忍的地方,大多数殖民社区现在都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不法分子。”
但汉娜没有评估海盗与殖民港口的隔离是如何改变海盗发起、维持和结束航行的方法和策略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海盗航行如何利用大西洋公域不仅掠夺,而且与殖民者和殖民地社区互动进行详细研究。即使是承认这种互动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历史学家,也没有解释这种接触发生在何处以及如何发生。
例如切特表示,“尽管英国人在18世纪努力使海盗和违禁品贸易合法化、非法化并加以压制,但他们仍继续从事和支持海盗和违禁贸易”,但没有提供证据或分析这种支持的手段和方法17世纪的那些。
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航行在整体上要容易得多,而是海盗航行主要开始、装备和结束的方式在17世纪比18世纪更为明显,当时海盗被欢迎进入各个殖民地港口,并从各个殖民地的港口进行活动,当航行在大西洋公域的无人注意的空间开始和结束时。

因此,关于18世纪大多数海盗航行的信息都是极其零碎的,很难核实。本文中讨论的航行提供了一个罕见的例外,因为它可以通过船员的供词从一开始就绘制到多个结论,与大多数其他海盗航行相比,它们数量更多、更详细。
此外,这些多份供词中提供的细节使我们有可能汇编涉及同一船员的大量受害者证词和殖民地报告,这些证词和报告证实并加强了被俘船员提供的信息。
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海盗主要在大西洋公域的那些区域活动,这些区域是航运聚集的地方,但这些区域要么是有争议的,要么是无人认领的,要么不受帝国权力的保护。

殖民地战区海军舰艇的总体短缺意味着这些地区没有定期巡逻,即使海军舰艇被派去寻找海盗,其信息也常常过时。在遇到海盗时,大型海军舰艇往往无法通过浅滩和浅水区追击小型海盗船。
因此被证明无法有效地压制海盗,除了积极护送从事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贸易的贸易船只外,这意味着在重要的殖民地港口附近以及在主要的殖民地航线上遇到和捕获船只对海盗来说是有问题的,他们转向那些使用贸易船只但没有武装车队或海岸防御工事的地区。
17世纪的海盗,是为了财富,为了自由而冲向大海,时间到了18世纪,这些海盗们已经完全成为了大国手中的工具,他们向往的自由也被这些帝国所剥夺,但是这也怨不得别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