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许钧
法语文学翻译大家、浙江大学教授许钧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是当代文学经典。近日,他的随笔集《译路探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谈谈对文学翻译的思考。本文节选自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原小标题为《开放的精神引导我走向“他者”》。

大学毕业从教已经整整48个年头。1975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1976年8月,我被公派去法国学习。两年之后的秋季,我回到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我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就在这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真正开始了。

许钧
在我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去法国学习是个很重要的阶段。我手头还保存有在法国留学时用法语写的几本日记,其中不少记载了我对语言与文化的一些思考。留法期间,我很注意收集有关法语新语言现象的材料,这对我早期的法语研究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时,我也很关注法国的文学与文化。留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我读了不少法国经典文学作品,还经常到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去淘书。那里书很多,品相很好,价格特别便宜。

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我们当时在法国的吃住行都是国家按一定标准包的,此外国家每月给我们发十元钱的零用钱。两年下来,我用这点零用钱,竟然买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像古典主义时期的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和卢梭的代表作,还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自然主义的左拉、意识流的普鲁斯特等重要作家的小说。虽然我不太喜爱诗歌,但也买了不少本,像雨果的《静观集》,兰波、瓦莱里等伟大诗人的诗集。

许钧与法国文学家、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合影。
除了经典作品,我对法国当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化现象尤其感兴趣,像萨特、加缪的小说,尤内斯库、贝克特的戏剧,新锐作家如勒克莱齐奥、图尼埃的作品,我都接触过,似懂非懂地听到了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这些流派的名字。对法国太阳剧社的活动,我有过特别的关注,因为我很喜欢,觉得他们的演出离观众很近,与观众有直接互动,觉得还真是用戏剧为人民服务,实在了不起。
当初的用心,听过的课,收集过的材料,买过的书,看过的作品,就像埋下的一颗颗种子,遇到好的土地,遇到雨露,尤其是碰上好的季节,迟早会发芽的。我就是这么幸运,两年的学习结束后回到国内,恰逢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开端。
对于拨乱反正的意义,一个刚刚归国的青年学者不可能有深刻理解,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在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不小的共鸣,有着一种朴素但强烈的认同。

马奈绘画作品。
之所以说强烈的认同,是因为我有到国外留学的经历,在法国学习到了一些新知识,读到了很多我感兴趣的文学佳作,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我的所闻所见、我学到的新东西讲给我的同行听。国家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国家发展决策,更是一种思想观念的重要转变,一种走出封闭、走向宽阔世界的积极行动。
邓小平英明决策,在1975年恢复留学生公派,我猜想这对邓小平而言,也许是一种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高度的人才培养举措吧。他在1975年出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也许就已经在心里有了改革开放的蓝图。改革要从开放做起,没有观念的转变,改革不可能迈出真正的步伐。
对我而言,开放,就意味着向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的长处学习。从法国留回来后,我自告奋勇地向我所在的教研室的老师们提出,要就新学到的知识给他们做一次学习汇报。这一次汇报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我做了认真准备,就法语近年来出现的新语法现象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老师们听了之后,给了我充分的肯定,杨振亚老师还笑眯眯地对我说,应该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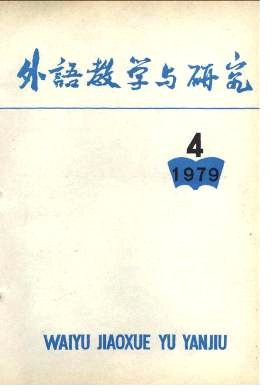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四期。许钧的论文《对〈法语中近年常见的一些新语法现象〉一文的一点看法》发表在本期杂志。
在他的鼓励下,我真的写了下来,于是有了自己在1979年给《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投稿并被录用的第一次学术作品发表经历。如今回想起来,我学术人生的第一次以汇报为名的“讲座”,还有学术性小文章的第一次发表,都与我积极开放的心态,与我那种希望交流的强烈动机相关。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单位组织听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又学习讨论的热烈情状。
改革开放,就要像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那样,“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有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我们不仅可以客观地评价外国的长处,还要勇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有了这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心底埋下的一颗颗种子渐渐发芽了。

最先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的,是我在法国读到的那些文学作品。法国有悠久的文学历史,远的不说,19世纪的文学对中国读者具有强大吸引力,像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左拉的代表作等。20世纪,法国文学气象万千,各文学流派呈现出鲜明特质。在1978年前后的一两年,国内几家比较有前瞻性的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一些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引起了一股外国文学热,常有一本书出版后读者排长队竞相抢购的场面出现。
面对当时涌动的外国文学阅读潮,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特别想把自己喜欢的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在纪念《外国语》创刊四十周年的文章里,我曾谈到在那个时期,我迷上了翻译。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名著,不是谁想译就可以译的。那个时期,重印的外国文学经典,都是老一辈翻译家的名译,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的译本,还有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作品。名著,我想也不敢想。我琢磨着,名著没有资格译,公认的好书轮不着我去译,那我能不能自己去选择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第一时间把它翻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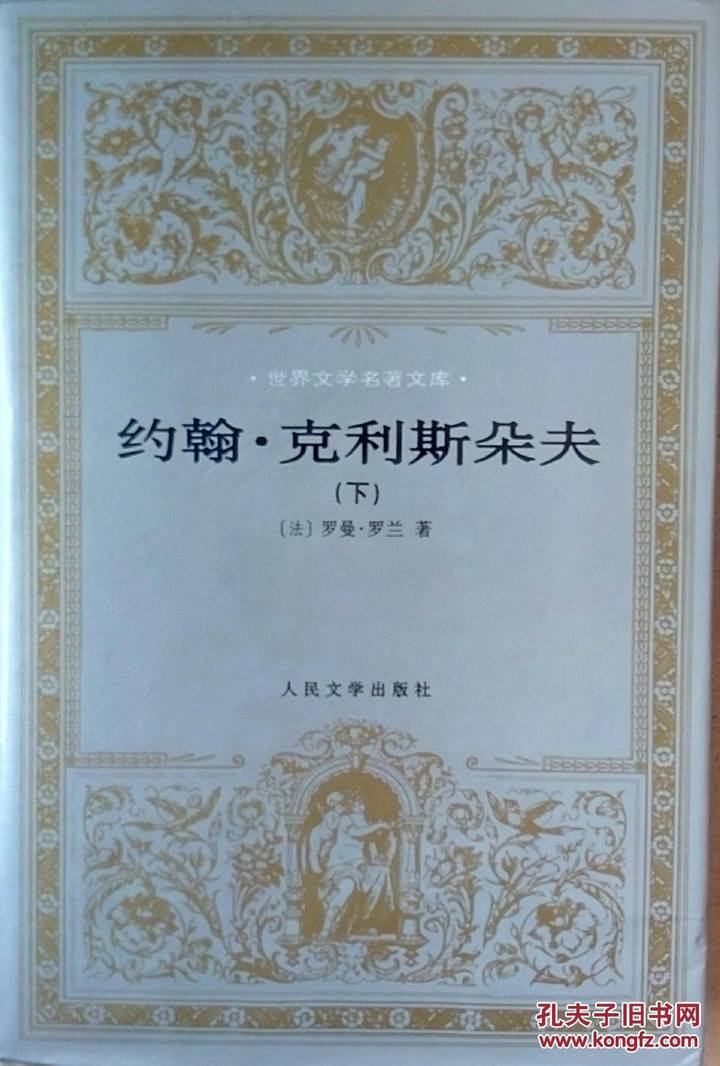
《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可是,我人在军校工作,除了在塞纳河畔淘到的几十本文学名著,因纪律所限,我没有渠道获得法国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为此,我想到了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他是我在法国学时认识的,当时他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中文,与许多汉学家有很深的交情。当我和他说起翻译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想法时,得到了他的鼓励,他说会帮助我去寻找好作品。
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钱林森老师通过法国友人,得到了在法国当年获法兰西学院奖的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叫《永别了,疯妈妈》。看到书,我如获至宝,真想马上动笔翻译,可是钱老师告诉我,要先读原著,如果觉得有价值,再写出一万来字的小说详细梗概,寄给出版社,出版社觉得感兴趣的话,就再试译两三万字,出版社全面审查后才能做出接受不接受此书出版的决定。

照着钱老师的吩咐,我一一都认真地做了,钱老师修改了梗概,又修改了试译稿。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当我得到出版社的正式答复,同意接受该选题时,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从1980年夏天选题被接受,到1982年译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后经历了两年时间。近四十万字的小说《永别了,疯妈妈》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赞誉,《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主流媒体与重要的学术刊物相继发表评论文章。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给我写的信,表达他们对作品的喜爱和对译者的感激,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外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