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相思》设定山海经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为故事背景。去年第一季播出即引发观剧追剧热潮,今年播出的第二季直接衔接第一季的结尾。有人嫌剧情拖沓,也有人被剧情“虐”。图为《长相思》第二季(2024)剧照。
小夭给人一种既自主又被动,既清醒独立又举棋不定的印象。她似乎积极参与政治,却因内心苍凉而缺乏明确目标;她口头上不断强调自己不会主动付出,实际上又在为玱玹、相柳、涂山璟等男性角色肝脑涂地。这种矛盾感确实带来了戏剧冲突,同时也让观众觉得“不对劲”。
小夭的这种纠结感,源于女性根本失权的设定。当亲密关系成为女性角色展示主体性的唯一舞台时,作为弱势的一方,其主动性往往只能通过自我牺牲来实现。这种虐女叙事增强了“从暴力到温柔”的传统男性气概构建,女主通过被虐获得“道德货币”,积累道德快感,而男主则通过悔改展现迟到的温柔,最终被观众赦免。
然而,当女性受众开始察觉到虐女叙事背后两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并对女性角色的自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时,什么样的女主角既能展露真情,又能通过不被虐的方式施展主动性,成为了新的问题。或者说,女性的爱欲表达需要超越虐女叙事,探索新的叙事模式来重构女性角色,使其在爱情、友情和自我实现中都能展现出独立和坚韧。
撰文|猪迅儿
“奉献之爱”:女性的“自我剥削”或“情感超越”?
小夭这一角色的拉扯感可能源于其成长的基础皆为某种排他性的亲密关系。对任何个体而言,深入的亲密关系都是自我认知和成长的重要途径,它带来了高度的自我暴露以及与他人的深层互动。但是,小夭在亲密关系中往往是牺牲付出的“被虐”的角色,常常经历极端的情感波动,感受刻骨铭心。然而,在以“女性受虐”为前提展开的故事中,女主应被视作自我剥削的“圣母”,还是实现了“情感超越”的体验王者?
在《长相思》的设定中,小夭实际上处于一个失权的位置,因此,她纵使有心建功立业也灵力尽失,无法作为。当女性在公共空间内无法大展拳脚时,爱情似乎会成为唯一的秀场。正如易洛思(EvaIllouz)在《爱,为什么痛?》中的分析:“浪漫爱”作为女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失权的安抚,承诺了女性能够享受更优越的道德地位和尊严。通过“浪漫爱”,女性以种种社会中的劣势换来了男性的保护与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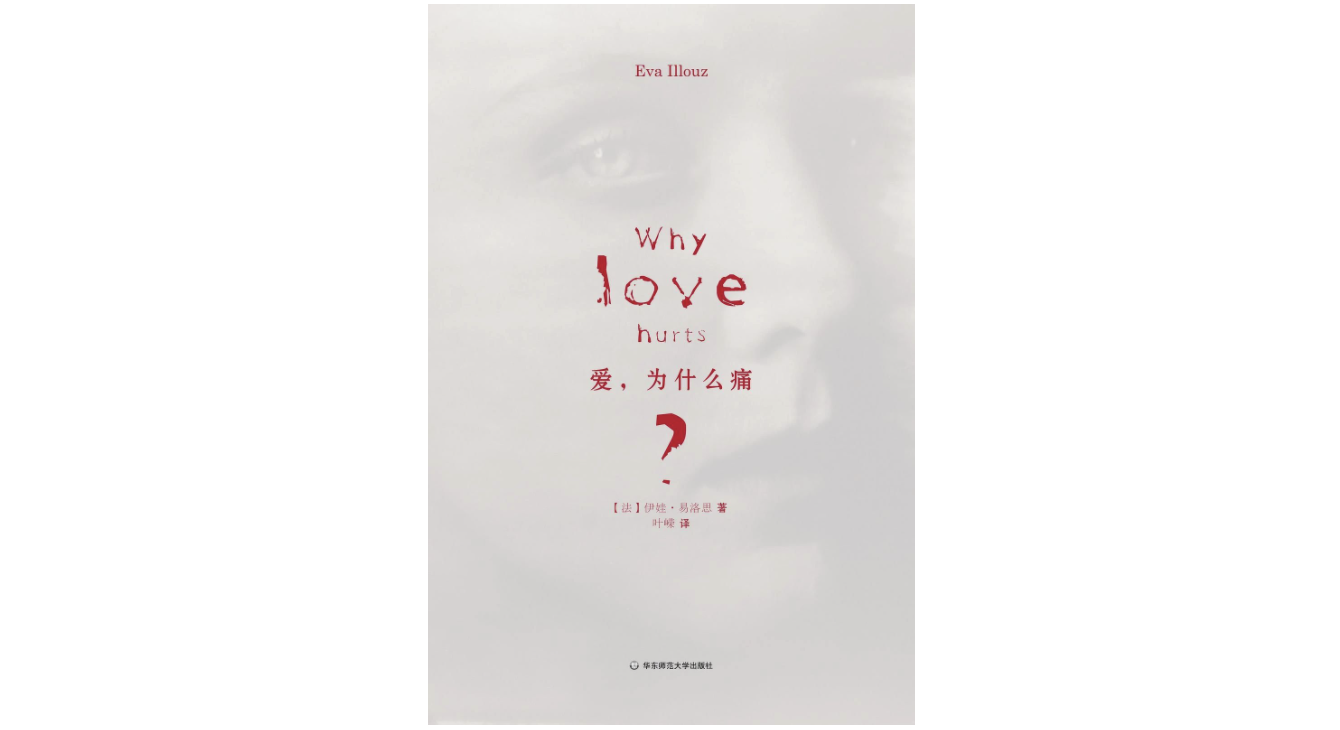
《爱,为什么痛?》,[法]伊娃·易洛思著,叶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在“虐女”的爱情叙事中,男主通常被塑造为对女主一往情深但被“大义”耽误的角色,他们经常为了一个宏伟的政治目标而反复伤害深爱的女主。女主则极具同情心和人性美,用爱超越伤害。虐女爱情叙事的“凄美感”源于现实之痛与理想之爱间的极致拉扯。“惜我余生”精准地概括了这种脚本中两性角色的特点:男性是“政治动物”,女性是“神女”。前者的核心是“争”,即宏大叙事下身不由己的权力争夺,后者的核心是“爱”,即对个体和众生悲悯包容,厌倦权力斗争。
“政治动物”不是不懂“神女”的人性之美,只是在感情的前期,他的目光总被世俗的权力所吸引,因此冷酷暴虐地应对“神女”爱人。但当他彻底失去爱人时,一定会幡然醒悟,痛心疾首,这就是俗称“追妻火葬场”的脚本。对应到《长相思》中,就是相柳和小夭的关系。相柳从最初对小夭随意打骂,施以酷刑,转变为日日相思,并在小夭死去后,用“心头血”舍命相救。更为典型的例子还有电视剧《步步惊心》,其中男主雍正在看到女主若曦绝笔“从别后,嗔恨痴念,皆成相思”后,心碎不已,孤寡一人,郁郁而终。
值得注意的是,“追妻火葬场”类叙事增强了“从暴力到温柔”的传统男性气概构建。在《阅读浪漫小说》中,作者拉德威(JaniceA.Radway)指出,拥有男子气概但不失温柔深情的理想型男主最终认识到女主的内在价值,女主自此放心地交出自我控制权,除了保持贞洁外,不再需要做任何事。

《阅读浪漫小说》,[美]珍妮斯·A.拉德威著,胡淑陈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7月。
正是这种独特的“被动性”(passivity)让人欲罢不能。虐女爱情叙事虽然不追求拉德威要求的“必定美满的爱情结局”,但它同样是“被动性”的艺术。被动的“神女”在没有攻击性的同时又能“勾引”出对方的“主动性”——“神女”总是用爱包容“政治动物”,而“政治动物”在失去“神女”后会自发地痛彻心扉。
虐女叙事限于恋爱关系之中,它的魅力却源于完美地处理了传统浪漫小说脚本中核心矛盾:女主到底为什么能够以及是如何把一个男人的残酷转化为迟到的温柔和深情的。男主对女主的暴虐和冷酷都被归因于误会或宏大目标之下的迫不得已,比如玱玹和小夭最初相见时,玱玹护短,于是对她实施酷刑。男性角色的一切残酷都是追悔莫及的前奏,最终都将被转化为迟到的深情与追忆,当他知道小夭就是他走失的最心爱的妹妹时,不仅追悔不已,而且时时刻刻都要在一起。总之,在前期,“神女”通过被“政治动物”虐待获得“道德货币”,“政治动物”则反过来通过透支“道德货币”获得世俗成功。但在关系的末期,“政治动物”总会悔不当初,于是被观众赦免。同时,“神女”或许香消玉殒,但却坐拥“道德高位”,自我带入的观众由此享受道德快感的盛宴。

电视剧《长相思》第二季(2024)剧照。
不可否认,虐女爱情叙事需要与观众的自虐情结相结合才能带来自我剥削的愉悦感。“惜我余生”将这种愉悦概括为:女性以纵容被伤害为筹码,以伤害者的痛悔和回头为期待,所获得的精神胜利。它的前提是对女主处境的全方位“弱化”,她因为无法自强而只能慕强,只能被动地期待强者能够分享自己的痛苦。然而,这是违背人性的。小夭完全无力向上的处境与主动的真情付出,这便是她展现出自主又被动的“拉扯感”的根本原因。
但是,虐女叙事吸引观众的仅仅是“虐女”吗?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种叙事中被捧上高位的是女性的“真情”。真情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可能挣脱世俗成败,获得“超越性”,成为“独一无二”的原因。或许正是这种对超越性的向往,时常使观众忽视世俗之中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存在以及自强与抗争的意义。
小夭:“败者组”的觉醒与挣扎
或许正是因为虐女爱情叙事中既存在着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美化,又歌颂了真情,这才使女性观众既着迷又察觉“不对劲”。在当下,女性应对爱情中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方式是趋向独立自主,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这在影视创作中反映为主创们努力塑造“搞事业”的“大女主”角色,在仙侠古偶剧中也是如此。
然而,这些“大女主”在能力、人格、情感三者之中往往存在欠缺,自身无法独当一面,总是需要男主的天降神助才能完成任务。例如,在今年火爆的电视剧《一念关山》(2023年11月播出)中,女主任如意虽然被设定为武林第一高手,但在包括营救养母等故事线的多个关键节点中,被强行弱化,总是等待着男主的救场。

电视剧《一念关山》(2023)剧照。
仙侠古偶剧虽然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但其内核价值应当与当下时代的趋势相符,那么就应当借鉴更为新鲜的思想以塑造女性角色。河野真太郎在《战斗公主,劳动少女》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当代女性的双人肖像,试图概括“觉醒女性”的境况。他以201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样本,对“觉醒女性”进行了分类和分析。故事的主角是阿伦黛尔王国的两位公主,姐姐艾莎和妹妹安娜。她们分别代表了“觉醒女性”的“胜者组”和“败者组”。艾莎和安娜的选择象征了女性“出走”的两种模式。
许多以性缘关系为核心展开叙事、以“大女主”为噱头的影视剧,往往试图在女主角身上统一这种双人肖像。这种叙事模式既试图迎合观众对独立女性的期待,又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性别角色设定,它与观众的情感共鸣一样复杂。
艾莎代表了“胜者组”。从一开始,异性爱情就不在她的人生规划之中。她的抉择正如本片主题曲《Letitgo》,她不仅逃离了不可名状的父权家长制,在随后也未与任何男性产生情感关联,一心只想建立冰雪帝国,最终也只被安娜的姐妹情打动。

动画片《冰雪奇缘》(Frozen,2013)画面。
在现实生活中,“胜者组”是所谓的“人间清醒”,她们通常呈现出“人生赢家”的状态,比如《向前一步》的作者桑德博格(SherylSandberg),她的作品和人生构建了一种互文,展现出“觉醒女性的理想人生”。这是成功出走的“娜拉”,在她们的视野中,“爱情”甚至不是一个重要选项。她们看透了大部分爱情的本质仅仅是权力关系,因此将注意力聚焦在公共领域之中发展事业。在中国的网络女性主义话语下,“胜者组”的终极版本是所谓的“又美又有力量又不沾男”的清醒女性。这种过于严苛的要求,使其可能成为规范和规训女性的新模板。
安娜则对应着“败者组”。这里的“败者”看似是对人生成就的判断,实际上,它主要关乎“出走”的失败。安娜最初像每一个普通的迪士尼小公主一样期待“真命天子”,于是遇见了滥俗的“白马王子”角色汉斯。安娜为了汉斯气走艾莎,但又在姐妹情的驱动下,开启了寻找艾莎之旅。随后,两人相见却无法冰释前嫌。同时,汉斯的真实意图暴露,他接近安娜的真正目的是占有她的王国。此刻,异性恋之间的“真爱叙事”宣告破产。
安娜所追求的真爱是虚假的,她也没能带回艾莎,她的“出走”失败了,这象征着大多数普通女性的处境。更准确地说,当思想没能完全解放时,“出走失败”是人生常态。因为成功的“出走”,不仅需要“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还要实现“情感独立”,即无论是否恋爱,都能充实丰富,独善其身。当下女性对于爱情的过度美化和依赖,既反映了她们缺乏“情感独立”,也使她们难以实现“情感独立”。然而,独自面对孤独本就是人生最具挑战之事,因此这种“失败”并不羞耻。
但是,没有封心锁爱,就是“败者”吗?或者更具体的问题是,仙侠古偶的创作是否只能局限于“败者组”叙事?事实上,单独展现“胜者组”和“败者组”的典范并不能为当代女性提供生活参照。《冰雪奇缘》的答案是通过姐妹情谊实现和解——安娜为救艾莎放弃了“真爱之吻”变成冰雕,而艾莎用一个拥抱“唤回”了安娜的生命。
而仙侠古偶剧当下的策略是将“胜者组”的独立意识和“败者组”的真情体验集于女主一身,然而,过于依赖围绕异性恋浪漫爱展开的落后虐恋情感逻辑,导致这类大女主的形象总是摇摇欲坠,或是充满不融贯的缝合感,但这或许也折射出了观众的觉醒与挣扎。观众的复杂反应是最应当被正视的,他们的“挣扎”不仅表现在对角色形象的期待上,还表现在对剧情发展和角色关系的思考中。
古偶“大女主”:恐惧爱、渴望爱
在根本上,古偶“大女主”剧所承载的实际上是当代女性的“爱欲”困境。问题在于,当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昭然若揭,同时爱情也已不再是展现女性主体性的唯一选择时,应当如何塑造一个渴望被爱同时独立自主女性。

电视剧《长相思》第二季(2024)剧照。
换个角度看,《长相思》等讲述虐恋浪漫故事的电视剧,如今似乎也试图构造一种围绕着女性视角展开的“新玛丽苏”故事。或许我们需要先为“玛丽苏故事”正名,毕竟它一度被污名化为女性粗制滥造的蹩脚意淫。实际上,这一题材中不乏为女孩们构建“RoleModel”(模范)的佳作。“玛丽苏”是一个舶来概念,英文是“MarySue”,在经历了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后,它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万人迷式的全能女主”。
帕特·普菲列格(PatPflieger)在《“好得不真实”:玛丽苏的150年》一文中梳理了西方的玛丽苏形象从19世纪“受他人崇拜的被动对象”到20世纪“积极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能力赢得掌声”的转变。(见文末文献4)中国的玛丽苏形象也在不断发展,张韶玥认为,这类故事的发展趋势所体现出的是“女性日渐高涨的自我意识与现实社会的父权制秩序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小夭是某种“自主玛丽苏”的代表,小夭在前期流落尘俗阶段,作为小六的时期,经营医馆,治病救人,守护身边众人。随后,当她恢复真容成为王姬后,被卷入政治斗争,同样有勇有谋。可惜的是,她的生命核心只有“真情”,全无现实。
另外值得赞赏的是,《长相思》在对男性角色的塑造上也进行了创新的努力。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理想型男主的塑造,以及两性之间的情感互动方式的变化上。根据张韶玥的研究,在21世纪流行的玛丽苏小说中男主角形象可以分为“威权型”和“奉献型”两类。前者作为女主的最终归宿,常表现为一个注定“追妻火葬场”的暴君,相柳就是这类角色的典型;后者则温柔体贴、为女主付出,但往往在男主获得相应职能后在情感竞争中默默退出。
在一定程度上,涂山璟和玱玹都在类型角色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创新的探索。玱玹属于“威权型”男主,但他和女主的羁绊主要展现为亲缘关系而非性缘关系,展现了两性在浪漫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再次落入了“政治动物-神女”的叙事模式中,小夭注定受虐。涂山璟则是剥除了“有毒男子气概”的“弱男”。他怯懦敏感,但尊重他人,对所爱之人的同理心不亚于小夭。最重要的是,他能真正倾听和理解小夭的诉求,而不是霸道地坚持“我觉得”。在涂山璟这里,小夭想要的“真情”是最能被感受和共鸣的。
除此之外,仙侠古偶剧在塑造自主女性角色方面还存在两类限制。一方面,女性的独特生命力和变革潜力与女性被压迫的处境重叠过深,大部分仙侠古偶电视剧缺乏剥离二者的意识。然而,金庸笔下的黄蓉却展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男权社会作为先决设定的情况下,观众能看到完整的黄蓉视角,并由此展开思考:郭靖之所以能成为郭大侠,是因为在男权社会中,黄蓉需要靖哥哥这样一个“话事人”来施展她的野心。
另一方面,或许创作者和观众都应该意识到,“真情”不只有爱情,亲密关系也不只有两性关系。女性对同性情谊的感知和体验同样值得深入刻画,而非徒有形式。女性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中似乎带有一种直接的信任感。她们关心对方的真实生活,希望彼此能够“好好活着”,而非追求某种与“共赴死亡”相关的浪漫化理念。女性友谊更多是“感知”这一情感纽带,并沉浸在这种平等真诚的体验之中,而非刻意地去“证明”它。她们的友谊并不强调宏大叙事下的壮烈牺牲,而是更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真挚相伴与相互支持。

电视剧《步步惊心》(2011)剧照。
在女性友谊中,所谓的“自然”的平等真挚之感,并非单纯由生理特征决定。其实,这更可能是源自权力关系对个人的深远影响。比如《步步惊心》虽然同样蕴含着虐女逻辑,但它通过女性视角提供了一种对“真情”的独特想象和解释是值得借鉴的。穿越为贵族小姐若曦的现代女性张晓一直在坚持以未被封建权力异化的态度对待他人。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情发生于她与宫女玉檀之间。若曦对待处于权力下位的玉檀时,展现出一种自我约束的平等之感——约束自己不受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这种“真情之谊”植根于“平等”,是一种本真的信任,它超越工具理性,直接对他人的存在进行感知。若曦和玉檀“不假思索”地照顾彼此,倾听对方的目标,严肃地思考对方的福祉。
中式女性情谊中流淌着的是一种温柔而深邃的平等,真情在人际交往中被放在了最高的位置。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角色的塑造只能局限于建立同性友谊,而是启发了创作者和观众,去塑造和理解性缘关系之外的多元关系。这或许就是“爱欲”困境的出口——爱与被爱与性别无关,只与真情和平等相关。在展现真情的前提下,抛弃虐女叙事,能更好地着墨于女性真正的主动性和决策力,描绘出更真诚自洽的女性自我。
参考文献:
[1]伊娃·易洛思著,叶嵘译,《爱,为什么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2]《“虐女”的爽感从何而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自虐”和“追妻火葬场”?从《长相思》漫谈国产影视剧离不开的虐女与自虐情结〉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u411J7zq?vd_source=afbb0cc81b8265b7dc68ec377d1329f4
[3]珍妮斯·A.拉德威著,胡淑陈译:《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4]PatPflieger,“Toogoodtobetrue”:150yearsofMarySue,AmericanCultureAssociationconference,March31,1999.
[5]张韶玥,《轨迹、人物、题旨:2005-2010年的网络“玛丽苏”小说》,华中师范大学,2023年。
撰文/猪迅儿
编辑/走走西西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