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易禹琳
10月10日清晨,微信又蹦出一条消息,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公布,残雪位列诺奖赔率榜首。这样的消息2019年就出现了,年年来一次。
去年湖南人还“严阵以待”,过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过一年,残雪又再次让无数人“我心狂跳”。今晚,残雪到底会不会中奖?湖南人的心跳得起来越急。
21年前采访残雪时,我认为她是个巫婆,写的文章是《向一个真正的巫婆致敬》,后来残雪把我发给她邮箱的采访提纲都拿出来在网上发表,估计她也觉得自己算是个巫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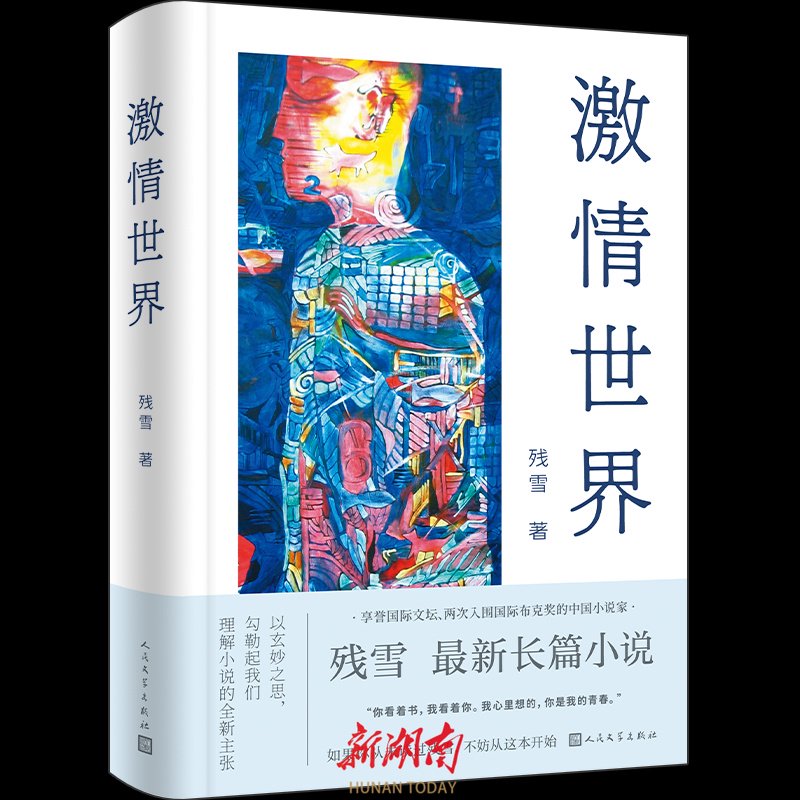
但巫婆总在变,自她从北京住到云南去后,也许温暖的南方融化了一些“残雪”,去年,我在书店竟然看到了她的新小说《激情世界》,赶紧看了电子书。她竟一反向来的阴冷,讲的是几对恋人通过读书了解自己和世界,展现了寻找情和爱的过程。私下认为这是最好的劝人阅读的书,岳麓书会咋不重点推荐呢?不过残雪这本书也招致了一些另外的声音。
但谁说巫婆就不能展现温暖的一面?尤其是年过古稀的巫婆还在寻求创新,我们应该鼓掌。
来,我们一起期待今晚吧!如果“巫婆”得了诺奖,她会是怎样的表情?
附:《向一个真正的巫婆致敬》
文|易禹琳
残雪是一个巫婆,谁会拒绝对一个巫婆感兴趣呢?何况残雪是个真正的巫婆。
说残雪是个巫婆,残雪本人没有反对———她没有理由反对!
她的小说所取的环境都是那些阴冷、黏湿、腐臭的地方,就像一个巫婆总是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她不愿意走出自己的世界跟别人沟通一下,说一走出去就破坏了她的世界,就像一个巫婆死也不肯走出她的山洞。
她小说的主人公总是那些最褴褛最负面的人物,就像一个巫婆总不愿意与好人为伍;她把蛇、蜘蛛、鬼当作最美丽的意象,只有巫婆才会喜欢这样的动物;她使用的语言与传统的古典文学完全不同,前者是以最少的文字表现最深广的思想,她的语言则词汇极少,却任意地重复冗长,就像一个巫婆的咒语。
她完全用一种潜意识写作,不考虑任何的结构技巧,竟然写了20年,这不是一种巫术是什么?她的小说根本谈不上好看,读她的小说好像接受自虐,令人痛苦恶心,完全像一个巫婆给我们的东西;她对世俗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就像一个巫婆一样,总想要攫取人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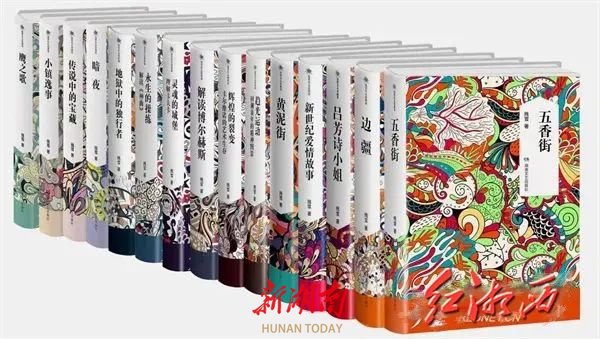
她说她的读者应该是未来的年轻一代,因为她的小说完全是一种想象,而且寓言的成分比较重,确实我们的新锐一代不知怎么特别喜欢巫婆的东西,竟把她的小说当成童话来读;她说,凡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创作,而且她说要跟这公认的世界反叛到底,只有巫婆才有这样的意志跟现实世界做斗争。
就是这样一个巫婆,中国文坛的“怪蛋”,异数、先锋;开过裁缝铺,当过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残雪,被认为是文坛奇才,东方的卡夫卡,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先锋派作家之一。
对残雪,就像对一个修炼了几千年的老巫婆一样,我们对她充满了恐惧和了解的渴望。残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2003年9月初,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上市时,记者采访了她。
》》我的小说是精神对肉体的复仇
记者:为什么会取残雪这个笔名呢?太阳底下残留的一点雪都是脏兮兮的。
答:这体现的是我的一种追求,当所有的雪都融化了,拒绝融化的残雪是我。可以是高山顶上无比纯净的,也可以是被践踏得脏兮兮的。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出一本访谈录?而且要取《为了报仇写小说》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书名呢?
答:我一直在想尽办法同读者交流。这本访谈录是一个极好的通道。
所谓报仇有两个层次。刚开始写小说时,冲动是来自对不公,对压迫的义愤,来自于某种同情心,这一点上我同大多数作家是一样的。但真正的纯文学作家不会停留在这个层次,一定要向内深入。于是在小说中,外在的矛盾被内在化了,报仇转化成精神对肉体的复仇。所谓肉体,就是人的世俗生活。人必须将这个肉体改造得适合于精神居住,这种改造只有通过复仇来达到。但丁的地狱,鲁迅的地狱,莎士比亚的监狱,描写的都是这种自我折磨。人必须知羞耻,灵魂才有救。
记者:你认为在中国能读懂你的小说的是哪些人?是不是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能理解你的小说中要表达的东西?
答:凡是喜欢文学的都有可能读懂我的小说。近年来,我的书大都可以印1万册了,说明读者在大大增加。西方人以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人酷爱幻想,所以更容易进入我的小说。但这些年,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大批喜欢幻想的青年人,他们是我的铁杆读者。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幻想力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经典文学,而当代西方文学的幻想力也在大大减弱。
》》我的作品通篇充满了阳光的照射
记者:你的小说揭示的总是阴险、狡诈、淫邪等一些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不给读者一些阳光的东西呢?
答:我敢说在我的作品里,通篇充满了阳光的照射,这是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来了的。正因为心中的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只有庸人和浅薄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记者:残雪,你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读者的感受?
答:我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读者考虑进去,我自得其乐,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
记者:听说你总是闭门不出,你是靠一种天赋一种想象力在创作吗?
答: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指的是精神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人走的地方再多也是白走。我的想象力都是从我的精神活动中喷发出来的,我实在想不出一个纯文学作家除了这个源泉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方式。
记者:有的作家一生就一本书,而你写了很多了,你最满意自己哪一部小说?你认为自己的创作状态进入了成熟期吗?
答:我最满意的小说有好多部。我就要出短篇总汇了,有80万字,希望读者去买了看。我已经50岁了,要是像某些人一样,还没有达到成熟期,我早就不写了。
》》我希望中国出现东方的但丁
记者:你一直说自己是搞纯文学的,而且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你认为在中国你的同道者多吗?纯文学有生命力吗?
答:我在中国有一些同道者。梁小斌的散文,薛忆沩的短篇小说,我认为是第一流的纯文学作品,而且我自己都写过评论。文坛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我感到非常气愤。纯文学有几千年历史了,今天仍在发展,这不就是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证明吗?
记者:有人说你是东方的卡夫卡,你认同吗?
答:如果有人说我是东方的卡夫卡,我会感到非常荣幸。文学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我还希望中国出现东方的但丁,东方的歌德。那种自己无才,却天天嫉妒别人的人是最要不得的,反映了千年的民族劣根性。
》》我在长沙活不下去
记者:看你的小说,很多人认为,你一定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是这样吗?
答:我有兄弟姐妹五个,虽然小时候,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打成右派,但一家人相亲相爱。
记者:你现在的家庭怎样?还做衣服吗?
答:现在很好,衣服早就不做了。1988年我成为湖南作协的专业作家,现在还是,生活基本有保障。丈夫是个性格悲观的人,但很深刻。
记者:你在长沙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突然想到把家搬到北京去呢?
答:我是2001年底搬到北京的。因为在长沙实在活不下去了。长沙的气候太潮湿了,10多年来我饱受风湿折磨之苦,后来借了点钱在北京买了一套110多平方米的房子。北京的干燥令我感觉很舒服。
记者:听说你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作,也有一点娱乐活动吗?
答:电视从来不看。每天上网浏览一两个小时新闻。每天学英语,坚持十年了,好阅读英语作品。我唯一的娱乐就是跑步,一天不跑步,就一天不能创作。
记者:听说你有一个很棒的儿子?你给过他怎样的家庭教育?他读你的作品吗?
答:儿子专业是化学。已经在美国读了两年博士,还要读4年,包括1年博士后。儿子的头脑不适合文学,但最近也读一点我写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