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亚洲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力量”文学分享活动在北京举办。本场活动是“第九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重点活动之一,韩国作家孔枝泳,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中国作家乔叶、辽京一同做客北京单向空间·郎园STATION店,围绕文学展开了对话。据悉,10月至11月,黎紫书还将从北京出发,先后入驻丽江、李庄“十月作家居住地”,经昆明、重庆、青岛、泉州、呼和浩特等地重返北京,与多位嘉宾进行深度对谈。

十月文学月期间,“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亚洲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力量”文学分享活动在北京举行。(主办方供图)
“每位写作者在童年时期必然是深度阅读者”
活动现场,乔叶从自己在河南小村庄担任乡村教师的经历出发,忆及她从读报纸到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散文的“野生”写作起点。“孤独和对现状的不甘让我通过写作来寻找生活的出口。那时我20岁左右,写的都是很个人化的情绪,却意外收到了读者来信,得到了遥远的陌生人的回响,这让我觉得神奇又温暖。”在多年阅读经验的累积和读者反馈的激励下,乔叶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其文学观及创作也随之探触到新的维度。
对此,黎紫书表示赞同,她认为,每位写作者在童年时期必然是深度阅读者。“小时候只要有文字的东西我都能看完,更精彩的世界总是在文字里头。”她回忆道。在中学时代未曾发表作品时,黎紫书的华文老师就成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位读者”。进入社会工作后,黎紫书首次参加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的评选便获得大奖,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始终心怀感激,“如果没有那段在学校写作文的快乐岁月,我可能没有勇气去尝试追逐文学梦想”。

《流俗地》,[马来]黎紫书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孔枝泳在分享创作源起时,也提到了自幼对文字的浓厚兴趣。她回忆了小学时参加全国小学生作文比赛、大学时参加学校诗歌征集并在诗坛崭露头角的往事。“我的文学之路开始得很顺畅,但是后来我的人生充满曲折。在那时候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今后的人生要怎么度过。我认识到,我更适合写作。”后来,孔枝泳创作了小说《拂晓》,正式开启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
辽京表示,“每个人文学创作的缘起都不尽相同,也许是因为某个关键的事件,也许是因为某个重要的人,但过程都是相似的,大家都是一边满怀信心、一边带点怀疑地走上这条文学创作之路的。”对于辽京来说,写作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持续进行文学创作,就是在“对抗对写作的懒惰或者恐惧”;选择文学不仅仅是选择一个谋生的职业,也是选择一种生活、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活着的方式。
“一定要离开、要逝去,才能在文学上真正拥有”
在媒介发达的时代,人们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他人的故事,创作文学和阅读的意义便值得考量。
尽管孔枝泳的作品涉及许多现实的社会事件,但她的目的并非仅仅描述事件本身,而是通过事件面前人们的态度和回应,让读者去感受和思考。谈及写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她说:“在《熔炉》中,女主人公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原本的我们。’因此,在变化急剧的时代,有些东西一定要保留,无论它是生命的尊严还是思想,我是为了守护这样不变的价值而在不停奋战。”孔枝泳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作品像星光一样发出信号,传递给世界上许多等待这样的信号的人们,她也因为《熔炉》《远海》等作品得到的反馈而感到幸运。
乔叶同样从作品出发,阐释了自己对写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理解。她坦言:“二十年前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强情节。后来慢慢地我的文学观和创作面向发生变化,我觉得写作更重要的是回望,精微又广大的写作才能触及更广泛的共鸣。”与《流俗地》《远海》《白露春分》精心呈现的日常生活相似,宝水村也是基于大量素材精心构建而成的“裸妆”式文学村庄。“这不是简单的村庄、亲人的概念,而是意味着血缘和地缘、个体和世界,一种复杂的对照关系。我希望《宝水》能够承载这种复杂性。”

《宝水》,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在家庭故事《白露春分》里,辽京里讲述了很多童年故事,如同乔叶所说,“故乡是离开后才能拥有的地方”,辽京认为人也是在告别童年后才能在文学层面上真正拥有童年:“成年人要回望自己的童年,才会想到应该怎么去表现它,在文学层面上呈现童年的另外一种色彩。一定要离开、要逝去,才能在文学上真正拥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白露春分》,辽京著,新经典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版。
由黎紫书创作的《流俗地》,以马来西亚锡都,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讲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务俗事,迂回曲折的情节,仿佛召唤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小事。“吾若不写,无人能写”,黎紫书谈到,书写怡保的故事与写作能力或名望无关,而是马来西亚能写怡保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即使怡保以后还会出现一个作家,那个人经历的家乡跟我看到的也不一样,如果我今天不写下来,我看到的故事就永远不会有其他人写了”。
黎紫书曾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她认为,小说家应该去发现新闻到不了的地方和角度:“借助我的眼睛,让我的读者在我家乡的这群平凡人和他们再普通不过的生活里看到亮光,也让读者看到他们自己生活的亮光,这是写小说给我最大的满足感。”
“每个写小说的人都在传递自身对社会的看法”
“文学是否还需承担教化、救世的功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辽京认为,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情感可能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作品中。
乔叶分享了她对个人化写作引发读者共鸣的看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写作时,遥远的读者会自动和我链接起来。我的所思所感、喜悦和忧愁、困惑和痛苦,可能都跟他们有同频共振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像地面上一口口独立的小井,但地下河是相通的。”她希望当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小井”打到足够的深度时,能引发人们更广泛的回响。
孔枝泳创作了《熔炉》《我们的幸福时光》《远海》《亲爱的女儿》等很多在韩国引发广泛公众议论的作品,对于这样的文学创作,她直言:“这些作品包含着我个人的判断和省思。我会思考我对社会的善与恶能否有绝对的判断,但如果问我是否后悔创作这些作品,或者是否觉得错了?我并不这么认为。”孔枝泳认为,所谓进步是让生命成长、让生命生发,为边缘的弱者带来饱腹的食物或文化,她想用创作来实现这种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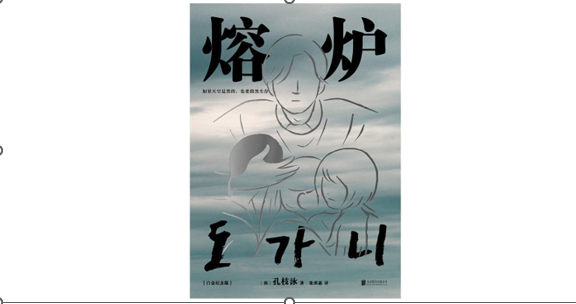
《熔炉》(十五周年纪念版),孔枝泳著,张琪惠译,磨铁·铁葫芦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4月版。
在作为记者长期接触社会底层的过程中,黎紫书深知弱势群体可能面临的命运,这也促使她在《流俗地》中写出盲女银霞的遭遇。至于如何理解,则交由读者自己去解读。“就像契诃夫,他从不讲‘爱’与‘悲悯’,可是他小说里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画面都充满对人世的同情与爱。每个写小说的人都在传递自身对社会的看法,不管写得多么隐晦或平淡。”
整合/何也
编辑/申璐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