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业衰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国际商战叙事,十分契合传统上以西方为中心视角的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以来既成为中国茶业改良的重要依据,也催生了一大批茶业史研究成果。美国学者刘仁威(AndrewB.Liu)的《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TeaWar:AHistoryofCapitalisminChinaandIndia)对这一成熟的史学题材进行了再研究,并试图创造一种关于近代国际商战的新叙事,从理论角度看颇具新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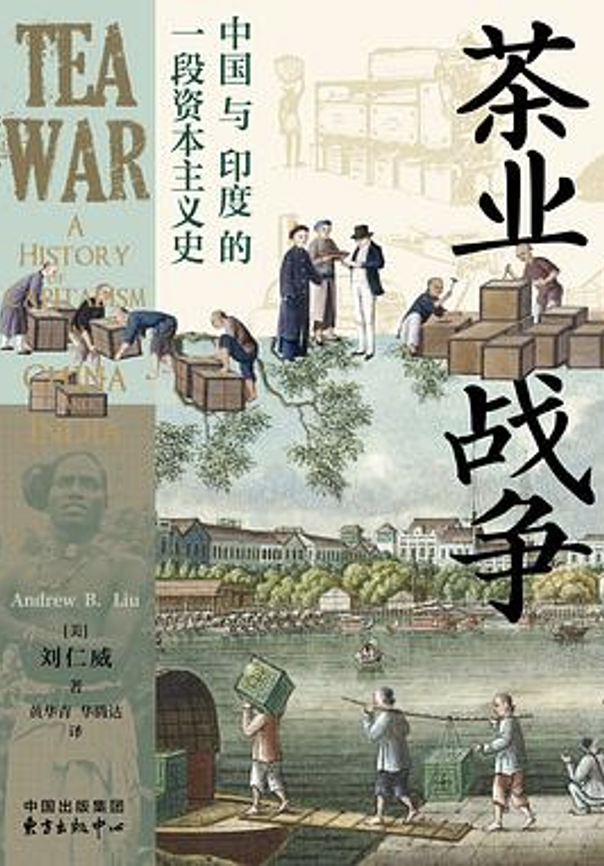
《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美]刘仁威著,黄华青/华腾达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1月。
撰文|严鹏
新资本主义史的新作
阅读一本学术著作,需理解其在学术史与思想史脉络中的位置。《茶业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以下简称《茶业战争》)书名包含的“一段资本主义史”,已经点明了该书可归入近年来欧美学界兴起的“新资本主义史”谱系中。
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西方形成于19世纪后期,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将目光投向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毕竟,传统历史学以帝王将相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为主要书写对象,马克思主义对物质的重视,提升了经济活动在历史研究对象中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核心概念“资本主义”,一度成为经济史这门学科的重要议题。一些学者尽管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理论等工具进行历史分析。不过,到了冷战时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用计量方法等新的工具创造了经济史研究的新范式,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和政治经济学的联系,而被一些学者规避使用。这里要强调的是,二战后的西方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史时,一部分学者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但还有一部分学者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与唱赞歌,并将资本主义简化为自由市场机制。冷战结束后,后一种倾向自然更为明显,相关著作如《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国富国穷》等均在原著出版后不久即译为中文引入国内,成为流行读物。因此,西方学界早期的资本主义史研究,明显分为批判性研究与肯定性研究两大类,而肯定性研究受简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本身即为资本主义文化机器的一部分。但如前所述,在一段时间里,西方经济史学界更倾向进行具体的实证性的研究,而不是讨论资本主义这一宏大叙事。
2008年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明显的复兴,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现实动荡有直接关系。由冷战胜利带来的西方“历史终结论”被全球金融危机所彻底终结,西方人开始再度聚焦孕育危机的体制问题。2008年,美国的企业史学会竟曾考虑改名为“资本主义史学会”,同年,哈佛大学创建了一个研究资本主义的项目。2014年,由主流经济学家主编的《剑桥资本主义史》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Beckert)出版了《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开“新资本主义史”研究之滥觞。其实,贝克特的原书名为EmpireofCotton:AGlobalHistory,并无资本主义字眼,但该书通篇讨论的正是资本主义,而且提出了“战争资本主义”的概念,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叙事,中译本在副标题加上资本主义四个字,倒也符合作者本意。其实,所谓“战争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只是对西方重商主义体系中由国家为经济保驾护航的历史的再提炼,甚至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一种新表述。贝克特在2012年世界经济史大会上的一个小组讨论中担任评议人,他也说过:“我们需要某种旧时的政治经济学。”这表明,新资本主义史的“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起来并不那么“新”,新在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构建的新自由主义历史,是金融危机时代历史叙事对冷战胜利时代历史叙事的批判与调整。简单地说,西方学界的某种“旧”资本主义史研究强调的是自由市场带来西方繁荣发展的单线历史进化论,而新资本主义史则揭示了这一过程离不开战争等暴力因素的协助,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制度能够从奴隶制等前现代制度中汲取养分。这种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语境变迁下的学术流变,是阅读相关作品时无法绕开的背景。
从学术史角度看,2020年出版的《茶业战争》属于新资本主义史的一部新作。用作者的话说,该书展现了近代“中国和印度腹地的茶叶生产者、茶商和种植园主是如何借由层叠的资本积累循环以及他们与其他工业世界共同面临走向集约化生产的压力而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导论部分,刘仁威提到了他的书要“与新的‘资本主义史’文献发生对话”,并提到此前新资本主义史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北大西洋两岸”,而他的目标是“理解资本积累在欧洲帝国边缘——也就是通常被视为无法发生现代增长的殖民时期亚洲社会——的意义”。因此,尽管刘仁威对贝克特等人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他的《茶业战争》仍然是一部新资本主义史著作,为不断增长的新资本主义史研究文献贡献了一个来自东亚与南亚的比较性视角。刘仁威在《茶业战争》的《中文版自序》中坦言:“我的个人发展恰逢美国高校研究更广泛地转向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我都深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在美国的学术界,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关于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史’的讨论……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丰富这些讨论。”这一背景性说明,是理解《茶业战争》并评估其价值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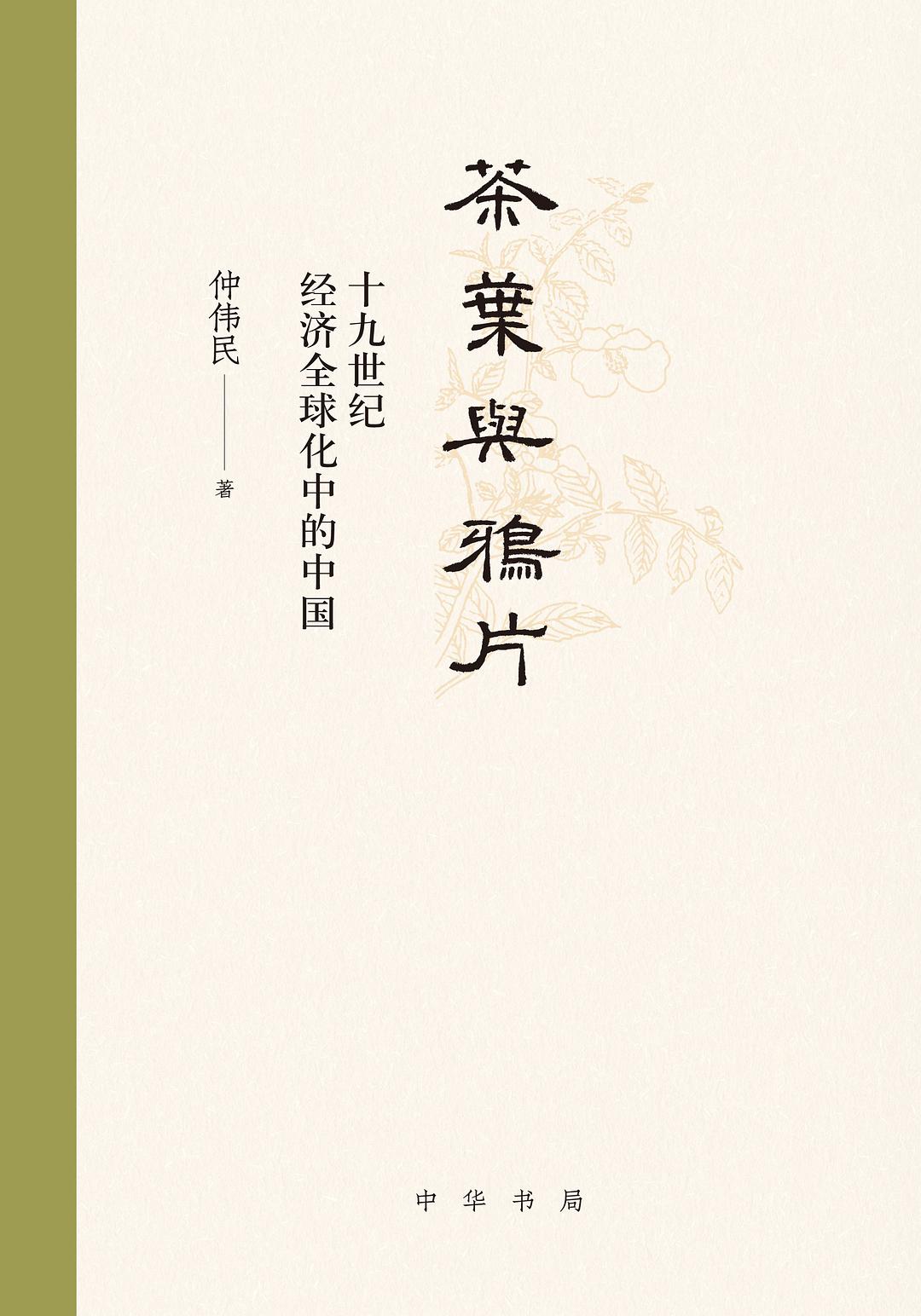
《茶叶与鸦片》,作者:仲伟民,中华书局2021年11月。
非线性的现代化故事
《茶业战争》除导言与结论外,共分7章,第一章概述了全球茶叶贸易简史,引出中国与英属印度这两个19世纪国际商战的对手,第二章到第五章描绘了1834—1896年中国与印度的茶业发展,第六章与第七章则分别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与中国茶业讨论两者的资本主义问题。在写作上,刘仁威既不断对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又注意考察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之间的张力,揭示资本主义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自然是为了消解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性,从而展现一个不同于标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更为复杂的资本主义。此举不啻于讲述了一个非线性的现代化故事,无论是否接受这个故事,它都是《茶业战争》的精华所在。
《茶业战争》以中国茶业改良的先驱吴觉农为引子展开书写,在全书的不同部分,也涉及吴觉农的思想与实践。实际上,吴觉农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都是被一种工业化的近代国际商战叙事所支配的。1943年2月,吴觉农在福建崇安茶叶研究所纪念周上演讲时,提出:“中国生产的茶叶,本来是属于半农产品半工业制的出品,将来农业生产事业发展,茶的制造必然更接近于工业化,这是无疑的。”这里的工业化,其实主要指的是机械化。吴觉农的呼吁是基于一种晚清就已流行的历史叙事,即中国茶业因机械化、标准化落后于英属印度而丧失了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另一位中国茶业的改良先驱张天福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欲求茶叶品质提高齐一,减低制造成本,舍制茶机械化莫办。”中国茶业被印度茶业赶超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对这一事实进行归因与解释,就构成了一种历史叙事。吴觉农、张天福所秉持的历史叙事其实最初源于英国人的宣传。19世纪后期,英国人宣称通过更科学的种植方法和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让其殖民地印度的茶业生产后来居上,产品品质超过了中国茶叶。更为一般化地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茶业在国际商战中战胜了中国茶业,可以视为一个浓缩版的现代化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现代化以科学和工业为支撑,终将战胜传统文明,西方世界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并成为一个样板,地球上的其他地区若不踏上这条历史的单行道,就只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竞争中被淘汰。这个故事,基本上也是从19世纪直到21世纪大部分研究近代茶业史的论著的内核。
美国学者埃丽卡·拉帕波特(ErikaRappaport)出版于2017年的《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AThirstforEmpire:HowTeaShapedtheModernWorld)对前述现代化的近代国际商战叙事进行了挑战,认为市场营销及其对消费偏好的塑造,远比机械化对于印度茶业的崛起更为重要。刘仁威在《茶业战争》中引用了《茶叶与帝国》的研究成果,并同样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与拉帕波特一样,刘仁威认为机械化不是决定中印两国茶业商战成败的关键因素。《茶业战争》指出,茶叶生产的天性意味着它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1878年,印度茶产区协会承认“对手工劳动的需求始终难以显著降低,它也始终是生产成本的决定性要素”;直到1883年,印度的英国种植园主还抱怨机械化可能会损坏植栽,难以在种植环节引入,相同的评论在十年后再度出现于英国种植园主笔下。然而,从时间上看,到1878年时,印度与锡兰茶叶在英国市场上已经超越中国了。因此,《茶业战争》认为,即使劳动节约型机械长期来看是有效的,但其引入过晚,也无法快速解决实际问题,难以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茶业的崛起。数据显示,印度茶园的平均亩产到19世纪末只有300—400磅,约等于同期中国武夷山的茶叶产量,直到20世纪前十年,印度茶园亩产量才跃升至500—700磅的范围。该书写道:“即便我们承认对于资本集约型机械的普遍采用的确最终使得1910年之后的生产力有了跃升,但印度茶叶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将中国的竞争者甩在了身后。”换言之,目前的量化研究尚不支持机械化赋予印度茶业以超越中国的竞争优势。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论证至为重要,因为它动摇了那种流传了百年的近代国际商战叙事的根基,并解构了线性的单行道式现代化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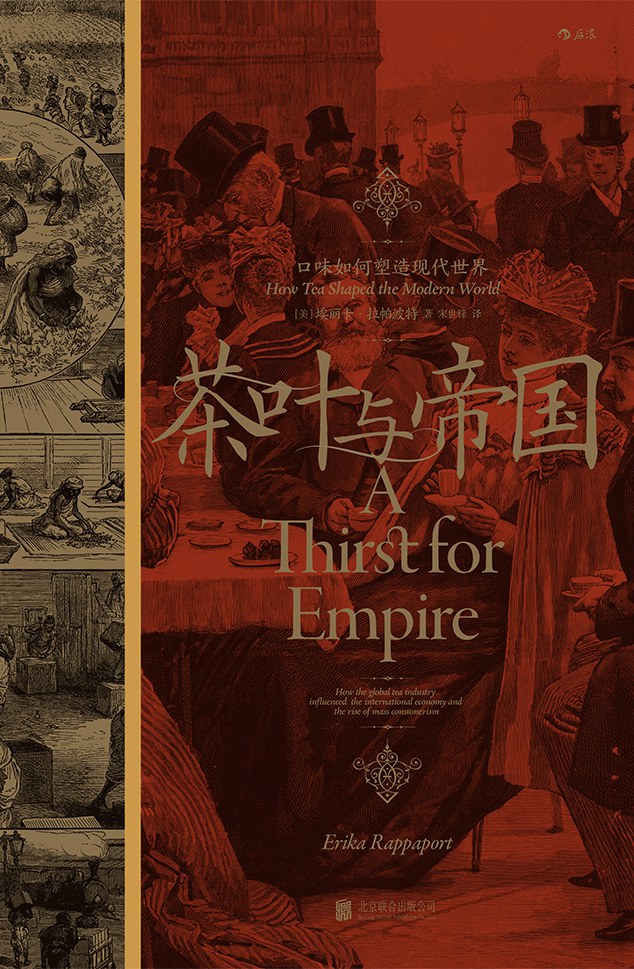
《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作者:[美]埃丽卡·拉帕波特,译者:宋世锋,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月。
然而,印度茶业的成功即使不源于机械化,也必须得到解释。对此,《茶业战争》的论点是:“印度茶叶之所以赶超了竞争对手中国,并非源于技术创新,而在于其劳动集约化的独特体制。”这一劳动集约化的体制涉及英国种植园主在契约劳动法案的支持下,能够简单通过给雇员降薪来削减成本。刘仁威指出:“从1865年开始,印度殖民地官员为阿萨姆茶产业定制了一套井然有序的劳动力招募和刑事契约劳动体系。其特征是对工人流动的限制、不间断的监管,工资由法律锚定而不受市场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种植园主制定了针对日常工作的劳动管理时间表,确保工人能不间断地工作,该时间表还与薪资体系挂钩,使劳动者获得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其任务的完成度。此外,英国种植园主还通过种族与性别的社会分类来组织劳动,即挑选一些更易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族群进行生产,并持续提高女工比例。当然,刘仁威没有否认机械化的作用:“英国种植园主的贡献是进一步拆解了茶叶的制作流程……任务的分工进一步促使种植园主用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取代人工简单的操作。”在刘仁威讲述的新故事里,机械化依旧是重要的,但对于印度茶业在国际商战中早早击败中国来说,机械化不是决定性的。进一步说,资本主义史不只是技术创新的进步史。对资本主义而言,使用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设备与对劳动力进行最大限度的生理性的压榨,是可以并存的。这种一般化的结论,正是新资本主义史想要揭示给当代读者的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相。
对中国读者而言,《茶业战争》对印度茶业历史的描写与分析,或许更有价值,因为这恰是中文文献相对缺乏的内容。不过,该书对19世纪徽州与武夷山茶区的劳动集约型资本积累的论述亦别出心裁。以焚香计时为例,刘仁威认为:“为了合理安排茶叶的揉捻、烘焙、筛分等工序,19世纪的中国茶商精准测算出了每道工序所需的时间,设计工作指令以尽可能压缩浪费时间的活动,并使用计件薪资体系,以激励劳工尽其体能极限最大限度地劳动。”这种管理制度并不与生产的机械化或工业化相配套,但它是高度理性化的,而理性恰恰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于是,这就又回到了对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的问题的思辨。刘仁威称,当他接触到中国学者彭南生的“半工业化”理论后,欣慰地发现“我们分别从各自的进路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即“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之近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任何特定的技术特色,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为世界市场种植和生产的社会冲动开始主导了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如仲伟民在《茶业战争》中译本序中所言,该书受到“加州学派”的影响,要讲述一个不同于19世纪线性进化观的非线性现代化故事:“资本主义不应被构想为一条通往英格兰模式的固化路径,而应作为一股抽象的动力——只不过在马克思时代,维多利亚治下的英格兰碰巧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诠释。这一分析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资本集约型产业及其令人激动的技术进步,而是一股走向永无止境的单纯利润积累的根本动力,以及它在历史上曾呈现出的各种形式。”从新资本主义史的视角看,《茶业战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多面性,在学术上是成功的。
不过,《茶业战争》显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思考与研究的问题。首先,该书以数据分析机械化并非19世纪印度茶业击败中国茶业的首要原因,令人信服,但该书建立的测度框架相对简单,仍有进一步量化分析的空间。其次,该书否定了主流的近代国际商战叙事,但着眼点主要在于19世纪后期,然而,那场商战实际上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对进入20世纪之后的历史,也就是吴觉农等人关心的中国茶业的工业化问题,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性。最后,该书收尾时也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茶叶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份额从一半下降到三分之一,而印度消费者中有饮茶习惯的人数却有了很大提升。这提示当代读者,近代国际商战的叙事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为中心书写的,但对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自身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基本上是漠视的。那么,当中国茶叶在全球市场占比份额再次超过印度后,是否能用民族主义的商战叙事去解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又是否仅限于以产品占领发达国家市场为指标?这是对茶业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撰文/严鹏
编辑/申璐李永博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