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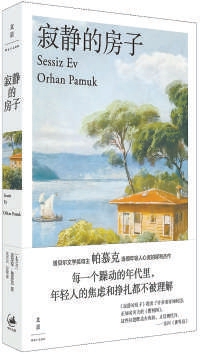
《寂静的房子》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彭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我的书中,年轻人最喜欢《寂静的房子》,里面的每个年轻人都是我。”这本出版于1983年的书,是奥尔罕·帕慕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既有作家本人的家庭写照,如自己外祖父母的不幸婚姻、价值冲突;又聚焦年轻人该如何审视历史,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应负何种责任。小说以祖父塞拉赫丁与祖母法蒂玛的老房子为中心,透视土耳其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孙子法鲁克、梅廷和孙女倪尔君回老屋探望祖母,在“天堂堡垒”短暂驻留,各自讲述记忆与闻见,如同《十日谈》提供了叙事契机与组织形式。
驾驭叙述视角的极大自由
塞拉赫丁因为政见被逐,离开伊斯坦布尔来到郊区行医。“让我们离那些非自然的愚蠢皇帝以及阿谀奉承的帕夏们远点吧。”然而,妻子法蒂玛时刻都在打听伊斯坦布尔时局,期待重返。作家隐喻了“新的东方”(想象的新世界)。对于孙辈,“不会教给他那种东方式的忧郁、哭泣、悲观、挫折以及可怕的东方式屈服,我们要一起忙他的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由的人。”
祖父把祖母当作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看待,而“其他人都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女仆和奴隶”。法蒂玛却将丈夫的私生子雷吉普妖魔化。事实上,帕慕克已将这个牢骚满腹的蠢笨祖母化为巫婆符号。在这个患上被迫害妄想症的女人身上,只剩下历史残存的顽固与怨恨。寂静房子里的老夫人,如同“阁楼上疯女人”的某种变体。
仆人雷吉普是一个侏儒,虽然厌恶法蒂玛,却听命于她,这种人身依附正是伦理惰性的表现。侏儒和巫婆,构成吊诡的组合,暗示某种朽坏、滑稽与怪诞。他们与老房子一样,处处散发出历史气味,属于过往世界的遗迹。故事里,家族第二代(曾做过县长的儿子)早亡且缺席,雷吉普客观上充当了父辈,成为祖辈与孙辈的联结。当家庭依赖这个身份污名化、身体畸形化的人物沟通,恰恰说明家族内部的脆弱、崩解与失语。
《寂静的房子》显示了帕慕克驾驭叙述视角、调度人物声音的极大自由。几乎每章都在切换叙事者,甚至你要分辨很久才能确认谁在场,谁讲述。令人眩晕的人称转换,使长篇小说的连续性产生阻断感。叙事单元的相对独立,如同建筑构件可重组。整部小说可以拆解出祖父祖母婚后生活、私生子伺候老夫人日常、孙辈探望祖母的还乡故事、哈桑与梅廷的青春叙事、法鲁克搜寻档案等情节段落。
如果“滥用”多声部与复调性描述此作,会发现并不恰当。因为帕慕克并不追求人物的对话性与合声意义。相反,他在暴露人物各说各话,互不理解,充满揶揄,侧目而视。正如梅廷对姐姐和哥哥(知识分子代表)的鄙夷,“他们当中一个是厌恶钱的空想主义者,另一个则萎靡不振得都懒得伸手去挣钱了”。我将小说描述为:一种并联的独白体矩阵。福克纳使诸多人物重述一个故事,那么帕慕克则使不同人物登场,而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外部时间性对小说愈发不重要,因为“线头”太多,作家随时都在另起炉灶地穿插。每个人物将是一个“点光源”,呈射线交织,叠合出小说整体光晕。
“寂静的房子”与“铁屋中的呐喊”
某种角度看,此作与20世纪的中国作家倒有冥合。“寂静的房子”与“铁屋中的呐喊”更像一种互通。小说潜藏的启蒙与革命,同样是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法蒂玛像九斤老太爱发牢骚,雷吉普如孔乙己被看客取笑,没人理解塞拉赫丁的“启蒙事业”,法鲁克只能埋头于历史研究。儿时玩伴成年后被不同阶层、教育背景阻隔。知识分子还乡后,对乡村的审视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典型场景。
帕慕克写知识分子,是将他们置于底层生态中,而非封闭于书斋高校里。故事里卖彩票的、挤牛奶的、开旅馆的,做各式生意的贩夫走卒,构成乡村市井、街角社会。环境很喧嚣,精神却沉默。祖父在行医中坚持启蒙,去除病人精神愚昧、文化禁锢,传播科学与无神论。他的桌子上摆放头骨、器皿与透镜,也说明科学实证主义,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深刻塑造。
医生与作家,行医和从文,产生了身份转译,同归于“救人”二字。“去吧,你去救救你们的村子吧……给他们读一个小时从我的百科全书中截取下来的小册子的话,那这个民族就得救了。”而塞拉赫丁至死也没完成那部能唤醒东方的百科全书。长孙法鲁克几乎复刻了祖父——爱饮酒和写作。他离婚、喝酒、发胖,把查找瘟疫历史当成生活寄托。“我要像他们那样,像爷爷一样,像父亲一样,抛弃一切待在这儿,每天也就去去盖布泽或是坐在桌前写写那些和历史有关的、上百万字的没头没尾的文章。”
小说和历史的隐秘对抗
我想帕慕克更意在探讨小说和历史的隐秘对抗。历史总在用“另外的”和“新的”故事,解释原有的故事。历史的技艺,是处理迷雾(档案文件、统计数据、证词书信),建立数以万计的事件关联。“我把它们比作没有重力的虚空里广袤无垠的一个蠕虫星系”,历史事件在大脑里闲逛,并没有接触联系:“必须找到概括了所有事件的一个短小故事,就必须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传说似的!”概括而言,小说是陷入故事,历史是添加故事。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面,一件一件的,没有什么故事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就给它们加上些故事。”《寂静的房子》正是添加家庭故事、联系起土耳其历史与生活的案例。历史书写已成为一种“家族遗传”。这种执念标记出影响的焦虑、人物内在的悖反。“要是我能把那些档案、小说、历史统统给忘掉,那该多好呀。”既想遗忘又想书写的冲动,漫长而焦灼。祖孙都陷入了历史的迷惘:选择保守化还是自由化,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是有神还是无神,世俗化还是教义化生活?小说里这些多元未解的疑难,构成作家对土耳其现实的历史性沉思。(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