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孙雯
今天(11月25日),一位文学老人正在被隆重缅怀。他是巴金。
诞辰120周年的巴金,从未老去。学者陈思和曾说,无论过去跟巴金接触,还是现在谈巴金,永远无法将他和衰老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笔下和人生,给人传递出那种“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理想和热情”。

巴金是四川人,但他的祖籍在浙江。“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我的高祖李介菴去四川),在嘉兴过去有一所李家祠堂,在四川老一辈的人同嘉兴的家族有过一些联系。”巴金在《随想录·西湖》中这样写道。
至于杭州,他说:西湖永在我心中。
自1930年初次来杭,至1998年最后一次到访,巴金的足迹遍布以西湖为中心的杭州几乎所有景点,并留下了众多描写和谈论西湖的散文随笔。1982年4月,在他的晚年重要著作《随想录》中,他写下了《西湖》,并说:我很想写一部西湖变化史,可惜我没有精力做这工作。但记下点滴的回忆还是可以的。
《随想录》创作于1978年12月至1986年6月,先刊登于香港的《大公报》,后集结出版。
1978年12月1日,巴金在《随想录》的序言中写道——
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变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这时,巴金已经74岁,他是怀着告别的心情开启了《随想录》的写作。《随想录》收有150篇文章,有反思历史、批判传统思想的杂文,有怀念亲友、作出自我忏悔的抒情散文,也有针对现实、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随想。
其时,巴金重拾独立思考,使《随想录》拥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并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微妙的影响,他谈及的话题,今天仍然不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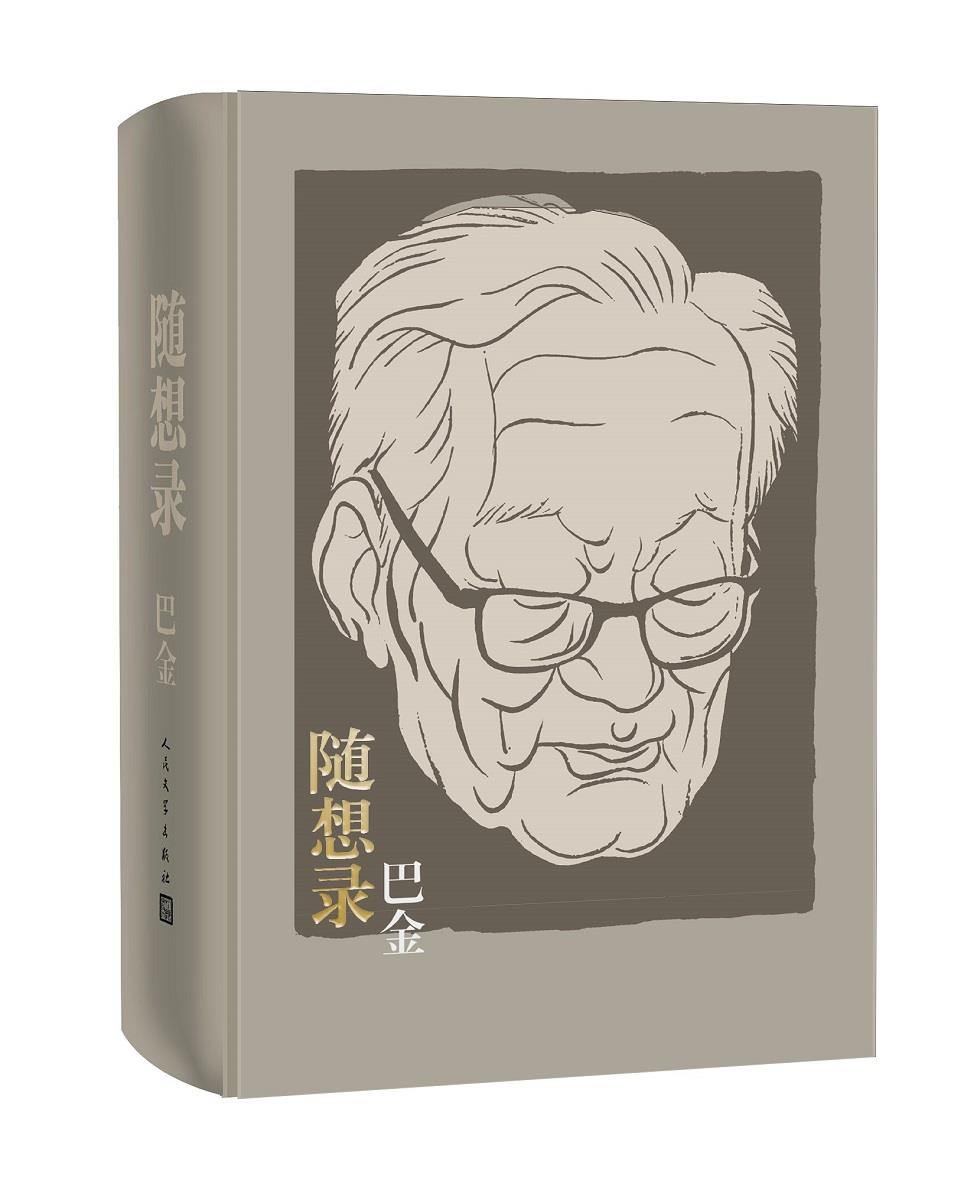
《随想录》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爱憎从“我的生活里来”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
——摘选自随想录第一集·文学的作用
真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摘选自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再论说真话
人人期待改革,可始终不见改革
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摘选自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小端端
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的力量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摘选自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我的“仓库”
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
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问,理想究竟是什么?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这几十年来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那么传播黄金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哪方?今天到处在揭发有人贩卖霉烂的食品,推销冒牌的假货,办无聊小报,印盗版书,做各种空头生意,为了带头致富,不惜损公肥私、祸国害人。这些人,他们也谈理想,也讲豪言壮语,他们说一套,做另外一套。对他们,理想不过是招牌、是装饰、是工具。他们口里越是讲得天花乱坠,做的事情越是见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子就变为“向钱看”,定风珠也会变成风信鸡。在所谓“不正之风”刮得最厉害、是非难分、真假难辨的时候,我也曾几次疑惑地问自己:理想究竟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已经被狂风巨浪吹打得无踪无影?我仿佛看见支流压倒了主流,它气势汹汹地滚滚向前。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理由灰心绝望,因为理想明明还在我前面闪光。
我在二十年代写作生活的初期就说过:“把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在人类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把它们分给别人,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你们问我伏案写作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追求什么?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话。我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
——摘选自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寻找理想”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