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1岁的科幻女王厄休拉·勒古恩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影响,开始创作个人博客。她从81岁至85岁的部分博客文章被收录在这本名为《无暇他顾》的小书中。她在文章中畅谈个人生活、文学创作、社会议题、女性主义,也记录自己与爱猫相处的日常。博客显露出勒古恩在文学创作之外私人化的一面,大胆、风趣、极具锋芒。阴性的乌托邦是勒古恩科幻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在随笔中她阐释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关于儿童与创造力,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们的确终生都能从孩子们身上学到很多,但‘如孩子一般’只是精神建议,并非智力、实践或伦理上的建议。”
本文摘编自《无暇他顾》,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节,注释见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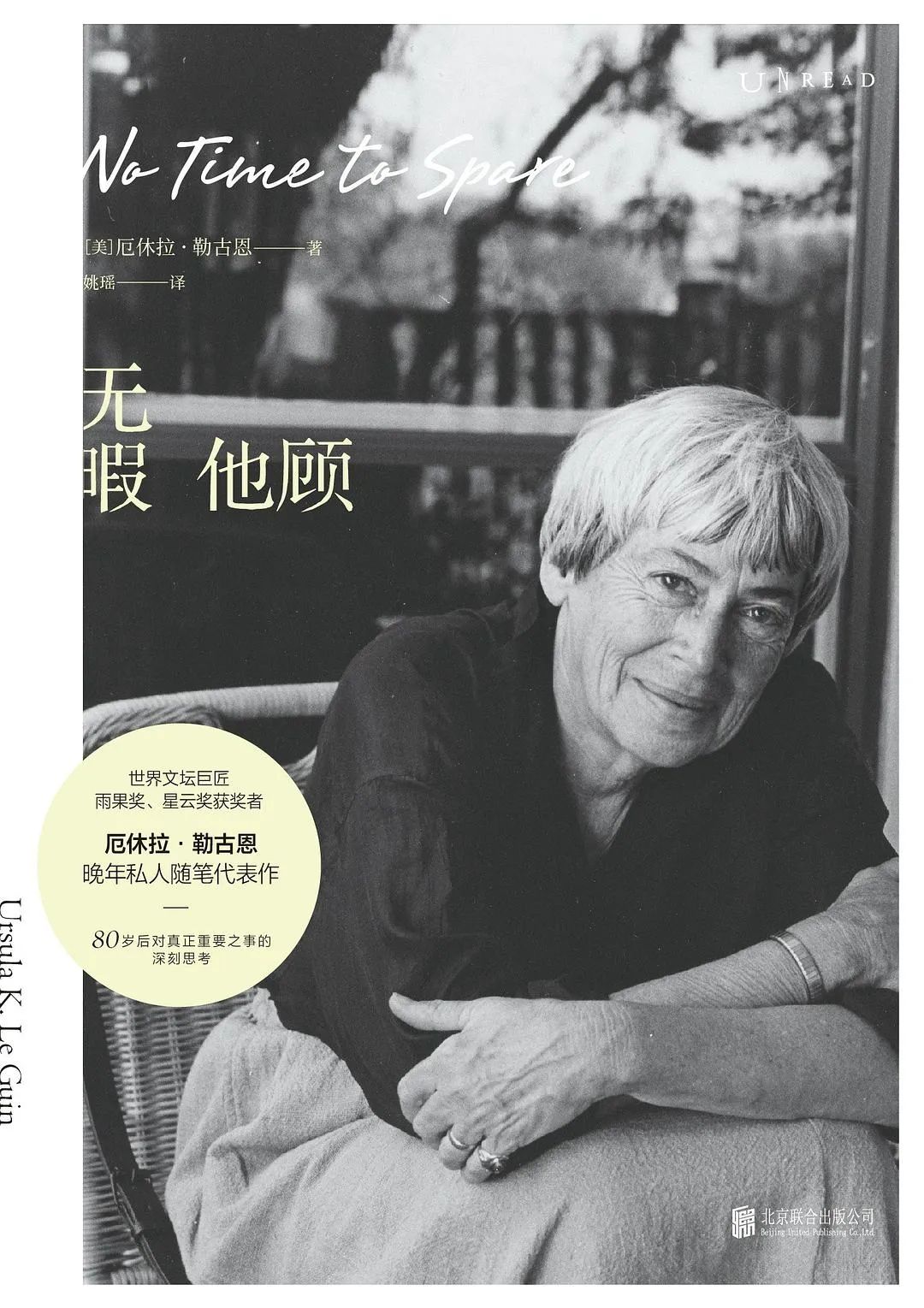
《无暇他顾》,[美]厄休拉·勒古恩著,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11月。
乌托邦阴,乌托邦阳
以下文字是关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一些思考。
古老而粗糙的好地方都是补偿性的幻想,是能够控制你不能控制的东西,拥有此时此地你无法拥有的东西——一个和平有序的天堂;一个时光的乐园;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通往这些地方的道路很清晰,但很极端。你得去死。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世俗的,由知识分子构建,仍旧是在表达对此时此地缺少之物的渴望——是理智之人对人生的控制——但他的“好地方”明确无误是“不存在之地”。只存在于头脑中,没有建筑工地的蓝图。
自此以后,乌托邦一直位于此世而非来世,但要跳出地图之外,越过大洋,翻过山脉,在未来,在另一颗星球上,一个宜居却无法抵达的别处。
自打有了乌托邦以来,每一个乌托邦,无论清晰或晦涩、确然或可能,在作者或读者的判断中,都既是个好地方,又是个坏地方。每一个完美乌托邦都包含一个反乌托邦,每一个反乌托邦都包含一个完美乌托邦。

纪录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在阴阳符号中,每一半都包含了另一半的一部分,表明两者完全相互依赖并不断相互转化。图形是静态的,但每一半都蕴含着转化的种子。这个符号代表的不是停滞,而是过程。
把乌托邦想象成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国符号或许有所帮助,特别是你如果愿意放弃通常的男性主义假设——阳优于阴,转而考虑两者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转化才是这一符号的基本特征。
阳是男性的,明亮的,干燥的,坚硬的,活跃的,犀利的。阴是女性的,阴暗的,湿润的,简单的,接纳的,克制的。阳是控制,阴是接受。它们是伟大而同等的力量,没有哪一方可以单独存在,每一方都始终处在向另一方转变的过程中。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往往都是一块被荒野环绕的飞地,受到最大限度的把控,一如巴特勒的《乌有之乡》(Erewhon),E.M.福斯特的《大机器停止》以及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_《我们》中所写。乌托邦的优秀公民认为荒野危机四伏、充满敌意,无法居住;而对爱冒险或叛逆的反乌托邦而言,荒野则代表着改变和自由。我在这里看到了阴阳相互转化的范例:黑暗神秘的荒野包围明亮安全的处所,“坏地方”随后又成为“好地方”,明朗开放的未来包围黑暗封闭的监狱……反之亦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模式恐怕已经被重复到了极致,主题的变奏越来越模式化,或者干脆随心所欲。
打破这种模式的醒目例外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是真正的反乌托邦,在这个故事里,荒野被缩成一块飞地,被高度集权的阳世界完全掌控,以致它所提供的任何自由或变革的希望都是梦幻泡影。还有奥威尔的《1984》,一部纯粹的反乌托邦作品,故事中阴元素被阳元素彻底抹除,只出现在受控制人群的逆来顺受之中,成为对荒野与自由被操纵的妄想。
统治者阳总是妄图否认它对阴的依赖。赫胥黎和奥威尔毫不妥协地呈现了成功否认的后果。通过对心理和政治的控制,这些反乌托邦达到了某种非动态的静止,不容许任何变化。平衡不可动摇:一面朝上;另一面朝下。一切永远是阳。
阴的反乌托邦在哪里?它有没有可能存在于劫后余生的故事和恐怖小说中,里面是成群结队蹒跚而行的僵尸,还有越来越流行的对社会瓦解、彻底失控,陷入混乱与动荡的幻想?
阳只把阴理解为消极的、劣等的、有害的,阳总是掌握着最终话语权。但根本就没有什么最终话语权。
眼下,我们似乎只会写反乌托邦。也许为了写出乌托邦,我们需要以阴的方式思考。我在《总是归家》(AlwaysComingHome)中试图写出一个。我成功了吗?
阴乌托邦是不是一种矛盾的措辞?毕竟所有我们熟悉的乌托邦都依赖于控制使之运转,而阴却不控制。不过,它仍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又如何运作呢?
我只能加以猜测。我的猜测是,我们终于开始思考如何将人类统治与无限扩张的目标,转变为人类的适应性与长期生存,这类思考是从阳向阴的转变,因此包含了接受无常与不完美,耐心对待无把握之事与权宜之计,以及与水、黑暗和大地建立情谊。
(2015年4月)
一群兄弟,一串姐妹
我已经逐渐认识到,男性集体的团结作为人类事务中极为强大的力量,或许比二十世纪末女性主义所认为的更加强大。
鉴于两性在生理和激素方面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数方面竟然如此相似,这真的很惊人。但总体而言,女性直接竞争的意愿和占据支配地位的欲望要更弱。因此,矛盾的是,在等级森严、具有排他性的团体中,她们彼此间的联结需求也就更小,真相似乎就是这样。
男性团体的固结之力必然源于男性竞争所带来的掌控感与引导力,来自对由激素驱动的主导欲的压抑和重视,这种主导欲往往会主导男性本身。这是一种显著的逆转。个人竞争与好胜心所产生的破坏性的无序能量,转化为对团队和领导的忠诚,或多或少流向了具有建设性的社会事业。
这样的团体是封闭的,认定“他者”为外人。他们首先排除女性,然后是不同年龄、种族、阶级、国籍及不同成就水平的男性,这种排外强化了排异者的团结与力量。一旦感知到任何威胁,“兄弟连”就会团结起来,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

纪录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在我看来,男性的团结是绝大多数庞大古代社会机构的主要塑造者——政府、军队、神职机构、大学,以及可能正在吞并其他所有机构的新机构,还有公司。这些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连贯而持久的机构的存在与主宰源远流长,几乎遍及全世界,以至于多数时候它们仅仅被称为“事情本就如此”“这就是世界”“劳动分工”“历史”“上帝的意愿”,等等。
至于女性的团结,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团结,人类社会也就不会存在。但男性、历史和上帝就是看不到。
或许把女性的团结称为流动会更好——一条小溪或河流,而非一种结构。我唯一能够确定有它参与塑造的机构就是部落和某种不规则的存在,即家庭。在由男性安排的社会中,只要是准许女性按照自身意愿组织起来的地方,往往都是随意散漫、不成体系、不分层级的,更偏向临时而非固定,灵活而非僵化,更有协作力而非竞争性。它主要在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运作,这是由男性控制社会决定的,是男性定义和区分“公共”与“私人”的结果。
很难知道女性群体是否永远不会聚合成大中心,因为男性机构针对此类聚合持续施加高压,从而预防了这一切。不过,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出现这种聚合。女性团结的力量来自互助的愿望与需求,往往也来自对摆脱压迫的追求,而非源自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对攻击性的高度控制。飘忽不定是流动的本质。
因此,当他们认为女性的相互依赖威胁到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威胁到了分配给她们的生育、抚养、服务家庭、服务男性的角色时,宣布女性的相互依赖根本不存在简直易如反掌。女性没有忠诚,不懂得什么是友情,诸如此类。否认是恐惧手中的有效武器。女性独立和互依的概念,遭到了自认为从男性统治中受益的男性和女性的嘲弄与仇恨。厌女绝不限于男性。生活在“一个男人的世界”,大量女性不信任自己,恐惧自己,就像男人一样或更甚。
姐妹情谊的本质与兄弟情谊的力量截然不同,很难预测它能如何改变社会。无论如何,它有可能缔造出何种图景,我们对此也只能略窥一二。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历史悠久的大型男性机构,这是巨大的变化。但当女性设法挤进这些曾排斥她们的机构时,大多数人最终都被这些机构同化了,服务于男性目标,实现男性价值。
在男性机构中,女性能够作为女性去工作,而不是成为男性的赝品吗?
如果可以,她们能彻底改变这个机构,以至于男性可能会将其贬低为二流,降低工资,并放弃这个机构吗?在某些领域,这种情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例如教育和医疗实践越来越多地由女性来处理。但这些领域的管理权,对目标的掌控和定义,仍旧归属于男性。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当我回顾二十世纪末的女性主义运动,我将其视为女性团结的典例——大家都是印第安人,没有酋长。那是一种尝试,试图创建一个不分等级、包容、灵活、协作、无组织、特殊化的群体,更为平衡地将两性团结在一起。
我认为,想为达成这一目标而努力的女性,需要承认并尊重她们自身那种难以捉摸、千金难换、坚不可摧的团结——就像男性一样。她们既要承认男性团结的巨大价值,也要承认性别团结相较于人类团结的劣势——就像男性一样。
在我看来,无论在何处,只要女性以自己的方式同其他女性和男性一起工作,只要女性和男性继续质疑男性对价值的定义,始终拒绝性别排他性,肯定相互依赖,怀疑侵略性,追求自由,女性主义就会继续并一直存在下去。
(2010年11月)
内在小孩与赤裸政客
去年夏天,一家做文化衫的公司请求我允许他们引用这句话:
有创造力的成年人是幸存的孩子。
我看着这句话陷入了沉思,我写过这句话吗?我觉得我写过类似的话,但我希望不是这一句。自从“创造力”这个词被公司思维占据后,我就不怎么用了。再说了,每个成年人不都是幸存下来的孩子吗?
所以我去谷歌搜了这句话。我找到很多搜索结果,天啊,有些真的太奇怪了。在大量搜索结果中,大家都认为这句话出自我,却从未给出过任何引用来源。
最奇怪的一个是在quotes-clothing.com(提供引语)的网站上:
亲爱的,
有创造力的成年人是幸存的孩子。
有创造力的成年人是在世界试图杀死他们,迫使他
们“长大成人”后幸存下来的孩子。有创造力的成年人
是经历过枯燥的学校教育、坏老师的无益言论和世上形
形色色的拒绝后幸存下来的孩子。
有创造力的成年人本质上就是个孩子。
你虚伪的
厄休拉·勒古恩
在这场顾影自怜的小小狂欢中,最为奇怪的部分就是“你虚伪的”,我认为这是实际写下这些胡言乱语的人含糊其词地供认了自己的伪造。
这句话本身的使用和普及甚至让我更为困扰。对词语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漠不关心,乐于将乏味的老生常谈当成有用甚至有启发性的概念来接纳,不在乎所谓的引言究竟来自何处——这就是我最不喜欢互联网的地方。一种“啦啦啦,谁在乎,我就想让它当个问询处”的态度,这是同时折辱了语言和思想的惰性思维。
但更深层的是我对这句话的厌恶:只有孩子是鲜活且有创造力的——因此成长就是死去。
尊重并珍视儿童新鲜的感知力,以及无边无际、变化多端的潜力,这是一回事。但要说我们只有在童年时期才能体验真正的存在,创造力是独属于幼童的功能,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在小说中,在对“内在儿童”的崇拜中不断遭遇对成长的贬低。
无数童书的主角都是反叛的怪人——那个因质疑、反抗或无视规则而给自己惹上麻烦的男孩或女孩(通常被描述为相貌平平,并且毫无意外多半是红头发)。每个年轻读者都会同情这个孩子,而且理当如此。在某些方面,孩子们或多或少都是社会的受害者:他们无权无势,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内在。
而他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热衷于阅读夺权、霸凌者自食其果、展示自我、实现正义的故事。他们渴望这样,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成长,宣告独立,从而担起责任。
但有一种文学既为孩子而写,也为成人而写,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人类社会被简化为孩子们好或有创造力与成年人坏或心如死水之间的对立。在这一结构中,儿童英雄们不仅是反叛者,更是在所有方面都胜过高压迂腐的社会和周遭愚蠢、麻木、心胸狭隘的成年人。
主角们可能会同其他孩子建立友谊,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理解——可能是祖父母般充满智慧的老者,肤色与主角不同,也可能是他们所处社会的边缘人或局外人。但他们无法从自己所处社会的成年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那些长者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他们。
这样的孩子总是正确的,比那些压制并误解他们的成年人更有智慧。然而感知力非凡、聪慧明智的孩子却无力逃脱。他们是受害者。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就是这类孩子的典范,彼得·潘则是他的直系祖先。
汤姆·索亚与这类孩子有一些共通之处,哈克贝利·费恩也是,但汤姆和哈克贝利并没有被作者带着感情偏向,只描述好的方面,或是在道德上过于简化,也没有自愿成为受害者。他们被描述为具备强烈讽刺幽默感的形象,也的确如此,这影响了顾影自怜这一关键问题。受溺爱的汤姆喜欢把自己看成被毫无意义的法律及义务残酷压迫的人,而哈克贝利作为个人与社会虐待的真正受害者,却没有一丝顾影自怜。
然而,他们俩都一心渴望长大,渴望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会做到的——汤姆毫无疑问会成为功成名就的社会支柱,哈克贝利会在海外领地成为更自由的人。
在我看来,感知力超群的自怜儿童受害者与内在小孩有些相似之处:他们很懒。责怪大人总比成为大人要容易得多。
人人心里都有个被社会压制的“内在小孩”这一观点,以及我们应当将这个“内在小孩”作为真正的自我来培养,并依赖它解放我们的创造力这一信念,似乎是对诸多明智多思之人表达过的领悟进行了过于简化的陈述。这些明智多思的人也包括耶稣:“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一些神秘主义者与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有意识地将童年作为汲取灵感的深层源泉,他们都提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必要保持儿童与成人之间坚不可摧的内在联结。
但将这种观点简化为可以打开一扇精神之门,释放我们被囚禁的“内在小孩”,让他来教我们如何歌唱、舞蹈、画画、思考、祈祷、做饭、爱人……?
华兹华斯的《不朽颂》(Ode:IntimationsofImmortality)对与孩童时期的自我保持联结的必要性与困难性进行了绝妙的表述。这首诗提出了一个让人深有体会、深思熟虑且非同凡响的论点:
我们的出生,无非是一场睡眠与遗忘……
这首颂歌没有把出生看作从空白的无与不完整的胎儿状态到完满儿童的觉醒,也没有把成熟看作一场行向空无死亡的渐趋收缩、枯竭的旅程,它提出,灵魂进入生命,忘却了自身是永恒的存在,终其一生,只有在暗示与得到启示的瞬间才能忆起,也唯有在死亡之时才能完完整整地忆起,而后重新步入永恒。

纪录片《勒古恩的多重世界》剧照。
华兹华斯有言,关于永恒,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启示,我们在童年时期秉持最开放的态度。纵然在成年生活中我们失去了这种开放性,当“习惯”笼罩在我们身上,“沉甸甸如寒霜,幽邃如人生”,我们仍旧可相信:
那些朦胧的追忆,
无论是什么,
仍是我们一整个白昼的光源,
仍是我们目之所及的主灯;
支持我们,爱护我们,并有力量让
我们喧闹的岁月,恍如永恒寂静中的片刻:
醒来的真理,
永不湮灭。
我尤为珍视这段证言,因为不用觉得它源于任何宗教信仰体系。信徒与自由思想者都可以共享这一人类生存观,即穿过光明,越过黑暗,再进入光明,从神秘到无尽的神秘。
在这种意义上,幼童的纯真无辜,对个人体验不做判断、不设限制的开放性,都能被视为成年人可以触及或重新获取的精神品质。我认为这才是“内在小孩”这一观念最本源也最理想的含义。
但华兹华斯并没有通过否认成熟的价值,或试图再次成为孩子来煽情地恳求我们去滋养曾经的那个小孩。就算我们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失去了自由、兴趣与快乐,但我们度过完满的一生,并不是通过停留在任何阶段,而是通过顺其自然,成为此刻这个我。
纵然没有什么能带回那时光
青草壮丽恢宏,花朵熠熠生辉,
我们不会悲伤,而是找到力量
从那遗留之物中;
从那曾经存在且必将永存的
最初的同情之中;
从那源于人类苦难
慰藉人心的思虑中;
从那看穿死亡的信念中;
从那带来哲理思考的岁月中。
“内在小孩”崇拜倾向于大刀阔斧地化简华兹华斯所留下的复杂内涵,关闭他所敞开的,制造并不存在的对立。孩子是好的——因此成年人就是坏的。做孩子很棒——所以长大就很糟。
毫无疑问,成长并不容易。一旦宝宝们能够跌跌撞撞学步,就必定会跌入麻烦。华兹华斯对此并无任何幻想:“牢房的阴霾开始迫近/降临到成长中的男孩身上……”向成年过渡,进入青春期,棘手且危险,许多文化都认同这一点,且往往以惩罚性的方式来认同,比如残忍的男性成人仪式,或是女孩刚一来月经,就立刻把她们嫁出去,从而残酷根除她们的青春期。
我把孩子们看成未完成的生命体,他们背负重任要去完成。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变得完整,实现自己的潜能——长大成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想承担起这项重任,并为此竭尽所能。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他们都需要成年人的帮助。这种帮助名为“教导”。
当然,教导也可能出错,成为束缚,丧失教育性,枯燥、残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出错。但只把教育看成对儿童天性的压抑,那就是对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世上每一位谆谆教诲的父母与老师的巨大不公,这既否认了孩子们成长的权利,也否认了长辈帮助他们成长的责任。
天性使然,孩子们必然不负责任,而他们的不负责任就像小狗或小猫一样,是自身魅力的一部分。当这种不负责任被带入成年期,就会成为实际及伦理上的巨大失败。失控的天性是对自身的浪费。无知不是智慧。天真无邪只是精神上的智慧。我们的确终生都能从孩子们身上学到很多,但“如孩子一般”只是精神建议,并非智力、实践或伦理上的建议。
为了看清皇帝并没有穿衣服,我们真的需要等待一个孩子说出事实吗?甚或更糟,等待某个人的“内在小鬼”突然语出惊人?若是如此,我们免不了要面对一大堆裸体政客了。
(2014年10月)
原文作者/[美]厄休拉·勒古恩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