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为什么会在今年大选中选择身负34项重罪指控的特朗普担任总统?美国评论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ldwell)11月28日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称,“我们这个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Streeck)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考德威尔看来,施特雷克与马克思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坚信资本主义存在某些不可持续的内部矛盾。
生于1946年的施特雷克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影响。在他的《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中,施特雷克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为应对经济危机,进行了税收国家(taxstate)、债务国家(debtstate)、新自由主义等转型和改革。他发现,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在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反而削弱了其所谓“民主”的支柱。
在施特雷克的新书《夺回控制权?全球主义之后的国家和国家体系》中,他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危机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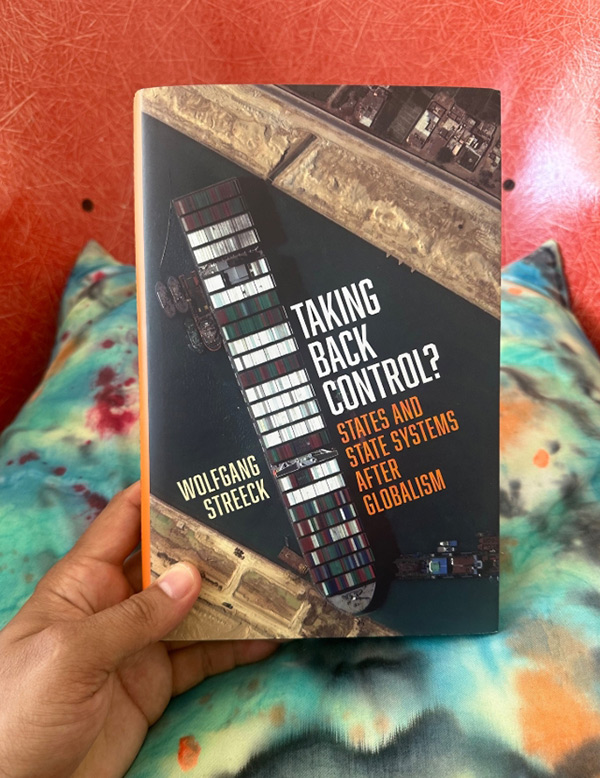
一名读者手拿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新书《夺回控制权?全球主义之后的国家和国家体系》。社交媒体平台
“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大师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目前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崩溃,是预示着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回归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未来,还是预示着其它更有希望的前景?”《机器时代》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称,施特雷克的新书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人性化的去全球化制度。
考德威尔也在文章中写道,施特雷克的理论清楚地阐述了由美国驱动的全球化复杂齿轮结构存在的问题。在施特雷克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矛盾已经积累了半个世纪。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赢得了丰厚的收入和广泛的保护。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73年阿拉伯国家宣布石油禁运后,西方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工人们投票要求更多的权利,但企业无法满足工人们的需求,政客们只好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工人们的需求。
但这种策略,从本质上说,是政府在向下一代人贷款。施特雷克表示,战后增长期过后,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开始将尚不存在的未来资源引入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中,但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改掉这个习惯。
施特雷克此前在接受中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采访时解释道,债务会推动增长,因为必须偿还债务及其利息,这样就增加了借出资本的价值。如果有增长的机会,一切都很美好;但如果无法大规模偿还债务,资本主义的增长就会停止,资本主义经济和依赖它的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考德威尔在文章中指出,扩大货币供应量很快引发了通胀,需要痛苦的紧缩货币才能稳定价格。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供给经济学”稍微缓解了这种痛苦,但结果是政府赤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施特雷克发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有机会消除这些危机,但必须通过放松对私人银行和借款的限制。也就是说,危险的债务敞口从政府部门转移到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银行账户。这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安抚经济的尝试(主要是美国的尝试),最终发展成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体系。在施特雷克的眼中,这是一个“政治经济项目”,旨在结束通胀,并将资本从战后和解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SocietyfortheAdvancementofSocio-Economics网站
施特雷克强调,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关键决策都是由技术官僚、专家和其他相对不受“民主问责制”影响的行为者做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央行行长介入接管了经济,设计了量化宽松和其他产生流动性的新方法。
新自由主义的提倡者认为自由市场是指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但施特雷克看到了“新自由主义项目”中的自相矛盾:全球经济要想“自由”,就必须受到限制。在自由社会中,监管是人们使用主权权利制定规则的结果。社会越“民主”,经济规则就会越复杂。但这是不为企业所容忍的,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和货物必须无阻碍、高效地跨境流动。这需要一套统一的法律,也意味着,“民主”必须让步。
全球化还要求一个国际规范,现行制度下的全球体制是美国体制的复制品。施特雷克指出,同一的规范带来了秩序和效率,但也使竞争环境向有利于美国公司、银行和投资者的方向倾斜。施特雷克解释道,这也许就是西方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的矛盾所在。俄罗斯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过渡“受到美国政府机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严格控制”。对印度或中国来说,这些“自由市场”可能带有帝国主义的专横和失去主权的威胁。
考德威尔认为可以用施特雷克的观念来解释特朗普如此受欢迎的原因。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由于我们不再有‘民主’管理的经济政策,它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施特雷克所指出的那样,普通人在“全球经济”事务上没有影响力,而左翼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放弃了对工人权利和生活水平的关注,转而专注于呼吁平权等价值体系的构建,这一转向疏远了很多人。
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民主”正在蓬勃发展。在选民投票率持续几十年的下降之后,参与率在过去20年里开始稳步上升。考德威尔称,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倾向于支持施特雷克所说的“标准模式政党”(partiesofthestandardmodel)的自由派评论员已经改变了他们对“民主”的定义:他们认为高选举参与率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不满表达,这“危害而不是加强民主”。
施特雷克也认为“民主”处于危机中,但这是因为“民主”被声称支持它的精英们阻挠了。当下颠倒的“民主”理念伴随着一种新的政治策略。标准模式政党的议程,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其他全球化重要提倡者的强化。斯特里克写道,这些人“与新一轮政治化浪潮作斗争”,“他们掌握了一整套工具——宣传、文化、法律、制度”。
考德威尔指出,施特雷克在这儿说的可能是对欧洲左翼设置的障碍,但他的观察同样适用于右翼政党。在欧洲,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正在接受审判,上个月100多名德国议员要求禁止支持率正在上升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美国,大选前特朗普背负34项重罪指控,但大多数美国人在大选期间通过投票箱宣布“豁免”他。
“随着全球主义在自身的矛盾下崩溃,所有严肃的政治现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向了民粹主义。”考德威尔在文章最后写道,施特雷克的新书并非关于特朗普的胜利,但他传递的信息非常值得注意——左翼必须拥抱民粹主义,其实民粹主义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潜在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