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大学毕业的老六(黄国良)因为在支教时目睹乡村教育之破落、留守儿童问题之严重,而选择投身于改变乡村的事业中。在那个热血年代里,他一毕业就投身于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是一所为培训农民而生的学校。后来又经历了北京、重庆、广西等地多家机构的辗转,却始终没有离开改变农村、帮助农民的工作场域。
二十年后,老六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乡村工作者。我们邀请他回顾那些往事,谈谈他的工作如何回应农村的现实问题。虽然老六谦虚地说,他不懂大问题,也无法看清未来的方向,但不读懂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他的经历与见解仍然值得今日乡村事业的关注者深思。
大学支教:思考乡村问题的开始
大学时,我学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治沙”专业,全称叫“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治理”。
我虽然是广西人,但去了陕西上学。因为那个时候倡导西部大开发,西北地区荒漠化问题严重,高考时我才报考了治沙专业。但是上大学后,我每天都很郁闷,因为我们是冷门专业,同专业的大多数人都是调剂来的,就为了重点大学的毕业证。
去学了专业知识之后就更加失望,那时候都说“大学生就是中国的未来”,但我们专业的很多前辈进入所谓“机构”上班后,就是整天喝茶、看报纸,没有什么事情干。反而一些民间人士,人家拿着一把铁锹就投入治沙一线,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学校里教授的专业课很多却是教沙漠里面修水渠,在不应该种树的地方种树。当时我的心态三观都在崩塌,也没有长辈能给出指引,整个人是迷茫的。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教育是不是有问题?
上完大学后,我也没有想在社会上找工作,刚好那时候有西部志愿者计划,便报名参加了。当时去的陕南的一所乡镇小学当支教老师,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深。
当时我去教的五年级的数学。要知道,让一个支教老师教主科,还是五年级的学生,这说明学校很重视我呀,我还是很兴奋的。但结果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人都傻了:全班48个孩子,只有一个人及格,剩下全是不及格的,还有考几分的、十几分的。
我的学生告诉我:“老师,他们把班级都打乱了,把好的挑走了,把差的留给你了。”我才知道有个排名制度:如果班级今年排名不好,老师就要被发配到更偏远的小学去。当年跟我合作的是一个还没有转正的老师,不在编制内。而我是个支教老师,也无所谓。
了解这些事之后,我就更认真地教学,还得了300块钱的奖励(当时在当地还是一笔不少的奖金),因为我教的班级学生90分的比例、过及格线的比例等等指标都快超过好班了。校长高兴坏了,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个多年来倒数的班级,一下子就甩掉了倒数的帽子。
但当我开家长会的时候,来的都是爷爷奶奶,有些孩子甚至没有家长来开会。他们说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到了下半学期,有两个个头比较大的女生跟我说:“老师,我不能跟你上学了。我要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第一次遇到这样情况的我当时就傻了,这才是五年级的学生呀。从那之后就再没有她的消息了。
在那之前,我一直在上学,从没有接触过这些现实。现在仍有很多大学生看不到真实的乡土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跟随老师参加一些调研,可能去的也都是明星村、示范村。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即使我自己带娃很辛苦,也不愿意把孩子丢回老家去——我就是目睹留守儿童问题才走上乡建这条路,不能再把自己的孩子也弄成留守儿童。
支教的经历让我看到教育有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村子里没有人,中国的乡村出了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要去参与乡建的原因之一。
在乡建学院,通过合作重建乡村秩序
我到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时,是2005年的夏天。当时邱建生、黄志友、潘家恩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快两年,但学院还是处在开荒的状态。


●年轻的老六在乡建学院,下图的驴后来被带到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成为农场的象征。
那时候办乡建学院,想的是建一所真正办给农民的学校。因为很多所谓“农业教育”并不是面向农民的,农民是没有地方学习知识与技能的。
所以我们想探索在村庄里面办学校的可能,面向全国召集学员。在纸质媒体时代,温铁军老师的《中国改革》杂志还是有相当传播力的,再通过农民之间口口相传,学员觉得课程不错就推荐给同村的村民。
乡建学院当时主要教农民这几件事:合作经济、生态农业、生态建筑、试验区工作、志愿者培养,还有帮助农民开展其他的方面合作。
当年已经有像河南的南马庄、安徽的南塘合作社这样的“明星”,也有一些小合作社在运作。我们也尝试收集全国各地的案例,讲给农民听;同时把合作社的问题理论化,尝试把“农民合作社”的概念推向大众。
尽管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呆了三年后就离开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于2007年关停),但是回头看,还是有很多让我们欣慰的事情,比如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法》的出台,我们当年的工作多少还是有一些贡献。在那之后,虽然合作社“真假李逵”层出不穷,但至少大家都知道,农民去做合作社是一件受法律保护的事。包括这几年从原来只允许做单一生产性合作社,到允许综合性合作社,也是一种往前走的探索,口子在一步一步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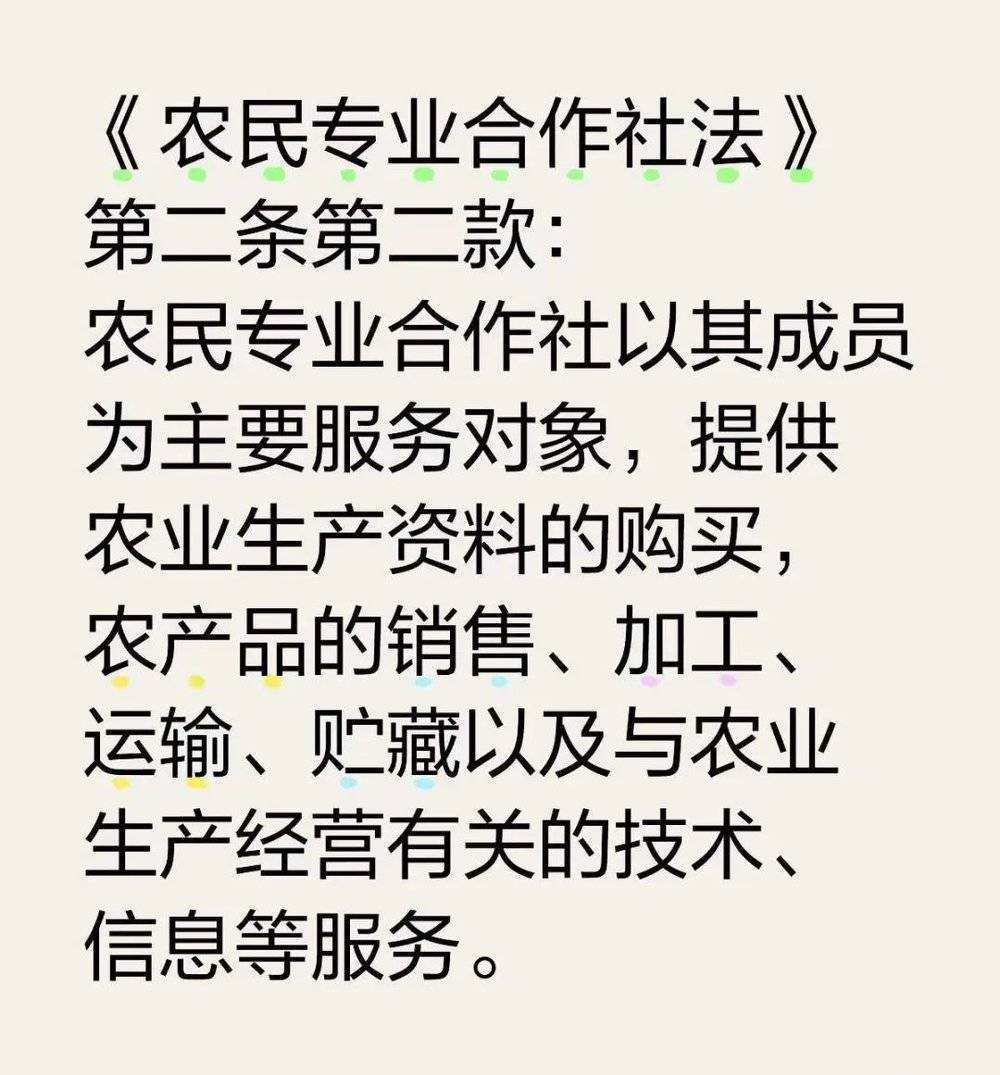
●2006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允许五名以上的成员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2017年修订时又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相关规定。
当时重提合作社,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村庄需要重新构建内部秩序。当时的村庄存在劳动力外流的趋势,在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之后,只剩下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群体,甚至村长、支书都没有精力去管理村庄了,村庄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此时的乡土是需要有人去协助的。合作社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协助,这并不是说村庄要回到过去的公社时代,而是帮助村庄从失序走向有序。
二是解决分散的小农面对市场的问题。面对市场不仅仅是把东西卖出去,也包括从外部购买,合作社类似于当地中介的平台。
看待合作社能否解决村庄失序的问题,关键在于怎么理解合作与组织。以前在乡建学院的时候,我们也常讨论什么是组织。比如当时我们发现:河北平原浇地是各家轮流的,一口井管周边几块地,需要有一个井长管理排队的秩序。排到你家是凌晨三点浇水,你就得凌晨三点起来,错过这个时间,对不起没水了,等下一次人家浇完了你才能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组织的形式。
并不是说村庄只剩老人、儿童、妇女就没有组织了。组织依然是有的,只是不像青壮年劳动力在村的时候,那样有秩序和活力。
当年的失序是突然分崩离析。大家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糟糕的状况,政府也没有办法兼顾。零几年的时候,农业税取消,地方政府的资金被抽掉了。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随着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运动,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政府将秩序又重新构建起来。虽然人口依然在外流,现在政府可以安排社工站、驻村干部去处理问题,但当时村一级是虚的。当然乡土也还存在一些秩序,比如只要白事发生,就会有人站出来主持活动。
过去乡土社会的合作是基于中国的农业生产状况,比如农业用水就需要整个村的人合力才能解决。因此,先有需求才会有合作。过去整个乡土社会是一个小小的系统,在运作时呈现出多元的需求。但是当青壮劳力外流,农业生产结构也变得很单一的时候,这种需求就不会频繁地出现。比如现在的水渠维修,可能政府请个施工队就解决了。
但是乡土中组织的文化基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会偶尔复活,就像给整个村子短时间内“插上氧气机”。比如在生死大事的时候,此时村子里面又凝聚起来,短暂地活跃一下。所以我们推动合作社的时候,是面临着原有的需求没有激活,导致很难从外力推动合作社或村庄发展起来的情况。如果村民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合作互助,村子里面很多公共事务是可以做起来的。
我们首先想到的公共事务,是道路、水利这些基础设施没有人管。其次,文化先行,村里的老人、妇女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大家更多关注的还是收入问题,所以各地才组织了经济合作社,比如南马庄“教授卖大米”,有统购统销,降低农民风险。统一购买农资,降低成本,相当于给农民省了一笔钱。
同时我们还在思考,除了合作社之外还能做点什么?所以才会有生态农业工作室、生态建筑工作室。
我当时也是在生态农业工作室负责种地的人之一。乡建学院里面有一块地,但是大学生们谁也没干过农业,生态农业工作室就把麦子地、果园等等管起来,变成一个自循环系统,然后积累经验,再去跟农民推广。当时大家都没有做过生态农业,只能粗糙地提出“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的“三无”理念。没想到20多年后,很多人还在用这几条标准,这其实是一个很粗糙的概念。

●乡建学院的麦田。老六后来对于生态农业的更多看法,详情见整理稿的上篇。
搞生态建筑更看重的也是协力。以前农民造房子是靠大家互助来建设,不用靠现金支付,就把房子盖起来了。现在都是请施工队或者包工头来负责,农民必须要进城打工,换来现金,才能盖房子。请施工队来盖,确实又快又好又漂亮,但你支付给他的钱,他用来从外部雇工,工资不会在当地花销,原材料也是从外面拉来的,这是一个流失、开放的链条。
如果请大家互助,今年你帮我盖,明年我帮你盖,虽然可能盖得慢一点,也没那么好看,但是房子同样盖起来了,同时积累与触动留在内部,这个链条是相对闭合的。

●老六和黄志友(现任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在学院的生态建筑前。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社会变化的缩影,从“互助造物”走向了“商业造物”。教育也是这样,原来可能在村和乡一级就能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现在必须到县城。农民面临的是买房的压力和更大的教育投入,种地没办法支付起孩子的上学成本。而且十多年以来,这种成本还在不断地提高。
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商品化的方式,打工赚钱完成阶层跃升,这确实是一条道路。但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式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只有一条路。当农民不想被卷到城市里,走完全商品化道路的时候,另一条路在哪里?现在是没有的。

●当年的年轻人们在离开晏阳初乡建学院前的合影。
重返广西与老种子保育
其实农业的问题不只在农村本身,而在于大家怎么去思考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市通过教育、医疗各种集中,就像抽水机一样,不断地从农村抽资金、抽资源、抽人才。关于城乡应该怎么发展,不应该只是农民的问题,城市的人如何去看待这种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北京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的定位是一个教育的窗口。它不只是在尝试商业化的配送模式,而是希望它变成市民了解农业、了解城乡问题的窗口。现在有更多人来做类似的工作,但以前的市民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了解农民、农业、农村。




●小毛驴市民农园2008年成立于北京海淀,一直运营至今。这里也是中国最早实践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Agriculture,CSA)的农场之一,市民可以租份额地,由农场配送到家,也可以自己租地来农场劳动。图1、2:2008—2009年,众人从一片荒地建设出菜园,最初的一批年轻骨干许多来自晏阳初乡建学院;图3:老六和农场工人在一起;图4:市民前来农场劳动,管理份额地。供图:老六、小毛驴市民农园
前面只说到市民了解农村,但另一个问题还没有回应到,如何解决小农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不断有打工潮人口外流的趋势。
第一批打工潮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到2011年我离开北京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又过去十几年,那一批老的打工人已经干不动了,他们将面临回农村或留城里的选择。但流出去的打工人回得去家乡吗?或者应该怎么返乡?
恰好西南是人口外流最大的一个区域,我当时最感兴趣也是这个问题。离开北京后,我跟几位朋友办了重庆打平伙社区食堂,后来机缘巧合回到了广西。自从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我从来没有好好认识广西,在社区伙伴(PartnershipsforCommunityDevelopment,PCD)工作的那几年有这个机会。那时候作为社区伙伴工作人员,可以天天下乡,了解农村真实的状态,也并不觉得苦。


●2012年,老六在重庆办国仁打平伙社区食堂,食堂提倡“本地生产,应季消费”,由买卖双方共担成本。
那时候,我们在本地做了不少保护地方品种的工作。
谈及品种保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鉴别一个品种是否是地方品种,不是用种植多少年去衡量的,也不只是以是否适合当地种植去判断的。举个例子,广西很适合种砂糖橘,但砂糖橘其实只是当地的经济作物,受市场的波动影响非常大,风险不是农民可控的,它不能算是当地的地方品种。
那么该如何定义地方品种呢?除了要适合当地种植,第二个条件就是,需要跟当地生活、文化紧密相关。举个例子,广西当地节日在包粽子或者做粑粑时必须用到特定糯米品种,他们不接受用其他品种的米来做这些食物。这样糯米本身绑定在文化系统里,可以成为地方品种。
我们要去保护它们,一方面是因为品种在消失,我们出于种质资源的重要性而推动保护。毕竟农民的精力是有限的,种了经济作物后,粮食、蔬菜或者油料作物可能就不种了,用种砂糖橘的钱去买可能是转基因的油,或者农药化肥种出来的米。这其中也包括健康、环境等等隐性成本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探索另外一条路:不一定要买口粮、买油料作物,至少自己家保障自己的口粮安全是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很多农友意识到了这点并做出改变,原先他们没注意到,这几年可能是被我们天天啰唆,听多了的缘故,他们也开始重新去种水稻,在菜园子里种上菜。


●老六在广西国仁开办水稻选育班,培训农友对地方品种做引种、保种、留种、提纯复壮。
其实和一般想象的留种不一样,保种、育种等一系列操作,是非常专业、非常耗人力的事情,而且重要的种子都被国家收到种质资源库了。我们去推动的时候,一般不跟农民强调这个品种会不会失传,因为该有的种子,库里都有备份。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民都去专业地搞育种,一个镇有两三个人感兴趣,能坚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
但如果大多数农友都能够做到留种和提纯这两件事情,那就很有意思了。留种并没有很复杂,你到稻田里面认真一点走一圈,留一下种子,这件事情就做成了。
拿水稻举例,有些地区隔一条山就有两三个水稻的品种,整个区域就有二三十个品种,因为有病害,他们也经常交换种子,区域里自发存在着流通。正如刚刚提到的,提纯是件繁杂的事情,原来这二三十个种子可能是几个村、几百号人在保护,如果把原来上百人完成的事情让一个农友去完成,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跟农友说,保留你感兴趣的种子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一些农友对种子是很有热情的,这是值得鼓励的,但并不建议所有农友都专门做这件事。如果每个农友留三四个品种,这样的农友多了之后,附近可能有二十个人在做相似的事情,互相之间有联系,想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就容易得多了。


●广西生态农友年会上,生态农友交换各自带来的种子。图源:山水涅槃朴门中心
二十年后的变化
最近我在广西下乡,看到的情况又和过去有所不同。原先路没修好前,人们光走出村子可能要花三四个小时,但现在公路和高铁修好了,人们的流动性更强,乡村空心化问题并没有缓解,重建的秩序也是严重依赖外部资源支撑的,这也是广西乡村发生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虽然大家离开土地已经太多年,但现在离乡村还并不远。暑期我和消费者聊天,他们说,我一脚油门就到老家了,所以这种割裂感还不是那么强烈。但随着城市更加集中,在未来一代的时间内,这种割裂感才会慢慢呈现出来。
我父亲那一辈已经六七十岁了,当时出去打工的还比较少。以前在家乡还做过农业,可以说,他们就是最后一代承接传统农业的小农。但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已经不了解父辈是如何种地的,从小直接学到的就是如何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所以,我担心的是当老一辈农民走了之后,四五十岁的农民将怎样面对农业。而且,他们还将背负着教育、医疗、养老,这新的三座大山。
未来经济发展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不是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去预判。农村未来的出路还要靠新一代农民自己去探索,去想象。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找到这条路,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想走那一条路,有些路是走得通的。
关于老六对生态农业的思考、在广西组织生态农友培训等经历,请参见整理稿上篇《离开书本,怎样办一场“言传身教”的农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