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谜团:关于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永久不平等条约这个事情,之前有人说租借100年,现在原版来了,不是永久割让,我们说的是给予。 在《南京条约》的文本中,英文版使用了"cede"这个词来描述香港岛的主权转移。这个词在当时的国际条约中通常被用来表达领土转让的含义,但在中文译本中被翻译成了"给予"一词。 翻译的差异造成了后续诸多争议,因为"给予"在中文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临时性的让与,而不一定意味着永久性的割让。 如果我们对比当时英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殖民地条约,会发现英方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时惯常使用"cede"或"grant"这样的措辞。这些用词在英国的外交文书中往往暗示着永久性的领土转让。 中英双方对条约条款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语言表述上,更反映了双方在领土主权认知上的根本差异。 在香港问题上,实际上存在三个关键性的条约文本,每个条约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效力。《南京条约》是第一个涉及香港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其核心内容是关于香港岛的主权转移。 《北京条约》则将九龙半岛划入英国统治范围,这份条约的措辞与《南京条约》相似,同样使用了模糊的表述。而1898年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则明确规定了新界99年的租期,这是唯一一个明确提出租借期限的条约。 这三个条约在用词上存在微妙的差别,《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使用了"租借"一词,而前两个条约则使用了可以引发歧义的表述。 从法律文本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条约构成了英国统治香港的法理基础,但每个条约的性质和效力都有所不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的99年租期成为后来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重要法理依据。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充满了不平等和强迫性质。 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翻译困境,当时能够精通中英双语的译员极其稀少。这种语言障碍导致清政府在理解和表达条约条款时存在诸多误差。 英方谈判代表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条约文本的起草过程中采取了模糊性的措辞策略。他们在英文版本中使用了具有永久性含义的词汇,而在中文翻译中则采用了较为含糊的表述。 这种翻译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条约的解释和执行。在清政府看来,"给予"一词并不必然意味着永久性的领土转让,而英方则坚持这是永久割让的明确表述。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领土主权的转移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双方的真实意愿。而《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 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列强普遍采用武力威胁的方式获取殖民地。这种背景使得《南京条约》在本质上就属于不平等条约的范畴。 中国近代史研究界对《南京条约》的性质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这份条约是在军事威胁下被迫签订的,不具备平等自愿的特征。 近年来,随着更多历史档案的公开,一些新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不平等性。英国外交部的部分解密档案显示,英方确实有意利用翻译差异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对于理解条约的真实性质具有重要价值。它们揭示了英方在谈判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手段。 各国学者对这些历史档案的研究表明,《南京条约》中关于香港的条款存在明显的操纵痕迹。英方通过精心设计的措辞,试图为其殖民统治提供法律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对这些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基于充分的历史研究和法理分析。 历史档案还显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对条约内容并没有完整的理解。语言障碍和外交经验的缺乏导致他们在谈判中处于明显劣势。 从文献记载来看,英方谈判代表对利用这种优势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刻意在条约文本中设置了有利于自己解释的条款。 而在条约执行过程中,英方始终坚持其单方面的解释。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国际条约的基本原则。 这些历史证据共同构成了否定《南京条约》效力的重要依据。它们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这份条约的不平等性质。 新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首先确立了对不平等条约的否定立场。这个立场基于充分的国际法理论和历史事实支持。 "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方案。这一方案既考虑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也照顾到了香港社会的现实情况。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在香港问题上达成了正式协议。这份协议的法律效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新界99年租期的到期成为推动香港整体回归的重要契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将香港分割管理是不可行的。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为香港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更加重视和平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为香港回归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实力的变化使得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在整个香港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准确的语言表达和理解对于国际谈判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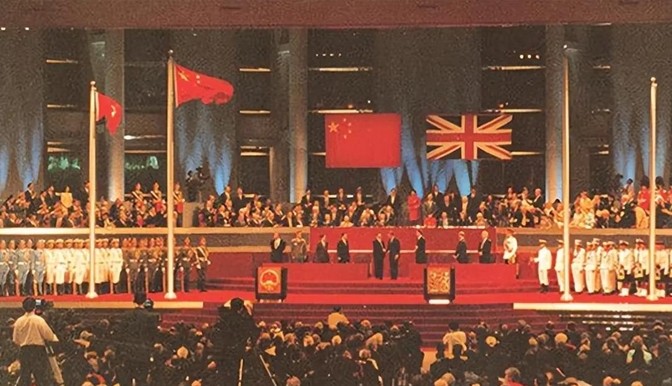
新中国1949年10之后,就已经全面否决了自1840年之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就是只要我们不承认的,那就是不平等条约。所以,不论是南京条约还是北京条约,自1949后就已经失去了一切效力,谁不服就干。再有,如果要真实解释,那就是当年的香港已经全面沦陷,是被日本攻陷的。原则上,自那以后起香港就与英国无关了,民国政府在二战胜利后就已恢复了主权,而英国人不要脸的重回去香港,不代表他们合法理。

用户88xxx40
玩弄这些文字游戏毫无意义。国家实力强,丢失的领土自然就收回来了,国家实力不够,列强上门打脸也只能陪着笑脸。
用户10xxx26 回复 02-11 13:19
打倒老美,压制老俄,我们就是第一了,那时美粉们再看俄熊还不还。
用户10xxx70 回复 02-11 13:20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把土地还给北美印第安,澳洲土著,新西兰毛利了吗?
用户10xxx86
措词只是在平等时有用!不平等时没有用。当年大清敢要吗?当年邓公时英国敢不给吗?
河塘独醉 回复 02-14 13:37
看你很能洗,瑷珲条约给都不要,你给洗一下呗
只买国货 回复 河塘独醉 02-25 15:41
中俄是边界划分,香港岛是割让,不要胡扯。
闲庭信步
爱咋写咋写。条约是约束弱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我们祖宗早就对全球宣誓主权了。
本家三哥 回复 02-13 18:18
对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还包括月亮及银河星宿!
glia
欧洲的规则是打一仗签一个条约,对条约内容不满意,再打一仗再签个新条约。英国答应归还香港,是因为它们肯定打不赢,而不是条约文本的问题。
用户34xxx54 回复 01-31 15:25
所以条约就是一张纸,斯大林也是这么说的。随时可以撕毁
豆沙包 回复 用户34xxx54 02-12 06:18
所以合同就是一张纸,双方实力不平等就可以随时撕毁?
zxyemoren
其实实力强时,直接派兵拿回来也行。。。主要是你要有那个实力
zxyemoren
其实实力强时,直接派兵拿回来也行。。。主要是你要有那个实力😂😂😂
用户15xxx86 回复 02-07 13:55
你给不给,不给我自己拿
萌太郎多肉
偷换概念,玩文字游戏。不管是什么,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宣布了,不承认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明天会更好
挺你!自身强大才是真理,
以后再说
大清帝国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挨揍有一大半是自己犯贱自找的,不遵守契约精神,天天搞算计又菜又爱玩。
江渐月 回复 02-05 12:02
狗屁的“契约”就是列强可以对弱者玩弄不平等条约的手段是吧?!
用户10xxx55 回复 01-30 13:09
清朝没有步入奥斯曼土耳其的道路你很难过是吧!
小书蟲注定一生孤独的猪
条约签订的目的就是为了撕毁 条约有效期直到下一个条约签署 尘埃落定了 没必要继续讨论 这个世界永远是拳头大的有理 昨天牠可以用大炮火枪逼着你签署那样的协议 今天你也可以用导弹氢弹逼着牠吐出吃进嘴的东西 人类历史数千年来莫不如此
$←_← 回复 02-15 09:37
当我们的巨舰兵临英格兰城下海岸,被抢走的文物,还有他们自己的文物都要吐出来
狙拉波
海参崴是租借50年,1996年到期
chinazjf
我们不纠结于这些无聊的词汇。如果说当年我们是无条件的给予让渡或者割让等那又如何呢?当年我们也是被迫被胁迫,现在我们强大了,我们要胁迫你们把你们吃的吐出来。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那有本事再来一战?
用户16xxx43
那都是废话,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纵横三万里
实力即是权力。重回世界巅峰,割占英格兰也非不可能。
张扬的嗨
条约是英国在武力威胁下签的,中国也就可以在武力支持下废除。很合理。
用户11xxx20
我们的大炮“粗”,就按我们的解释来。
袁建民
港岛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給英国的,尖沙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北京条约割給英国的,是永久的,九龙新界是1898年租給英国的,租期是九十九年,到1997年租期到了,九龙新界应该归还中国,英国人认为还了九龙新界,香港岛尖沙咀也没有价值了,索性连港岛新界一块还给我们,这样又保住了利益,又增加了对香港的影响。
$←_← 回复 02-15 09:47
想太多,人家想的是只还九龙新界,是邓公谈判时强硬的要求收回所有领土,英国佬的舰队有33艘船当时就在南海,邓公当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不服打一架,英国佬最终没敢动手,怕被灭国[打脸]
闲事不管
对强盗就是要打他个大嘴巴子
沧浪之水
根据条约,香港岛永久割让,九龙和新界是租借,1997年租借到期。但香港岛太小了,无法独立存在,英国佬1997一块交还中国了。英国佬没有那么善良,在谈判中,英国佬一直想用主权换治权,但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了。
ly7575079
中国在建国时就已经发表过声明,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那些被迫签订的条约都是废纸
袁建民
九龙新界是租,租期99年,港岛和尖沙咀是永久割让。
绿水青山
有什么好争议的,前面就是割让,后来香港要扩建,又租了一部分,叫新界。回归时,英国只想把租借的新界还回来,本岛不想给。后来经过反复谈判英政府才同意,但签了很多限制条款。这些限制条款也是今天香港动荡的根源。
captor_456
抠字眼没意义。印度从葡萄牙手中抢夺果阿地区还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呢!就是借口联合国的反殖民地号召。有印度强收果阿的先例,中国收回香港英国根本就不敢不答应!1949年时英国就做好了丢掉香港的心理准备。
夏日芒果
废话了半天,那还不是国家强盛了才能抗争吗?国力弱说什么也是废话。
dadidi
不管怎么翻译都没用,不平等的条约必须废除!
非翔Leonardo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第一天,就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谁还管里面的措辞?
用户10xxx11
租借99年的只是新届九龙,香港本岛的确是无限期的,不过这种通过武力签订是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同样也可以用战争来让条约重新签订,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处就说了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他们既然承认中国就等于承认条约。
盘整
英国人就是操蛋,事事都给你埋雷。
老古董
文章说的是什么意思?条约也罢条款也好?最终执行情况要看实力!!!!
用户10xxx20
国家强大了,解释权就在我们自己
午时真言
国家强大才是硬道理。香港的成功收回。着实让中国人民骄傲了一把!我们的奋斗就是为了强国富子孙。
pattonsun
弱时友好协商,强时自古以来,当然现在学了招新的,可以翻翻山海经什么的[得瑟]
蓝枫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老四
条约,只是暂时的约定而已
用户10xxx57
中国应该对英国给于更多的关注。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这个岁数
废话什么,055不行上076
看着办
新中国成立后就宣布,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
忠伟
什么条约,我们一律不承认,
专业怼口嗨
香港太小了,而且是个金融中心,肯定得要回来,都是大清丢的,你看看外东北,蒙古,贝加尔呢,
tb064675294
等你实力到了,就是把伦敦当香港一部分给拿来,他大英也得笑脸相迎给送来!
巴巴爸爸
强盗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早就在新中国建立时就不予承认了。
phil
谈判的官员们个个都懂,但皇上只看得懂中文版,所以……,你明白的
欣之辰
老子落魄的时候你有本事就拿去,现在老子发达了你一分钱都不能少都得给老子吐出来。少一分钱老子都必须自己去你家里“拿”。
Al自助直播省九成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条约解释权归实力强一方。
用户15xxx53
关键是看谁的拳头大!
惊天
看录取分数线就知道谁更好。
饿了就吃
去签个伦敦条约吧。在那边租块地。一元人民币一万年的。就照香港大小圈地。
huang
我看过的解释是,当时的国际法规定,租借别国土地最高不允许超过100年,所以是99年。
嗨皮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158
现在还来纠结这些措辞小编想干什么?1949年没有收回就是给了英国佬很大的面子了。
无忌
靠拳头说话,靠几个单词么
失魂人
我们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手里有家伙谁都敢打,谁都能打过,没有实力一切免谈,以为他们发善心了?
用户10xxx50
怎样失去就怎样要回来,没问题。
用户12xxx24
拿老子的 早晚都得给老子吐出去 条约算毛线
墨鱼蛏子
好像是瞎扯,十九世纪国际条约的最终解释文本是法文版。
diang008
香港岛是永久割让,新界部分99年租借。。
用户10xxx86
川普直接要那些土地,有条约?
尘缘如梦
实力弱,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实力强,不是你的也是你的。
我是风儿你是沙
收复外蒙古,收复外东北
闲村客
什么意思都没意思,新中国根本不承认任何不平等条约!用的着抠字眼吗?
用户18xxx94
说得好听大家过得去而已。不然打下来英国佬面子更难看
事太颜良
不用武力,谁愿意把土地给别人,难道还有自愿送人土地的国家?
柿蒂
敢BB,嘎了伦敦
yb无聊
尽扯淡,当年丢失是大清实力不济,后来收回那是因为对方实力不济!这是没见过邓公当年的发言,我们就是凭实力和邓公的魄力 霸气给收回来的!
只为正义
白写那么多字,乌东四州是什么性质?实力到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当初这个条约的签订不是以实力为前提的吗?香港与日落帝国本来八竿子打不着好吧!
驻倭华军
都是拳头来决定的
用户10xxx16
我们为啥要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
用户16xxx20
在绝对实力面前,这些旁门左道都不过是一堆废纸
笨笨
不给97年就打过去了。铁娘子当时就吓得花容失色。匍匐前进了
用户14xxx16
玩森么文字游戏实力在就说啥是啥,不服就揍他,揍到他服为止
大圣齐天
割让凭啥。不就是坚船利炮。我们的大炮也可以直指英格兰。去把伦敦弄回来。让代英也割让一块。
琉璃药师
国力的增强才是能收回香港的关键
镇倭大将军
收都收回来了还说这些干嘛?居心何在?
用户10xxx16
屁话,有本事就开打,没本事写的再漂亮也没用!实力确定一切
焰火
屁条约,再打一次,赢了还是英国治理,输了就特么得交回来。再哔哔,打到苏格兰签条约。
愚公
扣字眼有意思嘛?你实力够,随便什么字都能拿回来,否则就是扯淡!邓公伟人!
冤家
西方列国走进历史舞台后使用英语很正常英语的多译为以后可以带来很多谈判空间。
北纬34º
实力强大了,条约算个屁,丢失的再拿回来就是,不行的话打他丫的。你能抢我就能夺,条约只是文字游戏,给双方吵架的佐料。
留一半清醒一半醉
解释那么多干什么??英国不服气的话,我们可以单手吊打一次英国。
用户15xxx92
再打一仗,看灭不了丫的。
飞鸿雪泥
本质就是抢的,国家强大了不交也可以要回来。就这么回事儿。
用户10xxx15
老子不管什么给予还是割让,只要老子够强,是我的给我吐出来,不是我的也是我的。
CoICe
建国时,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解释在我
用户10xxx68
欺软怕硬而已,北方大国抢的一寸也不敢收回来
用户10xxx02
条约写的是给予,我给予你的时候是你的,现在我不给予了,那就是我的
pjz
实力强大了可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
Mickey
拳头是最准确的语言!当年给它是因为它拳头大强抢。如果它现在拳头比我们硬我们也拿不到。条约是给弱者的最后一丝体面。
小鱼
一切不平等条约作废
普通人
模糊那就按各自理解办,最终各凭实力,反正条约签订也是从实力出发的非平等条约。
踏雪无尘
现在讲一百年前的条约有个鸟用。看看美国是如何遵守条约的就清楚了
吕老
滚蛋!这些条约!
用户13xxx75
就算满清是永久割让,现在都回归了再讨论这些还有意义么,难道英国还能抢回去不成?
用户10xxx22
实力才是真实才是真理,有实力大英帝国也是中国一个省
一一
对付毒贩子,任何条约都可作废。
用户10xxx38
哪天咱们也去欧洲占领英国鬼子的地盘来玩玩!
00后
就是永久割让又怎样?伟人说,不承认前庭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看着吧,先远后近……会如了愿!)
南江沙洲客
管你什么狗屁条约!当年是当年,当年你是强盗到我家欺男霸女,我毫无还手之力,不给也得给,现在我有能力了,原本是我的东西,你说我已送你,可我不承认你就必须返还,否则一锤子砸你个稀巴烂!
流氓的低音鼓
纠正一下自媒体。收回香港跟南京条约没太大关系,有关系的话也是英国签了字。我们跟英国谈收回的事。邓公一开始就没扯99年一百年的事。就是跟英国谈收回。那时候部队已经放在香港边上了。不谈就武力收回。这就是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当时也有个历史机遇,中美蜜月期。中国跟西方关系普遍好。当时也是殖民地普遍建国的日期,整个历史氛围都对我们有利。当然香港回归对英国的国际声誉也有好处。
随缘
新中国不承认历史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别再说英国法理上怎么着了,一副奴才像。现在如果有人打作者一顿,说要杀了作者,然后逼着作者签一个欠条,作者在法理上就欠别人的钱吗?强迫情况下签订的有啥法理?
覃军
不评论,我的东西被抢了,现在拿(就算是抢)回来了,还讲什么合理性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