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以下简称《诗与它的山河》)是一部极具开创性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在这本700余页的专著中,作者萧驰先生将现地考察研究方法与案头文献相结合,采用跨学科的多元视角,对中国古典文学最为重要的山水书写进行挖掘,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古诗文中山水美学的逐渐生成,力图凸显中国山水画异彩纷呈的独特文化景观,相信对中国艺术史、人文地理学、生态诗学乃至跨文化的风景比较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获益。
聚焦中古诗文的山水美学
萧驰是萧乾之子,成长于北京,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修读古代文论。1987年负笈北美,先后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修读比较文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诗学,长期致力于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与传承。
《诗与它的山河》是作者年入花甲后,将学术关注的目光从“思想的天空”下落到产生中国诗的山河大地,历时七载创作而成的结晶,于2018年出版。全书分十章涵盖了中古时期书写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十五位诗人: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何逊、阴铿、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元结、柳宗元、韩愈和白居易。而从时间跨度来看,上限是谢灵运被贬至永嘉的永初三年(422年),下限是白居易于洛阳谢世的会昌六年(846年),前后共420多年。在作者看来,就书写山水自然而言,这应当是中国诗人最具创作力的时期。
人类所有民族都会对大自然,对山野林泉有某种神往和眷恋,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许多具体的习俗,却可能迥异。究其原因,各自生存地貌环境之不同、生活和生产方式之不同,以及各自语言语义系统中累世形成的美感经验之不同,都是根源所在。“常被视为本然的山水美感,其实是一种值得悉心研究的文化。”最早认识自然山水之审美价值并持续进行书写,是中国文学令人瞩目的一项成就。关于自然风景的许多话语和观念都率先在诗中出现,而后衍至绘画,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表达,《诗与它的山河》的宗旨,即是经由中国中古诗歌文本,考察中国诗人在持续正面书写山水自然的头四百年之中,中华民族特有的关于大自然的美感的生长,通过十五位诗人与中国山水的互动,讲述一个山水景观美感如何一点点形成的故事,同时也为早期山水画和园林景观观念的形成提供线索。
《诗与它的山河》主题词是“诗人山水书写”而非常见的“山水诗”,是因为作者认为后者涵盖范围过于狭窄。“山水诗”一词,最早见于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谢公才廓落……泄为山水诗”一段,然而在古代重要的论诗著作中,却几乎没有“山水诗”这样一种题材或文类的归类,这与古人画论中屡屡以“山水”为类为题的情形很不相同。由此作者推断,所谓“山水诗”这一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学术根据画史中山水终成大宗而做的推演。
萧驰先生既是“中国抒情传统”这一重要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始终与这个思潮保持着矜持而自由的关系;既具备深厚的中国古典美学修养,又具有广博的西方美学和比较文学知识。复杂丰富的学术背景,使其具备了参与者、游移者、反思者等多重身份,这也使得《诗与它的山河》与常见的中国古典诗歌普及读物有很大区别。该书不是在讲述中国的山水诗,而是在讲述中国山水诗中的山河,讲述诗歌文本背后中国古典文学山水美感话语形构中的纷杂和繁复状态。得益于海外学术背景,作者在分析中国传统诗学时,时常把中国山水书写、中古山水美感这一主题放置在全球视野中探讨,并屡屡引用西方文论乃至音乐、建筑、绘画的美学理论等,如果没有相应的古典知识和审美经验,阅读此书极有可能茫茫然如堕云雾。此外,本书语言古雅优美,这也提高了此书的阅读门槛。
回到诗文作者叙述之现场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采用了“现地研究法”,在撰写本书的七年里,作者前后十次前往谢灵运、王维、李白、柳宗元、白居易等重要中古诗人曾经游历、行旅、居住过的实地山岭和江流之中做现地考察。因此,《诗与它的山河》不仅是关于诗歌文本的知识考古,更是对中国山水永恒现场的追溯与考掘。
现地研究这一方法由日本汉学界首先做起,岛根大学户崎哲彦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曾在考察了湖南永州及道县的柳宗元和元结所书写的山水之后,出版了900多页的皇皇巨著《柳宗元山水游记考》。高雄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则在20世纪末在奉节考察之后出版了《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一书,继而又在陕西和山西等地的考察之后出版了《唐诗现地研究》。在简锦松教授看来,现地研究是“从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资料观,转向现地主义中国文学研究的资料观”。由此,研究者得以“回到诗文作者所叙述之现场,考察当地之实际情况,再据以对照诗文之内容,借此寻获真实之答案”。
原本是案头作业的古典文学研究增加了户外考察,研究者需付出几倍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对古人所面对的实地山水和话语山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透过多年的地貌变迁去重构当年的山水环境。沧海桑田,云水千年,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千百年来出现于诗歌里的地点,大多已被时间大手抹去了清晰轮廓,隐匿于远离尘嚣的僻静角落。在中国诗人的风景概念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山与水。山体的变化一般较小,水体的改变则相当普遍,如大量湖泊的消失、河道的变迁、长江入海口的变化等。作者需反复查证,才可能去重构当初诗人身处的实地山水。进行这番现地考察时,萧驰先生已年近古稀,寻路之旅之种种辛劳,自不待言。
“现地考察”只是开始,后续工作还是要回到案头。经由文献考证辅以现地研究,比对诗人在将自然山水加工为诗家山水时采取的视角和取舍,作者提出了不少相当精彩且翔实可信的观点:通过对辋川谷内外进行现地考察,对简锦松所论“谷外说”提出有理有据的合理质疑;对谢灵运诗中尚未辨认、多存争议的位置或景观如上戍石鼓山、斤竹涧、白岸亭等进行文学地理之考辨,通过考察引发诗人山水美感的实地山水,最终确认谢灵运的山水书写确是一种非虚构意义上的“地方之诗”;实地考察天门山并乘船往返两山之间的楚江后,发现矮小的天门山与浩荡的长江远达不到“天门中断楚江开”的比例,那雄浑壮丽的山水图景,其实源自李白雄奇瑰丽的想象力,因此阅读李白驱山走海的山水书写,绝不能局限于自身经验以及宇文所安所谓“中国文学传统之非虚构”……这些基于现地研究的论述既有助于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悬案,也说明了在地的山水对走入古人诗境之不可或缺。当然,山水诗、山水书写终究不等同于山水本身,它是一种话语运作,故而现地考察于此书也只是一种辅助方法和内容,在各章中根据需要比重亦不同,如讨论韦应物一章则完全未涉及现地考察。
山河依旧,诗词隽永。经由回到诗文作者叙述之现场,作者不仅看到了实地山水与话语山水间的重叠,更看清了实地山水与话语山水的连接与分野。当我们像作者那样,踏上或目睹古代诗人昔日踏足、吟咏过的风景,那些曾经阅读过的山水诗必将与眼前的自然景观幻化融合,在心中叠加出具有特殊意义的独特景观和文化记忆。
当下“山水”与千年“山河”
你可曾想过,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家国与自然有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思接千古,山河同频。正是中华大地上的山河将今人与古人相勾连,让我们得以叩听诗与华夏山河的隆隆共鸣。
《诗与它的山河》虽以讨论中古诗人的山水美感为题旨,却以“山河”作书名,其中意蕴,作者在书中第六章讨论杜甫夔州诗中的“山河”与“山水”时进行了说明。“山水”和“山河”两个词语,差之一字,涵义却大不相同。萧驰先生认为,“山水”主要用于一地景物之游赏,“山水”之“水”,为一人当下所见之水,而“山河”之“河”如黄河、长江,却流经千里,贯烁古今,直指华夏民族的广袤生存空间和悠久历史,被赋予了民族文化血脉的意义。在杜甫之前,山水书写主要基于三类需要:一类是“游览”之作,以谢灵运的永嘉诗作、鲍照的庐山诗,以及孟浩然和李白的许多作品为代表;第二类是为创造出一个独立于仕宦世界之外,标榜隐逸的价值世界——“别异乡”,可以王维的辋川诗作为代表;第三类则是与宦游相关的去离、羁旅中对自传性环境的书写,鲍照、何逊的大量山水书写皆可归为此一范畴。这三类山水书写,山水皆为与诗人个体生命轨迹相关的一时一地。而杜甫的夔州诗,则将客观存在的“山水”推广到了与永久的时间和广阔的华夏大地相系的“山河”,暗示出这片土地承载着的兴衰合离之历史,使“山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国”的象征。
山水是诗兴生发的唯一现存尺度,“一方山水一经吟咏,即如典籍一样具有了传承斯文的意义,后代即可借这一处‘山水’与前人‘古今相接’”。由此,萧驰先生的人文关怀很自然地落在对华夏山河的保护上。他借这一研究,提倡另一种环保意识,即注意保护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环境。因为中华山河不仅是古人吟咏的对象,亦是承载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广阔语境,一旦被横加破坏便再难复现。在导论中,他不无遗憾地提到,在谢灵运、王维生活或流连的浙中剡水和关中辋川,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说,某些村庄、山岩甚至以此命名,如嵊州谢岩石的康乐弹石、蓝田辋川的望亲坡等,然而这些宝贵的遗存已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乃至世界山水艺文的真正摇篮”、李白的梦土、王子猷雪夜访戴时舟行所经的河流剡溪,因两岸国道和高速公路的修建而面目全非,失去了过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其上,若云蒸霞蔚”的秀美模样;昔日王维别业所在地蓝田辋川谷,如今也因一条高速公路大桥纵贯而过,令人即使置身其中,也很难再去想象王维的诗境。由诗家山水的天空下落到祖国山河大地,萧驰先生以此书呼喊出了护持华夏文化山河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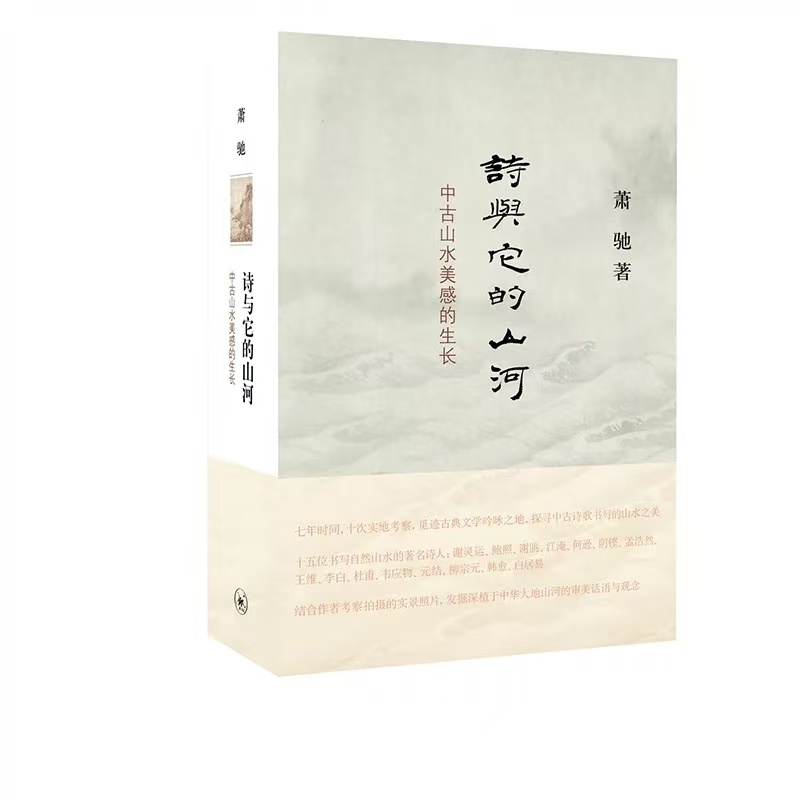
萧驰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