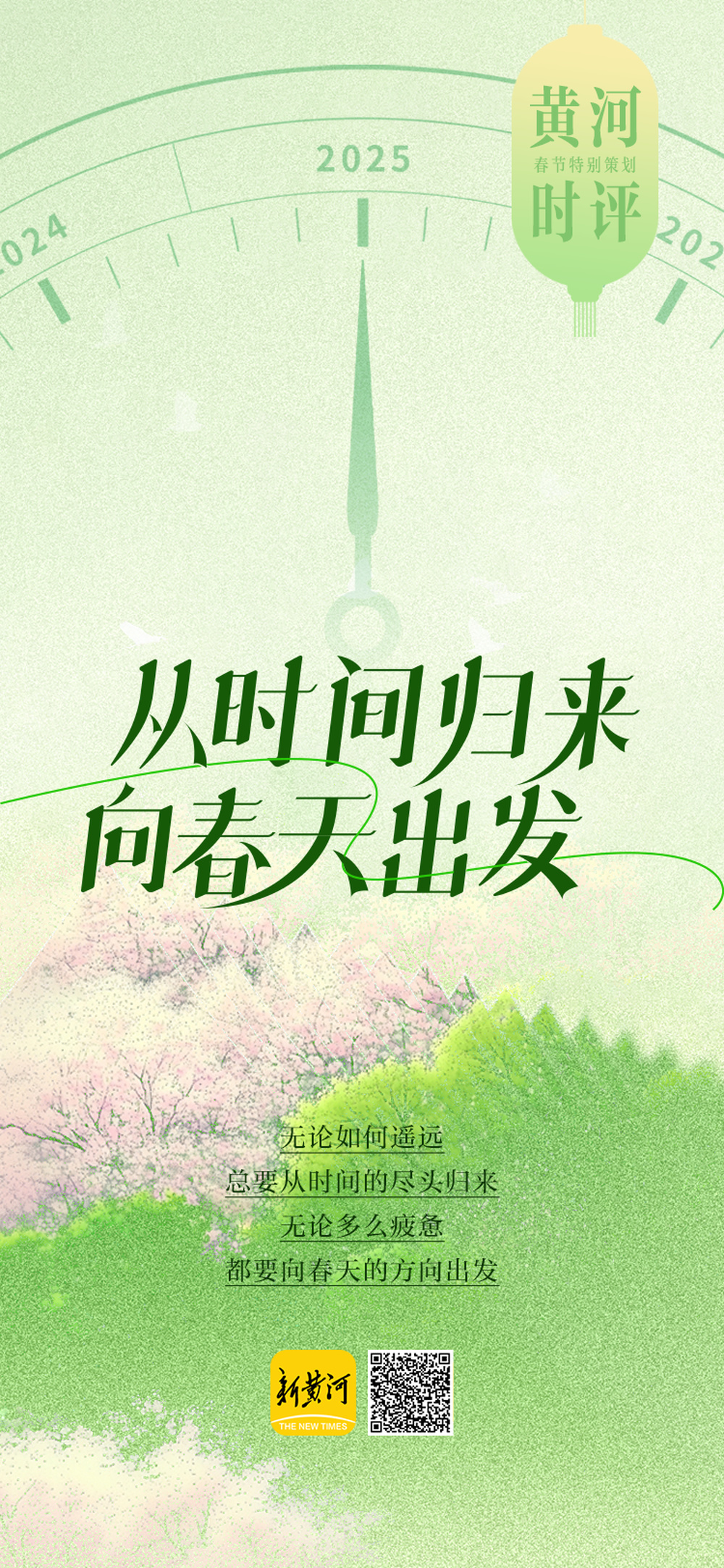
如果你来自外太空,你肯定无法理解一到这个时刻,在亚洲东部、太平洋以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折腾啥:
到处都是如过江之鲫般的人们迁徙回故地,繁华的城市迅速清冷,清冷的乡镇又瞬间丰满,人们如着魔一般,能抢票的抢票,能开车的开车,再不济还可以在雪夜中来一场摩托车的千里奔袭;
而路边卖煎饼馃子的大姨和她的小三轮好几天前就踪影难寻,待人潮恢复汹涌时又悄然出现;
即使是坚持营业的商超综合体,收银员也早早摆出“欢迎下次惠顾”的牌子,光亮的大楼和一个港腔男人唱的“恭喜发财”随即淹没在夜色里;
平常随时可以吃到的菜肴今天也都端出来它不可一世的高贵——饺子不再是饺子,而是包含硬币的希望。
一些暴躁的人们这几天情绪也颇为稳定,不小心踩ta一脚回以的也大多是“大过年的”“算了算了”。树枝上聒噪的鸟儿似乎都比平常体贴,它们在轻唱:回家,回家。

图源新华社
毕竟,农历新年,是中国人与自己最大的和解。
因为,它是公平的,它并不为自己的到来而挑三拣四。“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即便在晦暗的个体命运里,它也让一些灰头土脸的中国人获得短暂的松弛与充盈——杨白劳不也得在除夕的晚上逃回来给美丽的喜儿扎上二尺红头绳吗?
其实,物质丰裕、身处后现代的我们之所以还能被春节吸引,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不被闹钟捆绑的自然醒、不为体型焦虑所释放的胃口、亲人之间的坦诚直言,毕竟,春节不只是民族文化的符号,内在肌理是关于人的狂欢,人的自由,人的叙事。
所以,“人味”就是年味。当我们在抱怨年味淡了的时候,真正在变化的或许是我们自己:是一到“牛马生物钟”就再也睡不着的觉;想到节后他人对自己的“体型审视”就不自觉地放下筷子;在亲人闲谈中的“比较”不经意间戳痛自己职场上的狼狈与伤疤、催婚催育催二胎;还有已被屏蔽的工作群里时隐时现老板的信息……春节没有变,是我们自己在默默收缩。
当我们在呼吁年轻人克服审美疲劳和情感游离以守护年味时,倒不如说是不是高速行进的城市留给个体闪展腾挪的空间在变少了呢?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年,申遗文本指出:“‘春节’项目由全体中国人共享,在全国广泛实践。”这种实践其实也可以解读为中国人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做出的一种哲学思考:如何以真实的自我体感为圆心重建一种与社会的关系,哪怕它只在短短的几天假期中。
当然,从“全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春节,还能让我们超越民俗范畴而看到更广远的价值谱系:那些可以放声的大笑,那些没有束缚的自由,那些浓浓的团聚和骨肉间的依偎,不仅是春节需要的,而是生而为人之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它,不只是作为“龙的传人”的需要,而是身处现代文明的“人”的需要。
从这点上讲,不只是要把纯粹的年味留给人,而是应该把纯粹的人留在年味里。

图源新华社
所以,只有守护好春节所蕴含的小确幸,把对人的尊重投入日常生活里,这一声声“过年好”才有它持久不息的穿透力。
各位,过年好!
评论员:李明美编:杨壹晴编辑:韩璐莹校对:刘恬校对:汤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