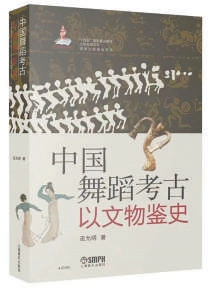
《中国舞蹈考古·以文物鉴史》巫允明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我喜欢读史,也喜欢写点什么,当出于专业的需求,在中国舞蹈史学的殿堂中遨游,以至自己应约写作《中国舞蹈》与《浙江舞蹈史》等书,欲四处寻觅现存的可证史料时,常会遗憾地发现,有的佐证被熙熙世流分解离析得只是残骸片断,而无法与整个人文大背景相互浸润;或只是作者一种思维的假代性自洽,读者仍无法获得真正的历史判断。这使我遗憾地感觉到,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种现象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结性反应,会如同涟漪般地出现在国内外有关中国舞史的研究中,同样的遗憾也多少出现在自己的写作中。
历史应该告诉人们的是明确的事实与严谨的真相。尽管史学研究的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最可靠的实证应是以不同形式存留至今、于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物体或物品——文物。文物本身或其物理层面,呈现给人类,作为视觉基础的图像。可惜的是悠长岁月的尘封与自然条件的侵蚀,让舞蹈文物的存在和面世变得那么不容易。但希望总存在于人们的期待中。
透过文物表象感悟舞蹈形象内涵
近日,被誉为“中国舞蹈书籍出版界第一编辑”的黄惠民先生向我推荐巫允明女士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新作《中国舞蹈考古·以文物鉴史》,给了我莫大的欣喜。由于我正应一家出版社之约笔耕一部地方舞蹈史,该书的“以文物鉴史”令我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
《中国舞蹈考古·以文物鉴史》装帧精美,结构依历史线脉的文物史料次递展开,眉目分明,内容丰硕,文字深入浅出,图录质感清晰。全书共分“新石器时期的‘乐’与‘舞’”“先秦的‘乐’与‘舞’”“汉代浓墨重彩的‘乐舞百戏’”“三国至南北朝的乐舞遗存”“隋、唐、五代辉煌的‘乐舞’”“宋、辽、金、西夏的舞蹈形象”“元、明、清舞蹈遗痕”等共七章。研究视角与方法积极敞开,在多元学科交叉互通的学术命题中,立足于舞蹈学对古代舞蹈文物主体间的把握,导引读者既要从整体出发宏观把握,又要微观进入细致品鉴。如对敦煌石窟壁画,均采用“全图”、局部“乐舞图”和“乐舞线描图”三部分,以“整体——局部——整体”的呈示方式,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乐舞”在全图中的位置、大小及清晰的舞蹈姿态,从而透过舞蹈文物的表象,去感悟舞蹈形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存在价值。全书在参考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图像学、人类学、艺术史学等学科理论时,匠心独到,鞭辟入里地拓展了该著作的学术话语。
汲取考古界最新研究信息
其次,该书在尊重舞蹈界前辈长年的中国舞蹈史积累与学术成果的同时,非常注意汲取考古界的最新研究信息,尽力开掘历史上更多的舞蹈本貌。该书引用的四百余幅文物图片,不仅收入了以往一些具有重大舞蹈历史文化价值的经典性文物资料,还补入了不少20世纪90年代前后及近期出土的舞蹈文物图录。作者据图而论时,并未沉溺于繁复沉闷的诉说,而是以理性探索精神的追问,将研究成果清新晓畅地分享给了读者。对待学界至今尚有争议的史料,作者除在书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外,亦诸说并列,以引导读者在比较中思考。
比如,当代几乎所有中国舞蹈史书籍都会提到的1973年于青海省大通县出土的“五人连手舞蹈纹彩陶盆”,许多年来众多学者围绕大通县彩陶盆文化内涵的见解并不一致。“概括起来大概有娱乐说、图腾说、祭祀说、庆功说、繁殖说、巫盆说等。同时,对作舞者头部的发饰也有脑后饰‘戴胜’说、女子‘发辫’说等。此外,对舞人身前突出物有利于狩猎的‘尾饰’说、作舞女子飘动的‘服饰’说等。”对此,作者认为研究和探讨任何出土器物与人类活动,都不应是孤立的审察,而是要与研究对象的历史阶段、生态环境等去密切关联。作者参照考古界对“五人连手舞蹈纹彩陶盆”制造时期的考证,认为当时生活在青海省大通县一带的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并部分具有农耕生产经验。祈求人丁与作物的繁衍已成为人们的第一需求,“因此祭祀器皿内侧所绘舞人身体前短物为男根的特别体现,更具说服力”。由于该彩陶盆舞人图案较为写实,舞蹈纹彩陶盆上的舞蹈形象“应理解为当地初民在祭祀过程中通过男子作舞娱神,以达到祈求人、畜、作物丰收目的的一种记录”。此外,作者还有一种很具特色的书写方式,即按照考古资料要求,书中所有文物图像均有其所在朝代舞蹈文化有关介绍与论述,所提及的文物出土处均标注了当今的准确地址与可供查阅的书籍及其篇章,这就为读者日后资料检索与进一步依此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呈现舞界多个首次表述
此外,我们亦可在该书中见到一些对史料的补证与通说的思辨,体现出作者于主流文化印象下,发挥自主人格、主体意识与独立学识的可贵建树。如在第三章“汉代浓墨重彩的‘乐舞百戏’”中,关于2007年出土于山东东平的汉墓“乐舞”壁画;2011年发掘和清理江西省南昌西汉第一代海昏侯、汉武帝之孙刘贺的墓地中,所出土双面“舞人玉佩”透雕的情况;于第四章“三国至南北朝的乐舞遗存”间,关于1977年甘肃省发掘的丁家闸5号晋墓《燕居行乐图》的介绍;第五章“隋、唐、五代辉煌的‘乐舞’”就1999年7月科学发掘山西省太原市虞弘墓石椁九块雕绘图的介绍,及椁内东壁南部《乐舞图》的剖析;对1992年陕西咸阳后周冯晖墓甬道东西两壁“乐舞”彩绘浮雕的演绎……均为舞界的首次表述。
作者研究意识的勃发还体现在个案探究时的学术思考。如对太原市虞弘墓石椁东壁南部《乐舞图》的研究,作者认为其“生动展示了千余年前旅居中原的粟特首领,举行集会时的宴乐场面和西域‘胡舞’”。对1992年陕西咸阳出土后周时期冯晖墓甬道东西两壁“乐舞”彩绘浮雕的剖析,不仅使读者了解到那个时期东西方文化艺术交往的史实,也在图文并茂中呈示了“乐舞”中的“执杖者”,为出现在后代戏曲中的“参军色”提供了前期的形象依据。作者在考究1975年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木梳和木篦上的宴饮乐舞时,引证并在舞界首肯了考古专家的观点:“虽出自秦墓,却为战国时期所制作。”这就将当代中国有的舞蹈(乐舞)等书籍中误认为木梳和木篦上的宴饮乐舞是秦代文物的年代前推了数百年。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吴晓邦和欧阳予倩两位前辈出任组长和艺术指导的“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在京成立,由此开启了“中国舞蹈史研究”这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建设工程。自此以后“江山代有才人出”,多有专家学者陆续出版了关于中国舞蹈史研究的专著、论文、教材,《中国舞蹈考古·以文物鉴史》就是其中非常优秀的一例。倘若有更多仁人志士如作者巫允明女士一样,兀兀穷年重视舞蹈的考古,化干涸的文物记忆为鲜活的历史长篇,有更多的同道者一起把全国范围内非遗传统舞蹈的史料与地方舞蹈史的编纂工作开展起来,那么中国舞蹈史在奠基人基石上的当代补正与更新将会到来,中国舞蹈史学体系大厦亦将于不久的将来落成。
(作者为浙江省文化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