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即便随着教育发展,接受教育的年限比以往增长了许多,占据更多时间的还是工作。工作和现代人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的时间安排基本上都围绕着工作这件事。无论是过节还是日常休闲都需要依靠暂时脱离工作才能实现:假期、下班或请假。
或许我们曾想象过遥远的古人,他们不需要打卡,不需要通勤,似乎比今天的上班人轻松多了。对古人的这种浪漫想象也曾出现在种种文本和影视剧改编之中。当然,在早期的初民社会,人类并未发展出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依靠简单的劳作谋生。
将时间拉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谓“工作”指的都是狩猎和采集;直到4.5万年前,少数专门化工种才开始出现”,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大分工也不过数百年。为什么人类就无法停止工作?或者说,人类最初是怎样进入劳作的?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以下简称《理解工作》)一书的相关章节,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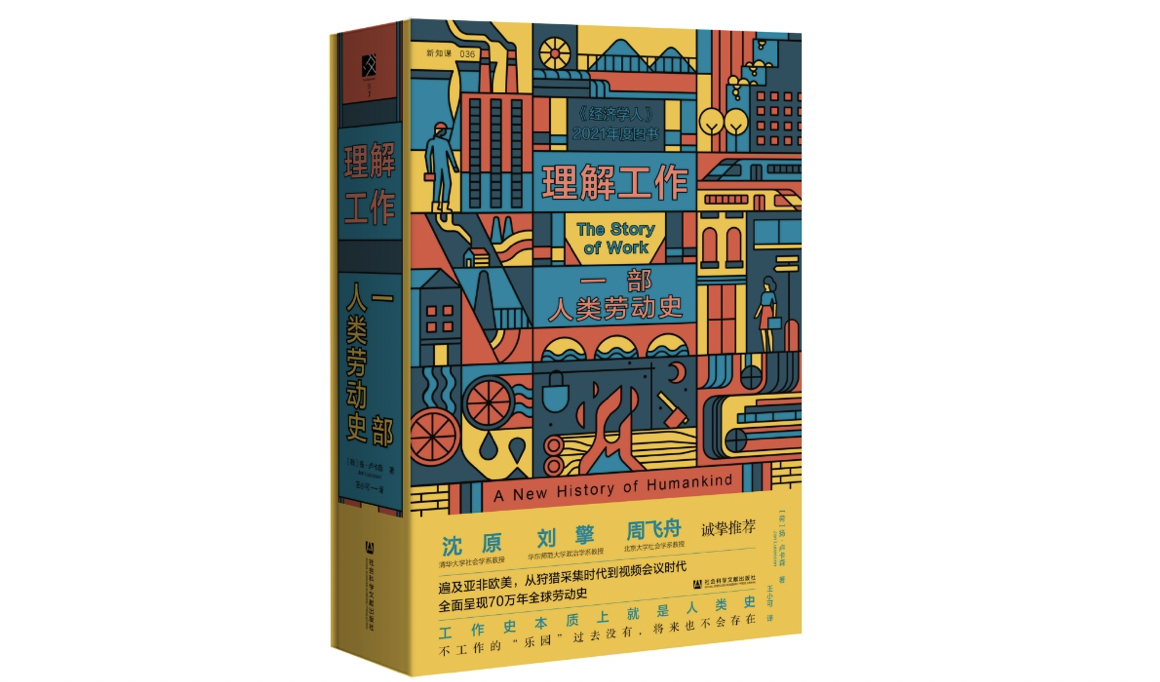
《理解工作:一部人类劳动史》,[荷]扬·卢卡森著,王小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寸,2024年11月。
1.“工作”中的动物与人类
正在工作的现代人类,和正在工作的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或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动物和机器差不多,离开人类就无法工作。如果没有人类的强制训练或命令,小熊不会跳舞,毛驴不会拉车,利比扎马也不会表演。
然而,多种因素表明,与机器之运转相比,动物(尤其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劳作与人类之工作具有更高的相似度。因此,理应从灵长类动物劳作的基本原理谈起;这也势必能促进人类对于自身工作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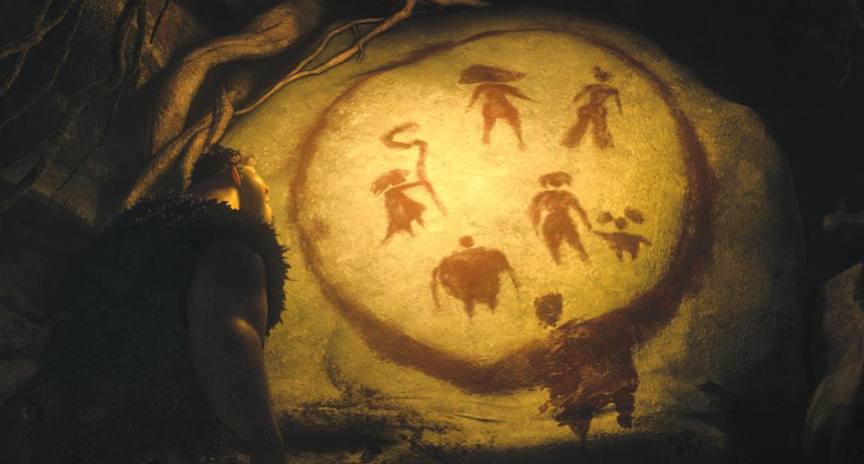
《疯狂原始人》(TheCroods,2013)画面。
第一,在大约1.2万年前,即新石器革命之前,人类唯一的活动是通过狩猎和采集获取日常食物,大多数动物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是工作,就必须得承认动物的同类活动也是工作——不受人类驱使的独立工作。第二,在食物、住所、医疗方面,奴隶得到的补偿与耕畜的遭遇无异,工作条件也和马的差不多。以上两点足以说明,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动物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共性。因此,下文将会对动物(尤其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日常活动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借以了解早期人类工作的起源和特点。
对于人类来说,觅食不仅是最必要的工作,也是每个个体从独立生活开始,就必须从事的最基本工作。但对于灵长类动物而言,觅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个体行为;事实上,其觅食行为意味着劳动分工。关于动物界的劳动分工,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蜜蜂——蜂王、雄蜂和工蜂在蜂群中共同生活,各司其职。
鉴于蜜蜂与人类之间的进化差距过大,深究这个例子并无价值;但是对于原始人类的研究,我们可以参考动物行为学和社会生物学这两个学科。这两个学科对大型猿类——尤其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社会行为展开了研究;而在1000万年至700万年前,这两种猿类曾与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
既然如此,关于劳动分工,特别是成年灵长类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任务分配,我们有哪些了解呢?首先,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雄性和雌性会承担不同的任务,雌性专门负责抚育后代,因为只有雌性能够哺乳。关键的一点是,母亲之外的个体如果与幼崽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血缘关系,即使母亲将照顾幼崽的任务托付给它们,它们也不会接受。换言之,在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中,照料幼崽是雌性的特有任务,族群其他成员并不会因为雌性承担该任务,就自觉承担具有互惠性质的其他任务,如主动帮助母亲采集食物。
但少数几种灵长类动物的情况稍微复杂,它们在劳动分工上,特别是在狩猎方面,确实存在互惠性质。对于大型猿类来说,植物类食物的采集大体相对简单,也是每个成员都要负责的固定任务;至于狩猎这项任务,耗时费力,且收获与风险皆不可预测。
一般来说,狩猎者都是成年雄性(雄性猿类的体格通常比雌性更大、更强壮),并由最熟练、最强壮的成员带领。在高效合作,且运气较好的情况下,它们能够不时通过捕猎获取珍贵的肉类。这些肉往往是整块的,量大且易腐烂,狩猎者自己吃不完——因此在黑猩猩和卷尾猴中,狩猎者一旦获得肉食,常会基于互惠原则,自愿将其分给族群内的其他成员。谁能得到多少可能是基于自己先前分发食物时的慷慨程度,又或与繁殖和情感上的付出相关(比如猴子之间互抓跳蚤)。这些幸运的受赠者并不一定是狩猎者的近亲(这与鸟类不同,鸟类在繁殖季节会互相喂食)。

《公元前一百万年》(OneMillionYearsBC,1966)剧照。
2.合作和分工是“工作”的基础
深入研究猿类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后,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deWaal)指出,进行狩猎的杂食性非人属灵长类动物,与巴拉圭、南非以及巴西的人类狩猎民族有着相似之处。对于后者的社会行为,他赞成美国人类学家兼灵长类动物学家凯瑟琳·米尔顿(KatharineMilton)的说法:
“在我们现代人类的经济体系中,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尽力获取和控制尽可能多的可用资源;狩猎采集者的原始经济体系则不同,它建立在一系列关于合作和共享的高度形式化的期望之上。……例如,在有幸猎得大型猎物之后,没有哪个狩猎者会认为,所有的食物都应只属于他自己,或只属于他的直系亲属。”
许多关于狩猎采集者的专著中,都阐明了这样一个原则:狩猎者及其亲属不能独享肉食,而必须让营地中的所有人共享。
萨拉·布拉弗·赫尔迪(SarahBlafferHrdy)的开创性著作《母亲及他人》(MotherandOthers,2009)对我们颇有帮助。对于人类及非人属灵长类动物中雌性行为的进化基础,该书使我们能从更加新颖的角度来理解。她指出,在进化后期,早于现代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另一种合作形式——母亲可以将自己那发育缓慢的珍贵幼崽托付给他人,后者即所谓的异亲(alloparent,包含父亲在内)。

《人类发现》(HumanDiscoveries,2019)画面。
据作者所述,这一形式可能在180万年到150万年前就已出现。与其他大型猿类相比,人类的出生率更高,生殖寿命更长,且断奶期更短,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人类的后代能够与更多兄弟姐妹一起成长,进而提高了他们的社交和认知能力。再者,用火加热和烹调食物,也使得人类能够进行体前或体外消化,促进营养吸收,改善身体健康。
和其他所有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无疑也具有竞争和攻击行为,但并非只有这一面。在物种的成功进化中,同样重要的还有人类的合作能力。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灵长类动物易受掠食者攻击,人类亦如此:“安全是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因……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彼此而生存。任何关于人类社会的讨论都应以这一现实为出发点,而非参照数百年前的遐想,幻想我们的祖先像鸟儿一样自由,没有任何社交义务。”
在人类工作的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互惠的基本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担育儿任务,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的特性。这一说法与上面所提的定义问题相符。假如在智人出现之前,除了觅食活动可定义为“真正的”工作外,相互间的情感和繁殖互动也是人类行为的固定元素,但这样一来,“真正的”工作和社交义务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因此,克里斯·蒂利和查尔斯·蒂利在广义上对“工作”进行了界定,这就整个世界史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个体及其后代的生存能力有两大基础:一是觅食方面长期依附于他者,二是知识的获取。广义上的长期知识转移决定了觅食者的生存机会。
人类这个物种不仅可以通过竞争来理解,还尤其能够通过合作这一维度来理解。此外,人类女性无须单独照顾孩子,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祖母,会一同承担育儿任务。这为我们研究狩猎采集者的工作历史提供了两个重要起点;它或许还是我们后续研究的基础:除服从外,合作更为重要。总而言之,现代人类至少在其存在的前95%的时间里所进行的工作,一直都呈现为某种“互惠利他主义”的形式。
3.“工作”中的狩猎采集者
新石器时代之前,人类的工作是如何发展的?

7万年前现代狩猎采集者的迁徙轨迹。图片为《理解工作》插图。
如今,大多数人很难想象狩猎和采集食物具体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多少时间,由谁来做,以及如何组织。对于这些涉及所有狩猎采集者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原因很简单,人类生存的区域如此之多,且属于不同的气候带——从海岸到高山,从沙漠到雨林。在全球的不同生态气候区,分布和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工作;只有发生过重大基因突变,并分化出新种属的动物,才能承担这样的多元化工作。随着大脑机能,以及语言交流能力的进化,人类承担上述工作便成为可能。
智人出现后,人类便再未进化出新的分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智人迁移到更偏北的地区后,受气候影响,肤色和身体比例变得更加多样化;但除此以外,在其历史上,他们并没有发生更显著的进步。
描述和理解早期现代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的工作生活并非易事,原因之一是考古学只能提供部分证据。幸而这些证据的可信度日益增加。针对这个问题,寻找类似动物进行平行比较并无帮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要依赖于过去几百年对近代和现存的狩猎采集者的记述。这样做的问题是,近代和现存的狩猎采集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先进”生存手段的影响,我们无法规避这种影响,在“纯粹”状态下研究这些群体。

《疯狂原始人》(TheCroods2013)画面。
一直到1.2万年前(公元前10000年),所有人类都以觅食为生,而在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这种生活模式已经扩散到澳大利亚、北美大部分地区、东北亚,以及南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据乐观统计,21世纪初所有的游牧民族、驯鹿牧民、渔民和开发临时性农田(刀耕火种)的农民加起来有2.5亿。这相当于世界人口的4%,而其中的核心群体是“已在近一两代人中摒弃了原始觅食方式的,数以十万计的族裔”。在这些核心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大概几万人)保持着大体上直接起源于古代狩猎采集者的传统,其余的则是农民或牧民的后代,他们抛弃农牧重新转向了原始觅食方式,正如南美洲人在躲避西班牙人入侵时所做的那样。
在《剑桥百科全书——狩猎采集者》(CambridgeEncyclopediaofHuntersandGatherers,CEHG,2004)中,则更为详细地研究了人数不多的八个近代狩猎采集者族群。根据历史学,特别是考古学证据,这一研究假定他们的祖先一直遵循这种生活模式。但在这部鸿篇巨制的百科全书中,我们无法确定其他几十个近代或现存的,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民族是否以同样的模式生活。不过可以证明的是,或者说确有可能的是,这些民族早期依靠农耕或养牛为生,比如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米克亚人(Mikea),以及目前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狩猎采集民族。
数千年来,上述八个族群的一代代族裔始终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是“真正的”狩猎采集民族。
但即便如此,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也必须保持谨慎。这些族群也经历了显著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他们不仅与邻近的农民有往来,最近还与工业国家的代表,如石油钻探公司产生了接触。以上内容虽有存疑之处,但我们仍会试图通过类比来重现史前狩猎采集者的工作及相关社会关系。
4.想象初民的“工作”场景:一个实例
平等、共享、慷慨、互惠之原则主要是针对游群内部成员,并非任意施行;他们还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边界防护措施。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包括早期智人在内的古人类,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和现存的狩猎采集者都是如此。狩猎采集者获取土地和资源的方式则存在一些差异:“共享不是某一进化阶段或生存模式的产物,而是决策的结果。共享资源有利也有弊,因此,狩猎采集者决定分享食物或允许外人进入其领地时,需要权衡利弊。”
基于上述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的特征,下面将探讨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实际工作。
虽然不同生态气候区的狩猎采集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也有一些标志性的共通模式,最显著的可能是捕猎大型猎物时的合作需求。在学会使用猎犬之前,人类在狩猎中完全依靠自身的奔跑能力。

《上帝也疯狂》(TheGodsMustBeCrazy,1980)剧照。
南非人类学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Liebenberg)在博茨瓦纳与“桑人”(San,非洲南部地区原住民)一起狩猎时发现,得益于臀肌和排汗能力,人类善于长跑,这有利于他们的狩猎活动。利本伯格加入的狩猎队中,猎人们已经年近40,但他们仍然能够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42℃)追着羚羊跑23—40公里,一直跑到羚羊筋疲力尽,被人捕获为止。猎人们平均每小时能跑4—6.5公里,但有记录显示,有人曾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跑了35公里。如前所述,这样的狩猎队由很多人组成,因此合作至关重要。
举例来说,北美的游牧部落会使用“围堵法”来猎杀野牛,这种做法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深入了解尼西塔皮人(Nitsitapii,或称黑脚印第安人,以下简称“黑脚人”)之后,就能得知此种“围猎”包含哪些具体做法。黑脚人进入北美大平原生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每个族群有80—160人,居住在10—20个圆锥形帐篷里,每个帐篷里都住着两个健壮的男人、两个女人,以及4个孩子或老人。

《史前一万年》(10000BC,2008)剧照。
春季时,他们会建起野牛栏,让年轻人“哞哞”地模仿野牛叫,把牛群引到围栏里。狩猎主力则躲在围栏附近的岩石或灌木丛后,一旦牛群靠近围栏,整个游群就会跳起来,挥舞长袍,大声喊叫,吓得牛群狂奔涌进围栏里躲避。而在围栏里,早已有人等待着用棍棒和弓箭杀死这几十上百头野牛。随后,6名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会组成一个团队,负责处理这些野牛的尸体。他们会趁新鲜食用野牛的胃容物和内脏,并把大部分瘦肉晒成薄条状的肉干,再混入脂肪和干浆果,将其制成干肉饼,然后装进皮袋储存起来。这些干肉饼可供族群食用到第二年的春季大型狩猎期,此外有记录显示,他们也会将其用于对外交易。
几百年前,这些野牛猎人还未开始使用马匹,因此活动半径必然很小。春季大型狩猎期之后,数千人会在初夏时节聚居,到了秋季则分散到隐蔽的溪谷中。制作干肉饼时用到的浆果由妇女采集,与黑脚人的狩猎活动相比,这属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植物性食物的采集;除了采集浆果,妇女还需要种植克美莲球茎和草原萝卜。此外,妇女不仅要搭建帐篷、做饭、制衣,还要为每个人提供庇护,以及承担一项重点工作:主持仪式。
合作是关键要素,这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活动,尤其是狩猎。若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狩猎采集者,就必须学会合作,而且要学习很长一段时间。
原文作者/[荷]扬·卢卡森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