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几个月,比尔·盖茨就满70岁了。
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顶着「世界首富」的名头游走各国,说服大富豪们捐赠身家做公益和慈善。近几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能自行运转,比尔·盖茨本人有了更多时间投入个人生活中——不管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案,还是如今甜甜蜜蜜的黄昏恋,他一直身处众人目光之下,毕竟,他所创建的微软仍是全球市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企业之一。
有人说,人老了的标志就是喜欢回忆过去,吹嘘过往的成就。比尔·盖茨想打破这一说法,2月初,其首部自传中英文版全球同步上市,在这本书中,他事无巨细地回忆童年及少年时期的激情与志向,真挚而温情地描绘亲人和挚友的过往,我们对他的事业和财富有所耳闻,但很少有人拨开时光的迷雾,回看他的家庭环境和成长氛围。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从他的自传《源代码》中摘取部分内容,和你一起观察年仅5岁的比尔·盖茨是怎么玩、怎么学的,从中你能看到两位了不起的女性如何言传身教,影响了他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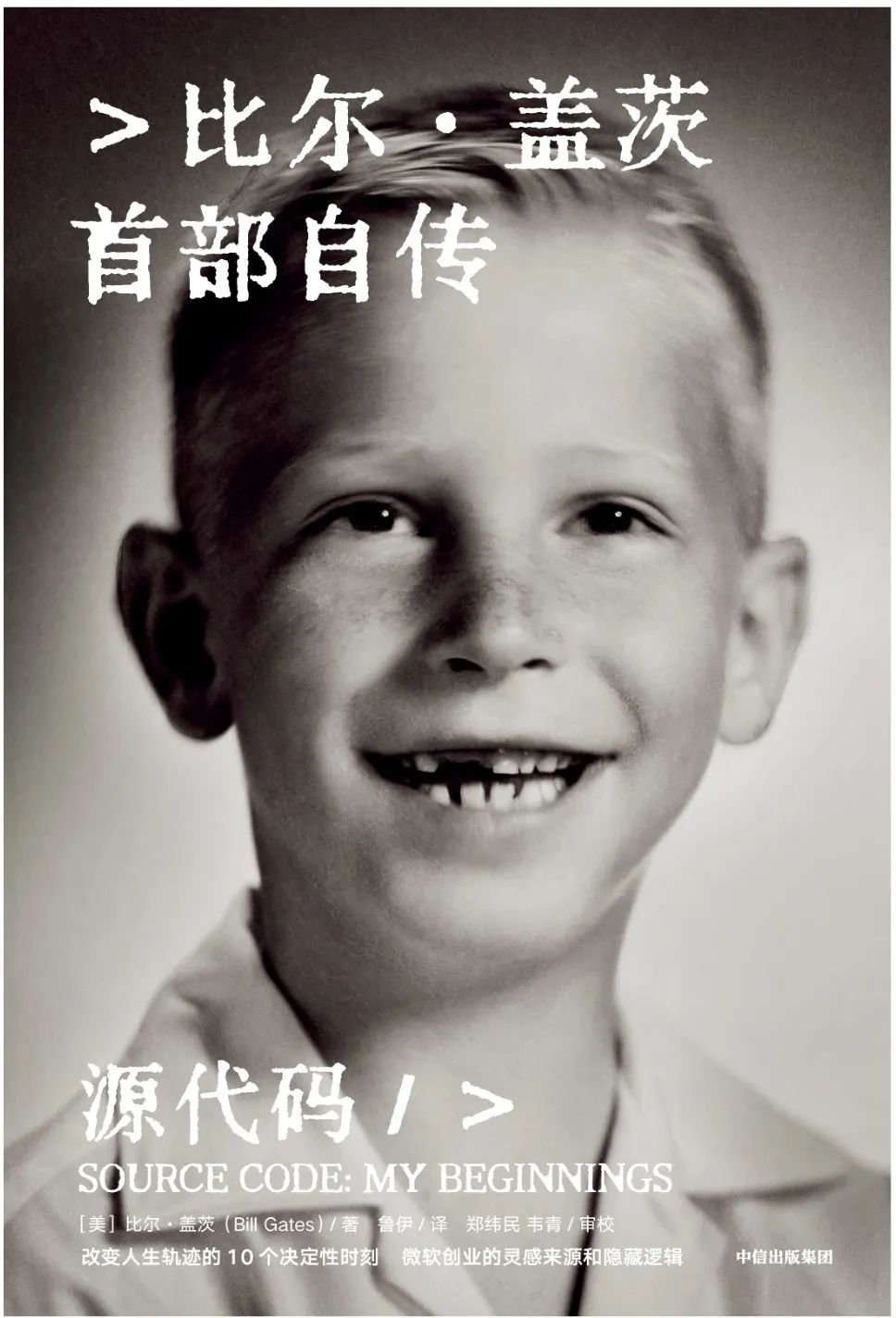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1.纸牌高手,家族传奇
有朝一日,一家大公司会应运而生。有朝一日,一些包含数百万行代码的软件程序,会成为全世界数十亿台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核心。与之相伴的还有财富和竞争,以及时刻存在的忧虑——为如何始终处于技术革命的最前沿而担忧。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摆在那儿的只有一叠纸牌和一个目标:击败我的外祖母。
在我们家,要想让人对你高看一眼,再没有比擅长玩游戏(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牌)更简单快捷的方式了。玩拉米纸牌、桥牌或凯纳斯特纸牌时得心应手的人会赢得大家的尊重,我的外祖母阿德尔·汤普森正是因此而成为家族传奇。
「姥姥玩起牌来是最棒的!」在我儿时没少听人这么讲。
外祖母在华盛顿州乡下长大,铁路小镇埃纳姆克洛是她的老家。此地离西雅图不到50英里,但在她出生的1902年,那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她父亲是一名铁路电报员,她母亲艾达·汤普森(我们口中的「拉拉」)后来靠烤蛋糕和在本地锯木厂兜售战时公债发了笔小财。
拉拉也经常玩桥牌,她的牌搭子和对家都是镇上上流社会的人,比如银行家的太太和锯木厂的老板。这些人或许比她更有钱,社会地位也更高,但拉拉靠着打牌时技高一筹或多或少地缩小了距离。她的这种天赋传给了我的外祖母,并在某种程度上传给了我母亲——外祖母唯一的孩子。
我很小便被口传心授了这种家族文化。在我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拉拉就开始叫我「老三」(Trey)。Trey在纸牌玩家的口中是「三点牌」的意思,它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我是家族里依然在世的第三个比尔·盖茨,另外两个是我祖父和父亲。(我其实是第四个比尔·盖茨,但我父亲选择自称为「小比尔·盖茨」,于是我便成了比尔·盖茨三世。)
在我5岁时,外祖母教会了我玩纸牌游戏「钓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起玩了成千上万把纸牌游戏。我们玩牌是为了找乐子,逗彼此开心并打发时间,但我外祖母玩牌也是为了要赢,而且她总能赢。
她高超的牌技当时便让我着迷。她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天生的吗?鉴于她笃信宗教,或许这是来自上天的馈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不出答案。我只知道,我们每次玩纸牌,她都能赢。不管玩的是哪种游戏,不管我有多煞费心机,结果都是如此。
20世纪初,基督教科学派的影响力在西海岸迅速扩大,这时候,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变成了虔诚的追随者。我觉得,我的外祖父母从基督教科学派中汲取了力量,他们欣然接受了其教义,即一个人应当从精神世界而非物质世界中寻求真正的自我。他们对此信受奉行。
因为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不以人的生理年龄为念,所以外祖母从不庆祝生日,也从不透露年龄,甚至不告诉别人她是哪一年出生的。尽管自身信仰坚定外祖母却从不会把她的观点强加于人。我母亲并不信奉这一教派,我们家也一样,但外祖母从来没试图劝说过我们改变信仰。
外祖母的信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让她成为一个极其自律的人。那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对公平、正义和为人诚信有着严格的个人准则。过好这一生意味着简朴度日,把时间和金钱奉献给他人,以及运用自己的头脑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系——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
外祖母从不乱发脾气,从不搬弄是非,从不评头品足,也根本不会耍花招。她往往是屋子里最聪明的那个,却总小心翼翼地让别人展现光彩。可以说外祖母低调内敛,她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让她散发出富含禅意的淡定自若的气质。
就在我5岁生日的前两个月,我的外祖父小J.W.马克斯韦尔死于癌症,年仅59岁。为了遵从其基督教科学派信仰,他拒绝接受现代医学治疗,临终前的那几年饱受疼痛折磨,外祖母在其左右照料也遭了不少罪。我后来才知道,外祖父认为他患病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祖母的行为导致的,因为在上帝眼中,她曾犯下某种无名之罪,如今才会惩罚到他头上。即使这样,外祖母依然隐忍地陪伴在他身边,给他力量和安慰,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最清晰的一段童年记忆是,我父母不让我参加外祖父的葬礼。我对所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父母和姐姐去见了外祖父最后一面,我则在临时保姆的看管下留在家中。一年后,我的曾外祖母拉拉在去外祖母家看她的时候去世了。
从那一刻起,外祖母将她所有的爱和关注都倾注在我和我姐姐克里斯蒂身上,后来还有我妹妹莉比。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她始终陪伴在左右,对我们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我能捧起书本之前,外祖母就读书给我听。
那几年,她为我读了一系列经典作品,比如《柳林风声》《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夏洛的网》。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开始教我自主阅读,帮我拼读出《九只善良的狗》(TheNineFiendlyDogs)《美好的一天》(It'saLovelyDay)和家里其他一些书中的生词。
当我们一起把那些书全都看完后,她开车带我到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东北分馆,借回更多的书。我知道,她读过很多书,似乎对一切都略知一二。
外祖父母在西雅图的高档社区温德米尔建了一座大宅,足以容纳一干孙辈和各种家庭聚会。外祖父死后,外祖母仍然住在那里。周末,克里斯蒂和我有时会在那里过夜,轮流享受在她房间里睡觉的特殊待遇。另一个人则睡在旁边的一间卧室里,那个房间以淡蓝色为主调,从墙壁到窗帘莫不如此。街灯和过往车辆的车灯照进来,在蓝色的房间里投下诡异的阴影。我害怕睡在那里,每当轮到我睡在外祖母的房间里时,我总是很高兴。
那些周末的探访有着特殊的意义。外祖母的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英里远,但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仿如假期。那里有游泳池,还有一个外祖父建在房子侧院的迷你高尔夫球场。外祖母还允许我们看电视,这在我们家是被严格管控的。
她热衷于一切活动,在她的影响下,我姐姐、我和我妹妹都变成了劲头十足的游戏玩家,我们把所有游戏都当成竞技体育,无论是「大富翁」「大战役」还是「记忆游戏」。我们还会买两幅一模一样的拼图,这样就能比赛看谁完成的速度快。我们都知道外祖母最喜欢什么,晚餐后,她常常发起牌局,然后杀得我们屁滚尿流。
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大约在我8岁时,我第一次对此有了模糊的认知。我依然记得那一天,我坐在外祖母对面,中间隔着餐桌,克里斯蒂坐在我旁边。房间里有一台巨大的木制收音机,就算在当年,它也算一件古董。靠着另一侧墙摆着一个大陈列柜,里面摆放着我们每周日共进晚餐时会用到的特制餐盘。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桌上纸牌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我们快速地抽着牌,手忙脚乱地配对。我们玩的是一种名叫「极速接龙」的纸牌游戏是接龙的多人加速版。在「极速接龙」中连续获胜的玩家能记住自己手上的牌、其他玩家亮出来的明牌,以及牌桌上公牌堆里的牌。拥有强大的工作记忆和模式匹配能力的人能在这种纸牌游戏中占上风,因为他们可以立马知道从牌桌上抽到的某张牌如何与手中的牌配对。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我所知道的只是玩家需要干点儿什么才能让牌运变好,而外祖母显然深知其中的诀窍。
我盯着手上的牌,大脑高速运转,试图找出能配对的牌。这时,我听到外祖母说:「你的6点牌可以打。」接着,她又说:「你的9点牌可以打。」她一边玩着自己手上的牌,一边指导我和我姐姐。不知为何,她好像对牌桌上的一切都心中有数,甚至知道我们每个人手上的牌——这并非魔法。
她是怎么做到的?对玩牌的人来说,这不过是基本技能。你越是能准确地推算出对手手中的牌,赢的机会就越大。不过,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这不啻天启。我第一次察觉到,尽管纸牌游戏存在神秘和运气的成分,但其中仍有值得我去学习从而提高自身胜率的东西。我领悟到,外祖母不只是足够幸运,也不只是有天赋,她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大脑,而我也可以这样做。
从那时起,我每当坐下来玩上一局纸牌游戏,便会意识到打出的每一手牌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只要我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外祖母也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让这条学习之路变得平坦易行。
她本来可以和我一起坐下来,一步步引导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教给我各种纸牌游戏的战略战术,但说教不是她的风格,她一向以身作则。于是,我们就一局又一局地玩下去。
我们玩「极速接龙」「金拉米」「红心大战」,还有我最喜欢的「排七」。我们玩外祖母最喜欢的「金拉米」的高难度版本,她称其为「海岸警卫队拉米」。我们偶尔也会玩一下桥牌。我们玩遍了霍伊尔关于纸牌游戏规则的书里提到的每一种纸牌游戏,不管其流行与否,连冷门的「皮纳克尔」也没放过。
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研究她。
有个计算机科学术语叫「状态机」,它是一个程序的组成部分,在接收到一组输入后,可以根据一系列设定条件的状态采取最优行动。我的外祖母拥有一个精密调校的纸牌游戏状态机,她大脑中的算法有条不紊地推演着各种可能性、决策树和博弈论。我那时候还无法清晰地表述这些概念,但慢慢地,我凭直觉感受到了它们。
我注意到,即便是在一局游戏中那些独一无二的时刻,比如出现了一种她或许从未见过的可能的打法与赔率的组合,她通常也能采取最优行动。如果她在某一时刻似乎错误地抛出了一张好牌,继续玩下去,我便会发现她做出这样的牺牲是有原因的: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一局又一局地玩,我一局又一局地输,但我一直在观察,也一直在进步。从始至终,外祖母一直温柔地鼓励我。「动动脑筋,老三。动动脑筋。」当我琢磨下一步的打法时,她总是这么说。她的潜台词是我只要开动脑筋,并保持专注,就能打出正确的牌,就可以赢。
有一天,我真的赢了。
没有大张旗鼓庆祝,没有巨额奖金,也没有击掌欢呼。我甚至不记得,当我第一次在一天中赢的局数比外祖母多时,我们玩的是哪种纸牌游戏。我只知道她很欣慰,我确定她笑了,这是对我成长的认可。
到后来,大约花了五年时间,我就一直能赢了。那时,我几乎已经是个好胜成性的青少年。我享受这种心智的较量,以及学会新技能所产生的强烈的满足感。
玩纸牌教会我:无论某些事情看起来多复杂、多神秘,我们通常都能最终琢磨出个究竟。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
2.千里路途,上千次学习机会
二年级那个学年结束后没几天,母亲和外祖母就把姐姐和我塞进车里,开启了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假期。
克里斯蒂和我一直以来都将这次旅行称作「迪士尼乐园之旅」,事实上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我母亲看来,对她的孩子们来说,即将踏上的千里路途意味着上千次学习机会。
1963年6月的那个早上,我们按照「妈区时间」——经我母亲调校后的时间——在8点15分准时出发,开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段路程。
我们将用四天时间抵达洛杉矶。我父亲在那周有工作无法脱身,因此他会坐飞机赶过去跟我们会合,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然后把车开回家。
我母亲刚买了一台代表当时顶尖打字技术的IBMSelectric打字机,它装备有高尔夫球大小、字号和字体各异的金属字体球。你可以根据自己对字号和字体的需要,随意更换金属球,你甚至可以用它打出草体字。我觉得它简直太酷了。
起程前,我母亲为我们姐弟俩准备了一份旅行日志,每天两页,供我们记录所见所闻。她用打字机敲出了草体字的标题,列出途经的城市和每天大概的行驶里程,还列出了需要填写的类目。日志差不多是这样的:
日志
日期/途经城市/行驶里程
地形
天气
人口分布
土地利用情况
产品
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
其他
(额外描述)
在页面下方,她为当天的旅行留出了一个文字描述栏。
对于这项练习,我们绝无数据匮乏之虞,因为我母亲以她一如既往的充沛精力为每天都安排了详尽的参观游览行程,包括两座州议会大楼、俄勒冈州的熔岩森林、几所大学、金门大桥、赫氏古堡、圣昆廷监狱、圣迭戈动物园,一场蜂蜡制作演示及其他景点。
我母亲开车的时候,外祖母会给我们读关于著名的赛马「黑神驹」的小说。这匹纯血马屡次在竞速赛和耐力赛中打破纪录,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赛场战绩。
姐姐和我一边听着,一边望向车窗外,在脑海中记录着可以写进旅行日志的内容:一个又一个苹果园、一栋又一栋土坯房、一辆辆载着巨大花旗松原木的卡车,以及一口口油井。
每天晚上,在汽车旅馆里,克里斯蒂和我都会分门别类地记下我们的见闻。她写得很认真,因为她知道母亲随后肯定会仔细检查,用红笔改正语法和拼写错误。在一个小一点儿的笔记本上,我用尽可能工整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补充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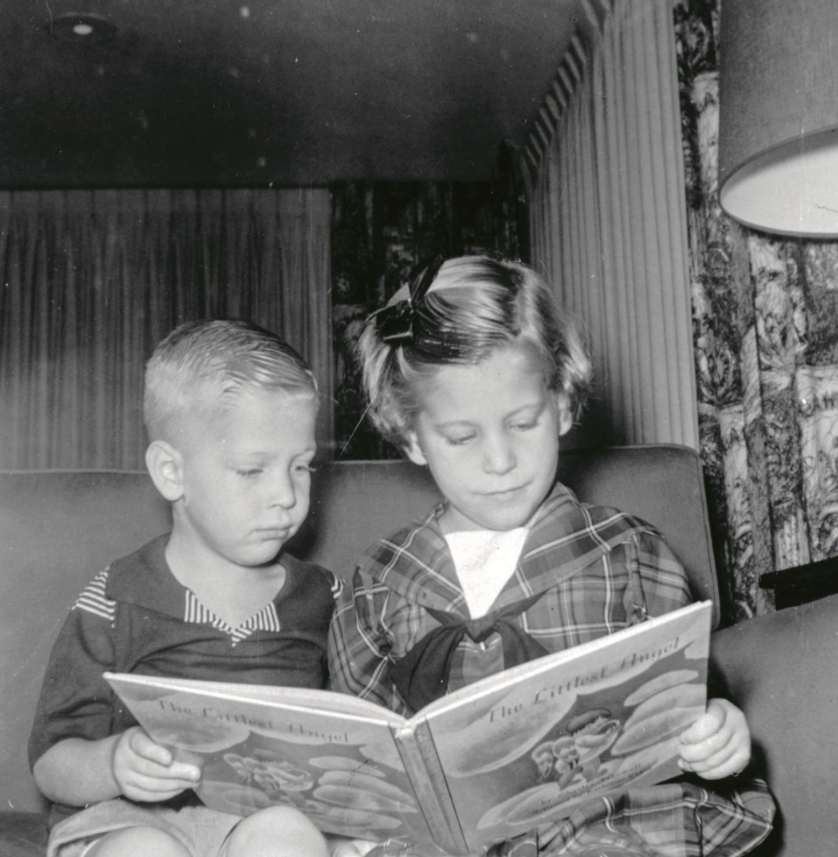
比尔·盖茨和姐姐克里斯蒂
母亲力求让我们借助每天记下的日志条目,学到有关地理学、地质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并且在好奇地观察周遭事物的过程中领略专注的艺术。正是因为这些日志,我才了解到钟乳石悬垂向下而石笋竖直向上的原因,而且假如有人想知道的话,我还能说出想要爬上华盛顿州议会大厦的穹顶,需要走262级台阶。
当父亲在洛杉矶与我们会合时,我们兴趣盎然地向他转述了一路上刚听完的那本书的故事:一匹神奇的赛马如何被精心地培育出来,以实现战无不胜的目标。有朝一日,我们会恍然大悟,我母亲对子女似乎也肩负着类似的使命。
在那次自驾之旅的夏天,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祖母对基督教科学派信仰的执着。在我看来,这种信仰特别注重条理性和纪律性。
与我的祖父母一样,外祖母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也是阅读教派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编写的「圣经日课」,这是她几乎雷打不动的每日作息常规。外祖母每天早上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1点半睡午觉,她总是在下午6点钟吃晚饭,饭后必定要来上一粒时思牌黑枫糖胡桃糖,这是她每天唯一的放纵之举。晚饭后,她会打牌或玩游戏,然后上床睡觉前重读一遍「圣经日课」。
20世纪60年代末,外祖母在胡德运河边购置了一栋度假屋后,为自己的日常作息增加了一项游泳。每天不管天气如何,即便冒着狂风冷雨,她都会在冰冷的水中优雅地侧泳,她那精心梳理的发髻一丝不乱,徒留我们担心她会被滚滚白浪吞没。
对于基督教科学派信仰的细节,我一度所知甚少。直到某个周末,当时因我父母外出,外祖母住在我们家。我和克里斯蒂还有她的朋友苏一道,把前院浇草坪的洒水喷头打开,穿着泳衣在水雾中跳来跳去。这期间,不知是谁(可能是我)想出了个主意,提议我们应该玩点儿刺激的。
我们把连接洒水喷头的水管拖到了车道上,穿着轮滑鞋轮流跳过喷溅的水流。那时候,有些轮滑鞋的轮子还是金属制成的。我不记得我们的轮滑鞋是哪一种了,但不管是哪一种,正如我们很快将发现的,它们都不适合在湿滑的车道上穿着滑行。
克里斯蒂穿着轮滑鞋助跑起跳,跃过了水管喷出的水流,但落地时失控了,重重地摔在沥青车道上,右臂肘部以上骨折了。
接下来,我只记得自己在克里斯蒂的房间里害怕得缩成一团,她疼得大声哭喊,而外祖母纠结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根据基督教科学派的观点,通常而言,信徒们会尽量避免去医院,多求助于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疗法术士,据说他们能够通过祈祷来治病。
据我猜测,当我们在克里斯蒂的房间里等待时,外祖母给她的信仰疗法术士打了电话。这个据我们所知名叫「保利娜」的女士或许跟外祖母说,骨折不是闹着玩的,需要接受正规的治疗。那天晚些时候,克里斯蒂去了附近的儿童骨科医院,她的整只手臂被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打上了石膏。
一两年后的一天,我爬上厨房的操作台,试图从高柜里拿一只玻璃杯,这时我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剧痛,摔到了地上。当外祖母发现我时躺在那里的我已是神志不清。这一次就医完全没有耽搁,我被确诊得了阑尾炎,好在外祖母及时把我送进医院,在阑尾破裂前做了切除手术。
克里斯蒂和我多年来一直开玩笑说,感觉只要父母不在家,坏事就必然登门。除此之外,这些突发事件也加深了我当时对成人世界的疑惑:为什么我的这位理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祖母从不去医院,甚至从不使用现代药物?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看报纸,坐飞机,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然而,一部分的她却生活在那个看起来更像是迷信的信仰之域中。
我们家所奉行的宗教信仰更像是一种社交实操和智力活动。
我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脱离基督教科学派,但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参加华盛顿大学公理会的聚会。这是一家在西雅图颇受欢迎的教会,拥有2000余名教友。富有个人魅力、在本地小有名气的牧师戴尔·特纳在该教会的兴旺中起着关键作用。公理会奉行的教义对于圣经的解读留有很大的余地。

比尔·盖茨一家五口
特纳牧师在解经时通常持自由主义观点,将经文与支持同性恋权利和民权运动等进步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他后来成为我父母的好朋友,虽然我父亲曾在高中时拒绝有组织的宗教,我母亲却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对宗教的道德教诲有所接触,这是他们相互妥协的成果之一。
我喜欢去主日学校,虽然它是需要正装出席的一系列活动之一。特纳牧师开出了一个长期有效的奖励条件:能背诵出《登山宝训》的孩子可以在太空针塔顶层的餐厅享用一顿免费的晚餐。坚振礼课上的绝大多数大孩子都接受了这项挑战,克里斯蒂更是在11岁左右就提前得到了她的那份奖励。
于是,在那之后不久,在和家人一起去华盛顿州海边自驾游的路上,我便坐在后座抱着《圣经》,背诵「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及《马太福音》中基督的其他道德训诫。当特纳牧师宣布我赢得了自己的太空针塔晚餐时,其他孩子都惊讶地打量我,一股自豪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敢肯定,我将耶稣传递的信息部分融入了自我意识,但这项小小的成就也是一个考验我能力的脑力测试。
正如耶稣所说,聪明人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在那个年纪,我的磐石就是智力、好记性和自己的理性力量。
3.与众不同的传家宝
坐在车后座——或是在任何地方——读书,这就是我的默认状态。
在我读书时,时间过得飞快。我屏蔽了外界的一切,只是隐约地意识到周围家人的存在,比如我母亲在叫我摆好餐具准备吃饭,我姐姐在和她的朋友一起玩。无论身处自己房门紧闭的卧室,还是汽车后座、烧烤聚会场所或教堂,我都沉浸于脑海中的世界。
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偷得片刻闲暇,遁入书中天地,独自探索、吸纳新的知识点,无须借助他人。
外祖母被我视为博览群书的楷模,她完全支持我的这个习惯。放学后她会开车带我去附近的图书馆借回一大摞新书,塞进她的车里,供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阅读。
在外祖母家,我经常一头钻进地下室,那里存放的《生活》周刊摆满了一整墙的书柜。她订阅该杂志的时间必定有数十年之久,并且觉得这份概览世间万象的期刊值得保留。

当时,我们刚养了一只英国古代牧羊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圆饼」。我在那些旧杂志中翻找小狗的照片,剪下来装订成册。后来,但凡需要完成学校布置的作文或研究项目,我总是会从翻阅一摞摞的《生活》周刊旧刊,寻找插图开始。
逐页浏览这些杂志,让我有机会沿着一条自己选择的蜿蜒曲折的求知路径自在而行,所涉猎的内容既包括时事新闻和名流逸事,也覆盖战争、科学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缩影。
我父母从来不会在买书这项开支上犹豫。
我家的传家宝之一是一套1962年版的《世界百科全书》,那是20卷红蓝相间的大部头,书页光滑平整,配有色彩绚丽的插图。我为书中博大精深的内容而倍感惊奇,那些分别绘有骨骼、肌肉和人体器官,叠在一起便正好组成完整人体的透明塑料插图页,尤其让人叹为观止。
《世界百科全书》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从中了解到自然、地理、科学、政治和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门类的知识。差不多9岁时,我便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套书。每年1月这套百科全书都会发行一本简要介绍前一年的历史性时刻的年鉴。当它寄到时,感觉就像一份迟来的圣诞节礼物。我也会一字不落地把它们读完。
通过阅读,我能找到针对各种问题的答案。当然,一个答案往往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越是深入挖掘,想要知道的东西就越多。
我曾对企鹅非常感兴趣,可以说出阿德利企鹅在水下憋气的时长(6分钟)和帝企鹅的身高(4.3英尺)。有那么一段时间,火箭和桥梁令我心醉神迷。我画了无数幅与火箭有关的图画,上面的火箭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我还一张接一张地绘制自认为优美典雅的桥梁,那些桥又长又高,有着精致繁复的格栅和似乎十分牢固的桥塔。
但在某一时刻,我意识到虽然它们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我并不知晓其原理。如何设计一座不会倒塌的桥梁?如何制造一枚真的能飞起来的火箭?在我的想象与现实事物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这让我深感苦恼。在我看来,自己的设计不过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幼稚的想法。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对我在学校认识的那些孩子来说,阅读量大、聪明、对老师教的内容感兴趣,这些都是女孩的特质。这种一概而论的偏见很可怕,但我确实也有这种想法,其他人也一样。
三、四年级时,我意识到,把阅读《世界百科全书》当成消遣,跟外祖母玩「红心大战」纸牌游戏,或是想要讨论为什么桥梁不会倒塌,这些都不够酷。图书馆举办的夏日阅读活动的参加者,除了我,都是女孩。课间休息时,其他孩子会拉帮结伙地在一起玩,而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大一点儿的孩子会故意跟我过不去。
现在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感受倒不是孤独或伤心,可能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这帮孩子的看法和我如此不同?
一起聊聊:
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为什么?
你家的传家宝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