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章咪佳
2月18日,持续深化“八项工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动员部署会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如何“在赓续历史文脉上实现新提升”?
今天起,人文读本将持续推出“文脉赓续”大型融媒体报道,寻访浙江籍文化学者的故事,显现根在浙江,同时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影响的,可以作为浙江文化名片的人物、家族、宗派,塑造真实清晰的当代浙江文化形象。

卓鹤君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采访结束时,卓鹤君先生站起来送大家到门口,特地跟我说了一句:“你可以乱写。”大家都笑了。
82岁的卓先生高大、笑靥拂面,他人生第一个大型个展《山魂》今天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闭幕。卓鹤君师从陆俨少先生,从1980年代开始,抽象的现代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山水画面貌。
他说可以“乱写”是完全真诚的建议。他就是一个不怕画坏的画家,胆子很大。他说:“山水画需要大胸怀、大眼界,看到的世界要全部都装得进去。”当然这也是他敢画的后手。
卓鹤君的山水间,马蒂斯和顾恺之初识,温岭石塘和毕加索前世有共同基因,敦煌,更是成天地跟蒙德里安、米罗、康定斯基聚会。他的笔墨在纸绢上创造出了一个乾坤袋,时空可以折叠,全部为他所调用。
但是他画了六十多年画,从来都只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展开。再大的巨幢幛作品,顶多由四尺(138x69cm)的小画幅一张张拼接而成。他的画室在家里,身兼数职:也是客厅,又是饭堂,还是堆满玩具,孙子、孙女儿玩耍的游乐场。宇宙观还真是一样的。
他也很喜欢玩,觉得“当画家真幸福”工作之一就是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吃美食也有出处,“农家乐都是当地山水的滋味啊。”
而且,他从来两耳不闻画桌以外的事。那天画展开幕致辞,他感谢各方,谈了专业,然后说出压轴语录:感谢夫人。并且自豪地表示:“我是怕老婆的。”
所以你看他的画,就会感觉像是卓先生驾着一艘满载宝藏的大船,驶过来了。
至于这里面有什么,你得细细地看,局部和全局,凑近、退远不一样;总之每次看,都会发现新的意思。
今年春天《哪吒之魔童闹海》“大闹”全球荧幕后,中国动漫再次被溯源到祖师爷一辈——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早就认识卓鹤君的山水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8年制作的动画片《山水情》,获得当年国际动画电影节最高奖项,也成了中国独创水墨动画的绝唱。
这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时长19分钟;包含的近百幅山水背景画,全部由卓鹤君设计、绘制。
1987年,上海美影厂的编导王树忱先生写了《山水情》的剧本,讲述一位少年在老琴师的指引下,从听琴、试琴、学琴到出师的故事。其间,师徒二人纵横于山水之间,外师造化,心神交会。离别之际,老琴师将琴留赠与少年,少年登高抚琴以谢师恩。
《山水情》在前期创作的程序和方法上,与以往的《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不同,这些都是先有齐白石、李可染的画作风格作参照和依据,再去寻找或创作与之相匹配的动画剧本,画家们都并没有真正深度参与到动画影片的创作中。
而《山水情》在筹备之初,导演组便邀请外聘的人物设计吴山明、背景设计卓鹤君,加入摄制组共同研读剧本,探讨影片的视觉呈现方式。
再现一下“乌云墨雨”这组将影片情绪推向高潮的画面效果,这场山雨,至今仍是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段经典cut——
老琴师回到深山,少年登高抚琴送别,往昔历历过目,直到墨云压顶。这时画面墨色越来越厚重,琴声转向激越昂扬,几团凝重的墨云贴着镜头渐次绽开,蓄势已久的墨雨倾泻而出,骤雨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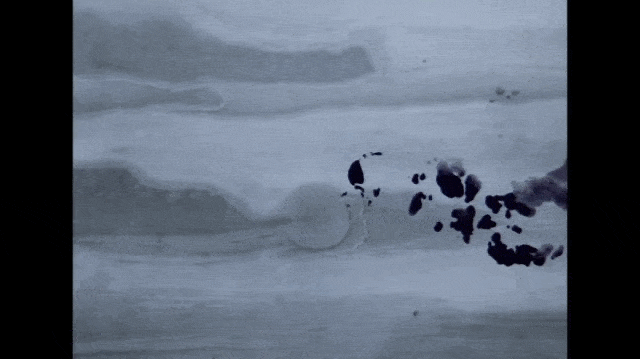
图源:费那奇动画小组
当年没有GPU渲染,影片里这组风起云涌的效果,就靠现场作画、连续摄影的方法完成。
在室内架起倾斜的透明玻璃平台,将宣纸固定在平台一侧。吴山明和卓鹤君共同现场创作:浓墨、淡墨互相破墨,两位画家你一笔我一笔,无需编排,默契使然。摄影师就在另一侧,将这幅墨韵淋漓的画面即时记录下来,后期合成实拍画面与动画场景,营造出了观众所见的疾风骤雨。
两位青年艺术家是新浙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彼时都在探索中国画的革新。动画片里初见端倪,吴山明设计的人物造型还没有出现后期成熟的风格,但已经显露独特的个性。卓鹤君的山水,在传统国画笔墨技法和审美规律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有种别具一格的现代意趣。
导演没有给卓鹤君配团队,他一人画到底,动画片里时而天朗风清,时而满目云烟的意境,全部产自美院景云村宿舍的小阁楼。
“画了好多底稿,按照剧本把景补上去,比如人物在山上跑,山形就有变化,一些局部都是我一张一张画出来的,然后再一个景一个景拍。”当时,卓鹤君画了整整一年。

1987年,《山水情》主创在杭州某招待所内讨论创作构思左起:段孝萱、卓鹤君、阎善春、特伟、吴山明图源:费那奇动画小组
还剩一个月的时候,他胆结石发作住进医院。导演特伟来病房看他,两人请求医生先打针把病压下去,“然后我从医院里跑出来把画完成,特伟回上海把动画拍出来。”
卓鹤君绘制的大部分背景原稿,后来都直接用在了影片画面中,这些画稿忠实地体现了他当时几近纯熟的艺术语言。
如果想趁展览最后一天去重温《山水情》中的意蕴,可以直奔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山魂”展览的第一个展厅,有卓鹤君1980年代前期三件水墨作品《行云流水》《山雨》《醉雨》里的片段。
在以“行云流水”为主题的第一展厅的第一个组团,描绘月下湖山、富春山雨的作品,被策展人聚拢在同一个展示空间。他说倘若有机会,希望它们会与黄宾虹先生变法时期的夜山和雨山照照面,谈谈天。
这个厅里的“夜山、雨山”群中,陆俨少先生为其中一幅画题字“山雨”——这幅“雨”里,满眼是山风;山形在勾、泼、冲、染的笔墨实验里,飘摇。
当时七十几岁的陆先生,自己就是上一轮绘画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山水画“北李(李可染)南陆”坐镇的一头。但他从来不要求学生固守,反而非常鼓励创新。
1980年代初期,又一个中国山水画系统内部生发出的变化期已经发端。卓鹤君身在其中。

《行云流水(二)》68x179cm1984年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卓鹤君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山水方向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人物画方向,有李震坚先生的研究生,山水画方向,陆俨少先生招了我们五个学生。”
1979年刚考上研究生时,卓鹤君问过老师:“有人说您是学石涛的?”
陆先生说不是,“我是学董其昌的。我与石涛是师兄弟。”
老先生的格局,给卓鹤君很大的启发,“与石涛比肩,站位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高。”
卓鹤君感到当时学校有一种很强烈的专业学习气场,每个学生入校后,对自己就有新的要求。
比如临摹的基本功,陆先生具体列了必临和选临的画,比如宋、元的范宽、李唐、黄公望、王蒙都是必临的;选临可以挑明、清时代自己喜欢的画家。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卓鹤君按照陆先生要求,不仅重点临摹了宋、元、明、清必临画的局部,还临了陆先生所有的课徒稿(老师教学时的示范画稿)。
陆俨少先生很讲究体验生活,重视写生创作。他曾专门到三峡一带写生。他看得很细,特别是石头的结构。在画面上表现的是水,但他说,画水就是画石。画浪、画溪就是画水下的石头,画瀑布就是画山。掌握石头的趋向,水的流向就出来了。
到陆先生这里,学生们主要是看他画,起笔收笔,勾、皴、擦、染这些用笔上的要害,都要记住。
对具体作画的过程,陆老说过一句很朴素但很要紧的话:“笔要加得上,停得下”。这两句话,卓鹤君深有体会,一生受益。
很快,年轻人的突破遇到了更多元的生态。当时,国内艺术院校重新大量引进国外出版物,欧美的画报、画册简直“倾泻”下来。年轻人看了激动,有样学样,很自然。
当国内艺术界在中西冲撞中发生新潮时,卓鹤君正在直面西方:1986年至1989年期间,卓鹤君由美院公派,先后两次赴美半年交流、讲学。当时西方已经轰轰烈烈地进入后现代主义。而往前一百年、五十年的野兽派、立体派,超现实、抽象表现,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全世界。
当时,四十几岁的卓鹤君身处主流现场。有一件事情他后来常跟学生提起,当时在美国观看了各种现代艺术展,但是坐下来思考,“脑中却一片空白”。
“能感觉到(西方的)这些形式很好。但是如果放弃自己的中国画,去搞纯现代艺术,没有文化认识的基础,是‘空’的”。卓鹤君很清楚,自己的水墨实验,是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完成中西交融。

《墨彩丹青图》136x238cm1988年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1989年从美国回来,卓鹤君对自己想要探索的山水画创作方向已经非常明确,“吸收西方绘画中构成、色块运用等理念,但采用中国传统技法来完成。”
这一年,他的作品量大、面貌丰富,一个中西流通的世界打开了:在采撷中国群山的基础上,汉代画像砖、敦煌249窟《狩猎图》、宋体印刷字……康定斯基、蒙德里安、波洛克……组成了一支随时待命的团队,卓鹤君布局一个什么样的宇宙,各位点名出列,山水共舞。
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他连续创作了《山魂》系列水墨作品:近二十年,前后五件巨幛。
1995年,卓鹤君完成了第一件大山水《山魂一》,高近4米,宽超过8米。这幅画就展在美院美术馆层高最高的二楼圆厅,今天是你能在展厅见到它的最后一天。
进门见山:远望,天柱之峰叠成万千葳蕤;走进细部,茫茫苍苍里不识深浅。再从山里走出来:起首和结尾的篇章,有几块纯黑平涂的方块彼此呼应——中国画里不会看到这种表达。是的,罗伯特·马瑟韦尔(西方抽象表现画家)到场了。
《山魂一》浑然天成的墨块里,有三大块其实是卓鹤君的“补丁”。
卓鹤君一生没有大画室,没有巨大的墙和地面铺开来画画。他在家里画,一张普通的书桌,最大也不过展开一张“四尺”。
他就这么一点点地生发自己的山水,一张画完,继续在另一张上生长。等画完了,会打包整座山川去学校——在大会议室里的地上拼图,人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地看效果。
那天从梯子高处往下看,卓鹤君发现有几处画面比较散。怎么办?他头脑中出现了马瑟韦尔大块的黑。
于是他就把那些“散”的、不知道是草木山石还是烟岚云岫,给涂成了墨块——画面马上整体了。
另是一种好看。

《山魂之一》820x350cm1995年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我问卓先生,画大画有没有草稿或者小样?
“没有的。”他说画再大的山,都是直接画。
所以我们最好奇的是,在这么小的局部上展开,怎么处理几百平尺的全局?
“丘壑全都在心中。”当然笔墨和跑山都是基本功,卓先生“25年考美院”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故事,能另作两篇文章。
“山魂”展的策展人说,卓先生整理出来的画作覆盖了美术馆全馆五个厅,还绰绰有余。所以从展陈思路上,从第一个厅开始就展出了卓先生成熟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是他1973年参加全国美展的《茶山春早》。“就像篮球运动员,学拍皮球的过程就不展示了,直接看高潮——灌篮。”
卓老师年轻的时候还真是篮球运动员,在学校球队任控球后卫,他因此拥有了画画的独门的“控局”秘方。他说打篮球的人有种“往前”的意识,扔球的人要提前预判球飞到的位置,接球的人要在运动中到达特定的地方接球。“有时候队友在这边,为什么把球扔到那边?其实是知道队友会去到对面候点了。”
画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超前”的全局观念。卓鹤君的研究生都记得也记得他携一众“四尺”到大会议室里,在地上拼图。
“卓老师这种超前的观念,开放的思维,对我们后学者有很多的启发。”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主任、美术馆馆长何加林,是卓鹤君的博士,他在展览上惊讶地发现,老师很多作品,他以前没有看过原作,甚至还有没有看到过的作品。“早些年我跟(张)谷旻一直蹿掇卓老师做个展,他总是说还不够。其实卓老师是非常谦虚,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看,他很低调,他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满足,总觉得自己还要往前走。
“我们学生辈,在作品的量、体量上,都不及卓老师。而且他的作品不是一个简单形式上的突破,其中有笔墨的内置。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雅,那种沉稳和它所蕴藉的画外之象,是现在很多做当代艺术所达不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方面望尘莫及。”

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中国美院山水画专业杭州人特别多,这里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和卓老师有关系。
何加林初学绘画时,在杭州上一个业余美校。1980年代初,他听说杭州市美协也办了业余美校,就想转去那里。他是奔着当时还在陆俨少先生门下读研的卓鹤君去的。
“我还有点忐忑,怕自己进不去(卓老师的班)。”这天他拿了一张临赵孟頫的树,在美校的传达室等着。
卓老师来了,看到他的画:“很好,你来(我的班)。”何加林就这样进入到这个班级学习,跟张谷旻做了同学。
那个时候学画很开心,学生们觉得卓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师,“他总是戴着一副变色眼镜,白天是个墨镜,晚上眼镜片就亮起来了。很时髦。而且卓老师年轻的时候个子还要高,长得很帅。”
卓老师在教学上非常用心,对这批学生有很大的期待,“他经常从学校里借了很多团扇作品的印刷品给我们临摹。当时是很稀罕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卓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
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任道斌也谈起,和卓鹤君交集比较多的阶段,正是他们带博士的时间,他就开始盘点卓老师一届一届的博士。
这份名单里面,何加林、林海钟、张谷旻、张捷……这些名字,今天都已经是中国山水画界的中流砥柱。
“不怕画坏,要大胆地画坏,没有关系,有新的东西会出来。”这也是卓鹤君跟学生说
得做多的,他自己就是非常敢下笔的。
他说新的东西出来以后,关键是你要有“加”的本事,也要有“停”的意识。很像前文里陆老说过的那句“笔要加得上,停得下”。
有人说,人类的艺术有三座巅峰:古希腊雕塑、中国山水画和德奥古典音乐。中国山水画不像古希腊雕塑那样容易被“看见”,不像古典音乐那样容易被“感知”,山水画是沉默的艺术,高妙到难以描述。
怎么“加”?
卓鹤君有一年监考,他一开始就注意看学生作画,目的就是看他们“加不加得上”。卓鹤君第一圈走下来,看一名学生作画感觉很不错,名字已经默默记下了。“一圈过后再看他,结果加得一塌糊涂,黑幽幽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
如果只看画作最后的效果,那一位在初试时肯定就会被淘汰,“加不上,就是把握度的能力不够,一加就加坏了。”
那什么时候“停”呢?
“停得下”,就是画画过程中感觉效果好,就要停笔,保留好的效果。
“加得上,停得下”,两者是相互的关系。
纵然无法言说,作为记者,作为观众,仍有必要言说,大胆地前进。
具体怎么展开呢?
还是卓先生的锦囊:你可以乱写。

请输入图片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