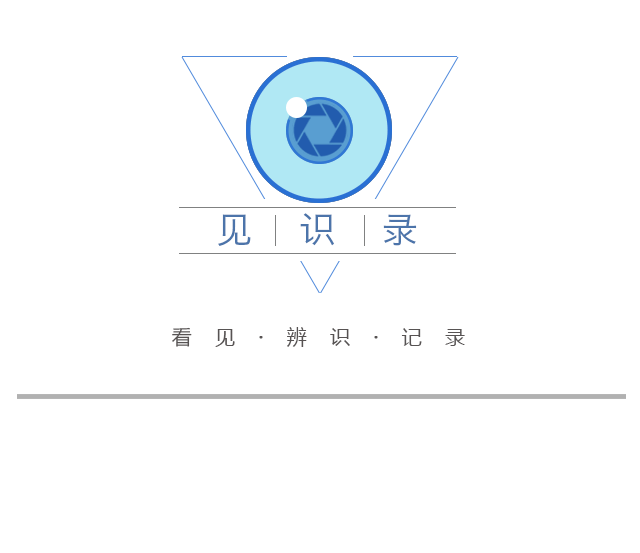2024年2月21日至22日,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迎来谢欣舞蹈剧场建团十周年作品《萨蒂之名·春之祭》的展演。

这部由编导谢欣与打击乐演奏家付艺霏联手打造的音乐舞蹈剧场作品,以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9首经典作品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为音乐蓝本,通过双钢琴双打击乐的创新编排与先锋舞蹈语言的交融,在舞台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轻与重、柔与刚的哲学对话。
经典重构:萨蒂的轻盈与斯特拉文斯基的狂野

作品分为上下半场,形成鲜明对比的艺术表达。上半场《萨蒂之名》以萨蒂的3首《裸体舞曲》与6首《玄秘曲》为音乐基底,付艺霏将其重新穿插编排为三组乐章:裸体舞曲1与玄秘曲2、4交织;裸体舞曲2与玄秘曲5、3呼应;裸体舞曲3与玄秘曲1、6收尾。

钢琴家李聪与打击乐手付艺霏的现场演奏,将萨蒂作品中标志性的简约与诗意化为流动的声景。
舞台上,12位身着浅色轻纱的舞者以松弛的肢体语言,演绎出风中摇曳的蒲公英、孩童嬉戏的纯真画面,甚至将“木头人”“老鹰捉小鸡”的童年游戏融入舞蹈叙事,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触摸生命的细腻温度。

下半场《春之祭》则是一场彻底的能量颠覆。付艺霏将斯特拉文斯基原作的管弦乐版本改编为双钢琴双打击乐配置,李聪、王鲁的钢琴与付艺霏、吕政道的打击乐形成暴烈对撞。

舞者们褪去柔美外衣,身着黑色紧身服装,在复杂多变的节奏中爆发出原始野性。谢欣坦言:“《春之祭》的拍子根本数不清,它是一道需要用身体本能去解的难题。”舞台上,樊小芸形容自己如同“一头野兽”,在重拍与不和谐音中撕裂出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迷雾笼罩的舞台空间里,钢琴的轰鸣与定音鼓的捶击化作春雷,舞者的躯干在抽搐与爆发间,完成对自然献祭仪式的当代诠释。

跨界共生:音乐与舞蹈的化学反应
此次演出打破了传统“乐池与舞台”的界限,四位音乐家与舞者共享同一表演空间,形成独特的艺术磁场。付艺霏将这种合作称为“化学反应”:“节奏为舞蹈搭建骨骼,而舞蹈让音乐视觉化。”

在《玄秘曲》段落中,打击乐的金属颤音与舞者指尖的细微震颤同步共振;当《春之祭》的定音鼓重击炸响,舞者的跳跃仿佛被音浪直接推入空中。钢琴家李聪特别提到,双钢琴版本如同素描,而加入打击乐后,“声音的颗粒感与舞蹈的肌肉线条共同构成了一幅动态影像”。

这种跨界实验在舞美设计中得到延伸。胡艳君设计的极简舞台通过高捷的灯光塑造出多重空间:上半场用暖色光晕勾勒萨蒂的忧郁水彩,下半场则以冷峻的切割光营造祭坛般的肃穆。李昆的服装设计同样暗含隐喻——从浅色纱衣到黑色战甲般的舞服,暗示着生命从轻盈到厚重的蜕变。
浴火重生:艺术与生命的互文
这部作品的诞生伴随着戏剧性的现实叙事。2023年12月,一场大火吞噬了谢欣舞蹈剧场的排练厅,十年积累的服装、道具与创作手稿化为灰烬。谢欣在发布会上回忆:“当我们在废墟前沉默时,《春之祭》的乐谱正躺在焦黑的纸堆里。”

这种毁灭与重生的宿命感深深烙印在创作中。舞者们坦言,经历火灾后的排练如同“用身体书写悼词”,而舞台上《春之祭》的狂暴演绎,恰似“从灰烬中迸发的凤凰之舞”。

谢欣将这次创作视为生命阶段的注脚:“十年前建团时,我们追求的是精确与控制;十年后的《春之祭》,我们要把身体彻底交给本能。”这种转变在编舞手法中清晰可辨:上半场精心设计的流动调度与下半场失控般的能量宣泄,共同构成了对“十年”的辩证思考——正如谢欣所说:“轻盈与沉重从来都是一体两面,就像火山爆发既是终结,也是新生的序曲。”

致敬与超越:百年经典的中国解构
1913年《春之祭》在巴黎首演,因其对古典音乐和舞蹈离经叛道的突破而引发骚动,自此,该作成为了全球编舞家的“试金石”。从皮娜·鲍什的泥土祭坛到玛莎·葛兰姆的图腾仪式,每个版本都烙印着时代的文化基因。

谢欣的创作则展现出东方语境下的独特解读:她没有复刻俄罗斯原始部落的献祭叙事,而是将“祭祀”抽象为生命能量的终极释放。当舞者在打击乐的轰鸣中集体倒地,那既是对斯特拉文斯基的致敬,也是对“十年磨一剑”的艺术团体的精神隐喻。

音乐改编同样体现着解构勇气。付艺霏在保留《春之祭》复杂节奏骨架的同时,用马林巴的晶莹音色软化管弦乐的暴戾,以颤音琴的绵长余韵呼应萨蒂的玄秘气质。这种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恰如萨蒂与斯特拉文斯基的精神共鸣——前者用极简音符探寻灵魂深处,后者以颠覆性节奏叩击生命本质。

《萨蒂之名·春之祭》作为谢欣舞蹈剧场的十周年纪念,既是对艺术初心的回望,也是面向未来的宣言。正如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合制作人刘鹤所言:“这不是终点,而是一场更宏大艺术实验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