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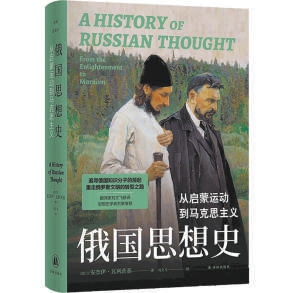
《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安杰伊·瓦利茨基著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
安杰伊·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是一部极具分量的学术巨著,自1979年英文版问世以来,它始终被视为研究俄国思想史的经典教科书。这部作品以宏大的视野、严谨的脉络和深刻的洞见,全景式地展现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激荡与嬗变,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进化史,也是民族身份与文明命运的沉思录。
构建独特的民族主体性
瓦利茨基的写作立场是其著作的独特价值所在。作为波兰学者,他既深谙斯拉夫文化的复杂性,又能以“他者”的冷静视角审视俄国思想的内在张力。他拒绝将俄国思想简化为“西方化”与“斯拉夫本土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将其置于欧洲思想史的坐标系中,揭示俄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接受与反抗西方思潮的过程中,构建独特的民族主体性。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启蒙运动虽受法国哲学启发,但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已显露出对农奴制的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并非简单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俄国社会现实的自我觉醒。瓦利茨基指出,俄国思想始终在“模仿”与“独创”、“欧洲化”与“本土化”的悖论中挣扎,这种挣扎恰恰构成了其思想史的核心动力。
瓦利茨基将俄国思想史视为一部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进化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教育普及和社会变革,俄国诞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多为贵族出身,却以“忏悔者”姿态为底层民众发声,如赫尔岑所言:“我们的罪孽是生来享有的特权,我们的救赎是为此赎罪。”书中详细梳理了三个关键阶段:
1.启蒙思想的萌芽(1760年-182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推动的“开明专制”催生了拉季舍夫和十二月党人,他们以自由理念挑战农奴制,却因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失败。
2.批判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1840年-1870年):别林斯基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将美学问题转化为社会批判,其“美即生活”的命题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哲学根基。
3.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1870年-190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点燃了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而普列汉诺夫则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埋下了伏笔。
这一脉络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到“革命者”的转型,以及思想如何从沙龙辩论演变为社会运动的催化剂。
“文学即思想”
瓦利茨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文学家纳入思想史的核心叙事。在俄国,文学从未局限于审美领域,而是承载着沉重的道德与哲学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通过宗教大法官的寓言拷问自由与信仰的边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史诗笔法探讨历史决定论与个体意志的冲突。这种“文学即思想”的传统,源于俄国社会的特殊性:当政治表达被专制政权压制时,文学成为知识分子唯一的公共论坛。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俄国,诗人的笔比政客的演说更有力量。”瓦利茨基通过分析文学文本中的哲学隐喻,揭示了俄国思想史上“审美救赎”与“社会革命”的双重路径。
全书贯穿的核心命题是俄国文明的自我定位问题。19世纪的思想家们深陷“东西方之争”的泥沼:斯拉夫派(如霍米亚科夫)将东正教和村社制度视为俄国的灵魂,而西方派(如恰达耶夫)则痛斥俄国的野蛮,主张全盘欧化。瓦利茨基指出,这种撕裂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心理的投射。俄国始终处于欧洲的边缘,既渴望融入西方现代性,又恐惧失去独特的民族性。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弥赛亚主义”,本质上都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试图在资本主义与传统村社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这种身份焦虑在当今世界依然回响。瓦利茨基的论述暗示,俄国的思想史实为一部“未完成的现代性”寓言,其核心问题“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仍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挑战。
俄国思想家的启示
作为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俄国思想史》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方法论创新:瓦利茨基打破思想史与政治史、文学史的界限,以跨学科视角还原思想的实践维度。
2.史料整合:书中涉及百余位思想家,从启蒙哲人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学家到革命家,文献爬梳之详尽令人惊叹。
3.批判性视角:作者对俄国思想的矛盾性和极端性保持清醒,既肯定其人道主义光辉,也批判其乌托邦狂热。
在当代语境下,这部著作的启示尤为深刻。当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时,俄国思想家的挣扎提醒我们:任何文明的活力都源于对“他者”的开放与反思。瓦利茨基的笔触冷峻却暗含温情,他让我们看到,思想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持续追问的勇气。
无论是赫尔岑流亡伦敦的孤独,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刑的顿悟,抑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中的写作,这些瞬间凝结成俄国思想的璀璨星座。瓦利茨基以史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让我们听见了那些在历史暗夜中回响的声音,它们或许未能改变世界的轨迹,却永远照亮了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