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赵茜通讯员薛子盈
上世纪,一把源自温州的改革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点燃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熊熊烈火,也点燃了一位青年记者内心的火焰,让他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成长史的观察者、记录者、见证者,与这片经济活力奔涌的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如今,这位书写者将目光移向义乌,在“鸡毛换糖”蜕变为“世界超市”的传奇里,让更多读者看到义乌这座“千亿强县”乃至浙江经济的无限潜力。
他是胡宏伟,现任澎湃新闻生态内容管委会副主席、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从业39年一直在追踪观察、研究浙江,曾出版《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等重要作品。
日前,胡宏伟新作《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义乌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为蓝本,深入剖析了义乌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县城崛起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经济传奇,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钥匙。
面对剧变的时代,曾经奔走于一线的媒体人有怎样的回望与思索?十多年如一日追踪观察浙江的写作者,如何书写义乌的故事?《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首发后,潮新闻记者专访胡宏伟,听他娓娓讲述自己因浙江改革史而“滚烫”的人生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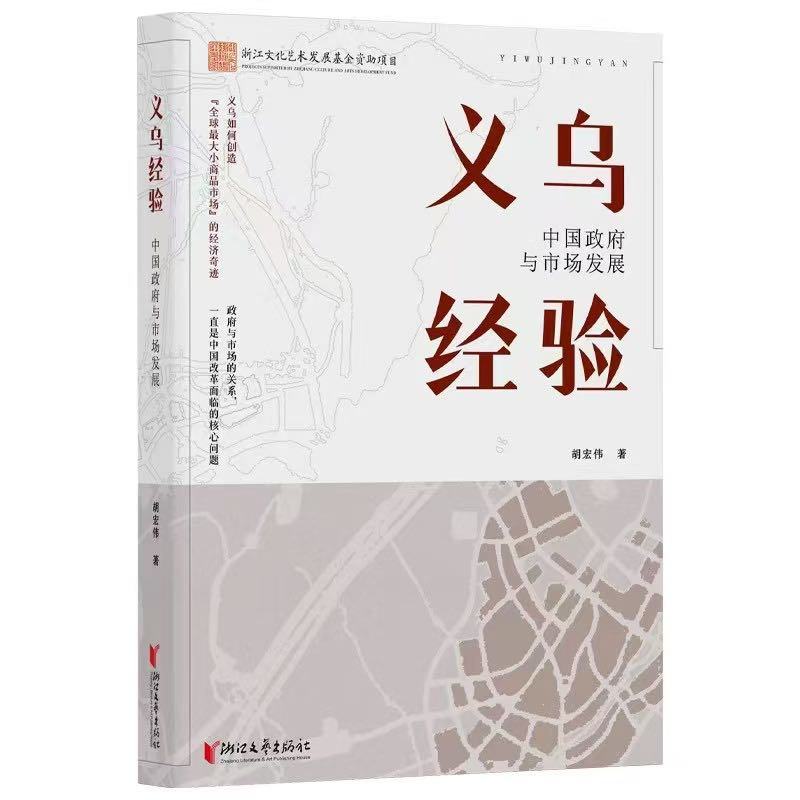
赶上一个好时代、选择了一个好职业、去了一个好平台……这三个“好”,是胡宏伟对此前职业生涯的总结。
1986年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胡宏伟作为第一届优秀毕业生,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成为一名采访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记者。后来引发他浓厚研究兴趣、因改革而兴的温州,就是他成为记者后第一个高度聚焦的采访地点。
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胡宏伟觉得年轻时的选择无比正确,“当时国家的伟大变革刚刚启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让我感到极其幸运。浙江是中国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省份,新华社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就,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这给我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在职业生涯里持续自我激励,一路坚持到现在。”
“坚持”二字,是他在对话中反复强调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这涉及到个人动力的来源是什么。我认为个人化的动力离不开时代的需求和机遇,当年,关系到这个国家命运的重大且方向性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春意萌动,没有任何事情比作为一个参与者去追踪、记录甚至推动社会发展,更值得我投身其中。”
与时代的共鸣成就了胡宏伟的写作,他感谢时代给予的平台,也相信没有愧对它。
胡宏伟想起了鲁冠球说过的一句话——“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只有这样才能够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这个时代。在他眼中,这是这位从田野走向世界的引领者一生中最精彩的一句话,“做人,最重要的不在于按世俗的眼光判断自己是否成功,而在于所做的事是不是符合你的自我价值观,以及这件事对他人、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这种理念,是胡宏伟选择媒体职业的初心,也是他近40年始终将笔尖对准浙江的原因。“今天,我的书仍然是媒体人写作的升级,我也一如既往保持以记者心态写作。这种坚持最终会有收获,这种收获又会反过来激励我,给我正向的反馈。”

2001年和吴晓波合著《温州悬念》,是胡宏伟书籍写作生涯的开端。“应该说这本书起点很高。当年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异端崛起’,在全国反响极大,迄今写温州的专著据说就有850多种,而《温州悬念》被视作其中的代表作品。”
从此,胡宏伟开始在浙江打下洞察中国的“深井”,完成从记者向学者的转型——
2008年《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出版,全书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以浙江实践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艰难而华彩的历史。
2018年《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问世,系统总结浙江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经验。
……
如果说《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奠定了胡宏伟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地位,确立了他此后十几年的研究方向;《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则标志着胡宏伟思维方法及风格基本定型。这两本书与《温州悬念》一起,构成了胡宏伟研究浙江改革开放历程最为经典的“浙江三部曲”。
2001年至今,他还陆续写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启发性的书籍,比如《非常营销——娃哈哈:中国最成功的实战教案》《温州炒房团》《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等。
所有作品里,唯一让胡宏伟不太满意的就是《温州炒房团》,他鲜少向外界提起这本书,“当时我好像又回到了媒体人的写作惯性,这本书没有留下很深厚的东西,更像单篇的深度报道,所以并不成功。”
这种反思,也体现了胡宏伟对自己的高要求,在他眼中,好的研究者应该“上接天,下接地”。“所谓‘上接天’,就是要有在3万英尺之上俯瞰世界的眼光,因为我曾是立足于国家级平台的媒体人,应具备很大的视野、更深邃的发现力,在写作中展现一种宝贵的历史纵深感;所谓‘下接地’,就是拒绝‘坐而论道’,要像农民一样去嗅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从社会底层,从义乌这样的局部样本出发,回答一些宏大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种思维,他笑称,自己从“短跑选手”变成了“中长跑选手”,不再局限于客观现象,而是把若干个客观事物联系起来,根据理论积淀进行逻辑推理和知识整合,最后得出结论。“以深度思考为人生维度,只要你能持久,这条路上没有竞争者。这就像人生的马拉松,可能跑着跑着就成了唯一,和《阿甘正传》里的主角阿甘一样。”
谈及思想的提升,胡宏伟还提到了一个词——“长考”
他认为,书籍写作的意义在于“长考”。长周期的资料梳理、伏案写作,一定会带来最系统、最深刻的思考,在因技术而变异的碎片化时代,这一能力将是长期主义者的生存利器,“文字是传导思想最有力量的工具,也是最笨、最有效的思维方式。写一本书要经历极长的周期,而且写之前必须阅读大量书籍、文献。我阅读量最大的一次,其实是写《鲁冠球:一位中国农民、改革者、企业家的成长史》的时候,当时大概看了550万字,把他生前有价值的资料全部读完,这样才能找到最能体现人物特质的语言、细节。我觉得,‘长考’会让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远超他人,你就永远不会有职业焦虑感。因为一生都在跑思想的马拉松,所以你的职业生涯会和你的生命一样长。”

不重复他人,是胡宏伟一直以来秉持的理念。
1995年,作为新华社农村记者的胡宏伟来到义乌,采访第一届义乌小商品博览会,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义乌。此后多年,他又多次前往义乌采访,却没想过写一本和它相关的作品。
“我当时感觉,义乌缺乏花大力气去写作的必要性。”胡宏伟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认为“义乌经验”是“温州模式”的延续和变种,“什么是‘温州模式’?我认为就是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以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激活千百万人的创造力。在这方面,义乌似乎没有超越温州。”
要书写义乌,就必须找出义乌区别于温州的东西。近十年时间里,胡宏伟无数次深入义乌调研,无数次翻看与义乌有关的资料,最终找到了一个答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这一点,义乌做得比温州好。放眼望全中国,区域经济变革生长的‘常青树’寥寥可数。以深圳为例,深圳是在中央推动下发展的,义乌经验却是完全草根的,难度更大,要想几十年引领时代,它背后一定有本质性的东西。”
这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政府行为。
什么是“好的”政府行为?“好的”政府行为为什么没有凌驾于市场之上,阻碍市场的活力,反而推动了市场的发展?“这不仅是义乌面对的问题,也是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面对的问题。”胡宏伟说,正确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义乌市场40余年活力勃发的核心要素,也是他最终决定花费一年多时间撰写《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的原因。
这也意味着他以一种兴奋的写作状态进入了一种更理性、更深刻的思考状态,“写《温州悬念》时,中国改革正处于一种狂飙突进的发展期,还没来得及沉淀,讲故事的文本更多;相较之下,《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更为学术化,没有采用媒体人最擅长的叙事性手法,而是以课题报告的理论逻辑为基本内核,系统呈现义乌发展壮大的底层经脉。”
全书由两部分构成,在样本观察部分,胡宏伟以历史为横轴、以地理为纵轴,搭建起观察世界的坐标、纬度,“人的活动、时代的发展都建立在这个坐标上,从这里起步,后顾与前瞻,才能跳出小商品市场的狭小半径,从中国及中国式市场经济宏观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义乌现象。”
为了全方位观察、记录义乌市场背后的政府行为,他又设置了“人物口述史”部分,采访政府决策者、市场建设者、市场主体和义乌现象的研究者,多视角呈现义乌贯穿40余年市场成长史背后每一个重要节点时刻的故事、场景及历史意义。
“完成这本书后,我好像翻越了一座中国改革史的大山。”他说,有关中国改革的理论论述数不胜数,就像山峰林立,但中间有一座珠穆朗玛峰,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我翻越得很累,但伫立于山顶眺望时真的有一种欣慰感。虽然探寻与发现还要继续,但我找到了观察中国改革的正确方位,这是我最开心、最幸运的一点。”

潮新闻:《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中的人物口述史访谈大多发生于2024年上半年,采访对象都是义乌市场的亲历者,这些采访对象是如何从茫茫人海中圈定的?
胡宏伟:虽然我的写作和人物采访集中在2024年,但《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其实是我长期积累的结果,前期准备就有三十年。从1995年第一届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开始,我就开始关注义乌。从2016年到撰写这本书之前,我就带队写过与义乌相关的三组报道,其中一组有八篇稿子,五万多字。
因为希望从多角度回答和记录义乌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我对口述史采访对象的选定都是从书稿的需求出发的。我一共选择了四类人物,时间轴上横跨43年。第一类人物是政府决策者,如谢高华、黄志平、王健;第二类人物是市场建设者,他们其实是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义乌工商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如何樟兴、陈勇、赵文阁;第三类人物是市场主体,里面有个体户也有企业家,他们是义乌市场变化发展的真实感受者,如何海美、郑期中、楼仲平、刘文高、冯旭斌;第四类人物是义乌经验的研究者,如冯志来、杨守春、张年忠、陆立军。
《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序言,包括世界、中国、义乌和开放式悬念四个方面,我认为序言是一本书的总纲和灵魂;第二部分是关于义乌的学术性深度调查,这部分中对商帮文化优势论、地理区位优势论和改革先发优势论等内容的概括分析都是我独有的观点;第三部分是十五位人物的口述史。这本书最初是源于义乌地方政府委托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的一个重大课题报告,我是课题牵头人。由于我个人的精力有限,因此口述史部分我选择了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际合作,十多位同学共同参与。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我一对一地进行了全程指导,但是其中一些人物的采访我没有亲临现场,也是一大遗憾。
潮新闻:从前期图书策划、中期采访到后期书稿交出,期间您和课题组有没有遇到什么困惑、难题,或者有没有经历比较难忘的事?
胡宏伟:这期间,让我最难忘的是一些采访者的离去。其中有一位采访者孙樟宝,他是义乌市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筹建时的工商所书记。我们已经和他约好了采访时间,可惜还没来得及见面就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这让我们失去了最有价值的采访素材,也让我有了一种特别的紧迫感,感觉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理论总结要有改革实践和人物故事作为基础和支撑,人物一旦离开了,就永远无从追溯。
潮新闻:从义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到今年杭州科创热潮,浙江地方政府做对了什么?从政府行为的视角观察,浙江在营造良好政商关系方面有何突出优势?
胡宏伟:浙江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它只有10.5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域面积倒数第四的省份;浙江也不是中国GDP最高的省,在全国的GDP排名第四。浙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是中国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省份,培育了市场经济最好的基因和土壤。同时,浙江的发展路径十分多元化,它走的是“八仙过海、因地制宜”的探索之路——温州最早探索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在温州模式的基础上,义乌重点探索了如何尊重市场、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杭州则是在尊重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很好地定位了政府行为。
当下浙江地方政府的定位可以总结为有限、有为、有效,即政府不是全能政府,没有无限的权力,但政府也不能无所作为,而应该给全社会提供高效的服务。关于营商环境,杭州的政府行为最典型的特征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各地政府往往重视“有求必应”,而杭州的突出优势就在于守好“无事不扰”的边界,非常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学习。
潮新闻:去年12月,义乌开启新一轮国际贸易的改革进程,在“买全球”上加码发力。你觉得这会给义乌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胡宏伟:以2023年为例,义乌的出口总额有5005.7亿元,但是进口总额只有654.8亿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义乌是从“卖全国”到“卖世界”,但是在如何“买世界”方面做的是不够的,出得多、进得少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不平衡。义乌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市场,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国贸改革、拉动双向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义乌可能会遇到很多瓶颈,更需要有良好的政府行为来赋予市场活力,就像“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潮新闻:您的下一本著作会把视角转向浙江其他地区吗?写作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胡宏伟: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仍然是中国当下尚待破解的命题,也是世界性的命题。义乌虽然不大,但义乌承载的使命无比大,在看得见的未来,义乌一定值得我继续追踪。我曾经说过,我对浙江区域经济的长期追踪也许已经到了画句号的时候,但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新传奇总是让我欲罢不能。
其实写作《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时,我同时在写一本关于圆通速递的书。浙江最厉害的就是流动性,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宁波舟山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全世界最大的线上市场阿里巴巴,浙江人是走遍中国最多的中国人。而不应该被忽视的还有,浙江一个小县桐庐创造了世界性最大的快递产业集群。这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进化最快的产业——包括人的进化,作为其中最优秀的经典案例圆通速递,无疑是洞察和解读这一现象的最佳窗口。
也许,我还会写一本关于杭州的书。近期的杭州科创热潮引发广泛关注,大家都在追问为什么是杭州?但我不会止于当下,我会追溯到将近一千年前的南宋,南宋定都于杭州,奠定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江南时代的到来;以及数百年以降明清、民国时期这一区域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再到近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又引领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想从这样的地理、历史的年轮和脉络来解读杭州。这本书将和《温州悬念》《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起,构成我研究浙江区域经济市县样本的新三部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