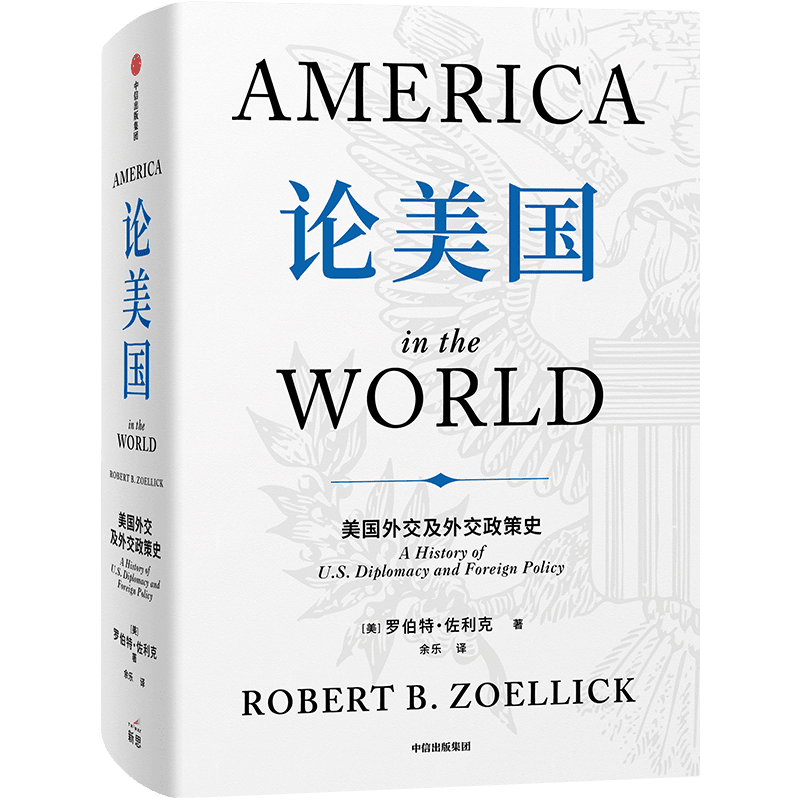本文摘编整理自《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作者:罗伯特·佐利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61—1963年的柏林危机
从1961年到1963年,柏林危机成了肯尼迪总统工作中的头等大事。这场危机考验了他,也塑造了他。柏林危机——后来演变为古巴导弹危机——是核大国之间第一次试图用直白的战争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赫鲁晓夫挑选柏林这个地方来展示核武库以威胁西方。肯尼迪真的很惧怕核战争的危险。长期担任肯尼迪助手的肯尼斯・奥唐奈尔(KennethO’Donnell)后来写道,肯尼迪感觉自己被柏林“困住”了。奥唐奈尔发现,在白宫内部的会议上,肯尼迪在他放在内阁桌子上的一个黄色便签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柏林”这个词。
肯尼迪和他的团队开局并不理想。他们最开始的关注点是莫斯科而不是德国。吸取了1914年的“教训”之后,这些“新边疆主义者”非常担心对局势的错判会升级为核大战。美国的盟友、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也持这样的观点。在经历过两次与德国的世界大战之后,英美两国都在问自己:为了一个被苏联包围的前敌国首都,是否值得让自己的国家承受核毁灭的风险?
古巴导弹危机
(1952年,编者注)10月,柏林危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加勒比海——来到了最紧迫的时刻。有一段时期,历史学家们把古巴导弹危机当成一个单独的事件来研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搞定柏林问题是赫鲁晓夫把中程核导弹部署在古巴的重要目的,甚至是首要目的。苏联的外交行动表明,美国需要铭记自己传统上的大陆安全目标,包括注意这个国家南方侧翼的安全,并认识到北美和全球权力映射之间的新关系。
赫鲁晓夫计划先把导弹在古巴安装好,然后于1962年11月前往联合国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想把他在联合国提出的柏林问题解决计划作为一个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升级的“妥协”方案。苏联人不需要用核导弹去保卫古巴。他们的目的是威胁美国,并迫使肯尼迪让步。为了准备在秋季摊牌,苏联人建造了横跨东德的石油管道,并在东西德边境上驻扎了大量部队。他们没有为军队的行动做任何伪装。这种大规模的军力展示会加强威慑力,迫使德国人和其他西方盟国让步。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马上识相起来”。
这一次,肯尼迪对战略实力的对比有了新的了解。他曾在1960年说过美国的导弹水平“比不上苏联”。到了1962年10月,这位总统已经十分确定,双方的导弹确实有差距,但美国才是大大领先的那一方。卫星图像和间谍,再加上U-2侦察机从空中拍摄的照片都说明,美国在洲际导弹方面的领先优势巨大。苏联人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数量比美国人之前估计的要少很多,而且苏联已经部署了的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甚至还存在一些问题。比数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显示,美国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少是不亚于“苏联的第一次打击能力”。1962年10月,总统授权国防部副部长发表演说,公布美国的导弹、战略轰炸机和导弹潜艇的数量——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就能表明,美国与苏联相比处于战略优势地位。为了保证苏联政府能得到消息,美国把数字和照片都通报给了北约各成员国,这样苏联情报机构就肯定会报告给中央。
10月中旬,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古巴的苏联核导弹,并认定苏联政府正试图扭转战略平衡态势。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显示,如果苏联人成功部署这些核武器,苏联政府“可能就会认为,其在柏林等其他冲突场合威逼美国的风险将会降低”。几十年后,梅和泽利科在研究了苏联档案后认为,虽然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非常重视古巴,但他们在讨论导弹部署的时候却极少提到其威慑美国以使其不敢入侵古巴的作用。他们谈论战略核问题的时间要多得多。柏林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在讨论中不断被提起”。
古巴与柏林
1958年和1961年,赫鲁晓夫的两次最后通牒最终都不了了之。东德人希望苏联政府能再强硬一些。1962年3月,苏联新任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Dobrynin)在前往华盛顿就职前见到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其他所有话题。”多勃雷宁回忆道。赫鲁晓夫声称美国人在核威胁的问题上“格外傲慢”,并表示“现在是时候把他们的长臂剪短了”。梅和泽利科在他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著作结尾处写道:“我们相信,赫鲁晓夫1962年时的柏林问题战略的关键之处,就是古巴的导弹。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和伦敦的专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肯尼迪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古巴导弹和柏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第一次在演讲中提醒美国公众注意苏联导弹的时候就警告苏联政府,不要对柏林采取不友好的行动。10月19日,肯尼迪对参谋长联合会议成员们说,美国如果进攻古巴,就会给苏联一个接管西柏林的借口。他强调:“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古巴,也是柏林。而且,在我们认识到柏林对欧洲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的盟友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两难选择。”按照劳伦斯・弗里德曼的说法,肯尼迪“把古巴看成柏林危机的延伸;他无论对古巴采取什么行动,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招致苏联对柏林采取行动”。柏林人很快就明白了古巴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赞美肯尼迪,说他们知道“肯尼迪正在像为自己战斗一样为他们而战斗”。
关于肯尼迪是如何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迫使赫鲁晓夫把导弹撤走的,历史记录能充分地说明问题。在一个美国占据军事优势的环境里,苏联的行为显得太得寸进尺,而肯尼迪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提出了强硬的要求,并精心计划了每一步的行动——其背后依靠的是充足的军事实力、与盟友的合作,以及公众的支持一一每一步都把重心放在他的核心目标上。他给了赫鲁晓夫避免冲突升级——尤其是升级到使用核武器——的时间和机会,同时又“保持了热度”。“检疫隔离区”的设置显示了美国人的行动决心,同时又给了他的对手一个停下来权衡后果的机会。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留了一条退路,并使用私人渠道来提供让步。苏联的一位外交部副部长曾提议进攻柏林以转移矛盾焦点,但赫鲁晓夫没有选择在柏林摊牌以加剧古巴导弹危机造成的风险。肯尼迪要求,如果苏联开始封锁柏林,克莱将军就要立即前去应对。
随后,苏联人从古巴撤退,从而改变了柏林危机的进程。美国及其盟友在苏联咄咄逼人的举动面前给出了强硬的回应,显示出了力量——这也是克莱将军曾经试图在柏林使用的方法。赫鲁晓夫的咆哮现在已经不那么管用了。苏联对柏林的骚扰仍在继续,但其行动变得更加小心,也没有那么自信了。
冷战缓和
肯尼迪这次终于展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现在他可以按照自己最青睐的方式去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了,尤其是要降低核战争的风险。1963年6月,美苏同意开通一条热线电话,以供在紧急情况下建立快速联系。1963年8月,两国又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TestBanTreaty),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爆炸。这一条约的军事意义并不重大,但这是美苏第一次共同做出军控的努力。
一些研究冷战的学者认为,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是东西方关系发展路径上的转折点。从1961年到1963年的经验中产生的决心、威慑和议论最终导致了发生于1989年到1990年的剧变。柏林、德国和欧洲的未来将由下一代人在下一个时代决定。西方同盟的边界线将会是柏林墙——而不是易北河、莱茵河或英吉利海峡。在整个世界上,柏林和柏林人都将成为一个象征。
让我们再回到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大学发表了第二次演讲。这是一次更为冷静的政策宣讲。他强调了谈判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德国统一,但也提醒人们要有耐心,因为统一进程“不会快,也不会容易”,而且其他国家“需要比今天更清晰地看到它们自己的真实利益”。肯尼迪的这番话将在27年后得到验证。
评价肯尼迪外交:德国、积极行动主义和危机管理
肯尼迪的冷战外交故事给了我们三点思考。第一点,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最开始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政府身上,而马歇尔和艾奇逊——尤其是后者——都把美国的盟国作为首要的战略重点。美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意见和愿望的支持下,建造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同盟,并让成员国结成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伙伴关系。那两位早期的冷战斗士得出的结论是,在此之后,与苏联人的谈判要么就不会有成果,要么就根本无法进行。
由于缺乏耐心,肯尼迪曾主动和赫鲁晓夫谈条件。他一开始把柏林视为一个人质——它的存在使任何试图缓解核紧张气氛的外交倡议都无法奏效。与他相反,艾奇逊和克莱认为,只有坚定地支持柏林和西德才能保卫跨大西洋同盟,而这个同盟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实力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尼迪比他的幕僚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柏林的价值——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西方世界桥头堡,暴露出苏联共产主义的缺点。柏林提醒着每一个人,美国有意愿为欧洲的安全站岗。这座分裂的城市还创造了美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情感上和实际上的纽带,而这个欧洲中部的国家将决定冷战的命运。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冷战接近1989年到1990年的终点之时,这一战略视角的分歧又重新出现了。我会在第17章讲到,当时的总统老布什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强力联手,让一个民主的德国完成了和平统一并加入了北约和当时的欧共体。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其中部分原因是她不想得罪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有些惧怕德国统一后的实力。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Mitterrand)起初也不喜欢德国统一的前景。德国统一之后,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俄罗斯事务顾问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对老布什和他的国务卿贝克提出批评,说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支持他们的保守派同党赫尔穆特·科尔,因此站在了一个重要盟友的一边”。塔尔博特认为“快速统一所造成的干扰性后果”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在那个时候,塔尔博特认为帮助戈尔巴乔夫要比信守同盟承诺和保卫德国的制度,并让德国成为泛大西洋安全系统中的一个合作伙伴更为重要。
美国永远都不应该认为自己和德国的伙伴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考虑到德国的面积、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这个国家将会像过去一样,在欧洲的未来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美国在冷战的几十年中,尤其是成功的尾声阶段中赢得了和德国的特殊关系。如果美国政府无视持续破坏这种关系的后果,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肯尼迪——与几十年后的布什和贝克一样——也认识到了柏林人和德国人对美国外交的重要意义。柏林人不想成为强势政治人物手中的棋子。从1948年到1949年,以及1961年到1962年,柏林人都站在西方世界的前线上抵挡住了外部威胁。美国如果放弃他们,那就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1989年和1990年,柏林人和其他两德人民一起发动了通过外交途径完成统一的进程。美国和联邦德国利用人民的热情促成了民主的统一,而不是让两个不同体制的国家结合在一起。
第二点思考是关于肯尼迪的积极行动主义的。肯尼迪渴望成为“进攻的一方”,以便抢占辩论的主动权,并改变战略判断的结果。对于这一点,我是很敬佩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僚机构,包括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都倾向于只是被动地做出反应。领导人总是难以改变现状或重新思考已形成惯例的行为方式。艾奇逊已经通过定义政策规划的作用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肯尼迪能够小心地争取美国公众的支持,这展示了他作为民主领袖的技巧。
即便如此,肯尼迪还是认识到了,冲动的积极行动主义或是欠思考的行动都是危险的。要想让积极行动主义有效果,就要先研究一个问题的历史,对设想提出挑战,并考虑第一步行动之后每一步的计划。这样有助于理解其他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与对手较量的时候,积极行动者需要知道对方的经验、思维方式甚至政治文化。肯尼迪是在总统任期内边学习边成长的——从一开始的草率行动到后来的谨慎权衡各种选项。
肯尼迪能够运用他活跃的思维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想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也考虑了如何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让赫鲁晓夫做出让步。在国际关系中,两个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长期共存,所以高层外交和谈判往往既需要实现一些目标,也应估计到未来还需要更多轮的交涉。美国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彻底摧毁一个对手,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例如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后来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美国官员也必须密切关注战火熄灭后新崛起的力量。
作为一个积极的谈判者,肯尼迪必须学会什么时候要隐忍不发。由于他愿意谈判——且急切地希望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肯尼迪还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坚守强硬的立场,且有拂袖而去的勇气。特别是在那些权力压倒理性的地区——最显著的就是中东地区——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是需要展示力量的。实用主义者也会寻求解决方案,但有的时候时机并未成熟。这个时候就需要后退一步,考虑如何让形势和环境发生变化——无论是权力还是认知。
第三点,肯尼迪的风格太容易引发危机。他那聪明、自信且精力充沛的团队沉迷于危机管理,甚至是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高潮过后,肯尼迪团队给《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发去了一篇自吹自擂的(且不准确的)当事者自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这篇文章里的形象格外好。他对他们这种新的外交风格进行了总结。“再也没有战略这种东西了,”这位手握重权的国防部部长说,“只有危机管理。”
管理者如果眼里只有危机,就可能考虑不到那些关系到长期战略利益的紧要问题。1963年11月21日,也就是肯尼迪前往达拉斯进行竞选活动的前一天晚上,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迈克尔·福里斯特尔(MichaelForrestal)谈到了越南问题。后者即将前往柬埔寨。肯尼迪看起来很累,并且想要沉思一会儿。
“你知道,等你回来以后,我想让你来找我,”肯尼迪对福里斯特尔说,“因为我们必须开始计划我们在南越的下一步行动了。我想要开始一次全面且非常深刻的回顾,看看我们是怎么进入这个国家的,以及我们当时以为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又认为自己能做什么。我甚至还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那里。”这位行动主义者,坚信自己“能做到”的总统开始成熟了,成了一个擅于分析且更有反思精神的政治家。对于肯尼迪和越南来说,时间已经不够了。第二天晚上福里斯特尔刚抵达西贡(胡志明市的旧称),就听到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HarveyOswald)刺杀肯尼迪的消息。肯尼迪没能解决越南危机就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