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往往只能观察到幼儿的行为,却不了解其背后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经常容易根据成人思维推断,给幼儿的行为简单粗暴地贴上各种道德标签:哭闹是任性,不肯分享是自私,依恋妈妈是软弱……殊不知幼儿有独特的大脑发育程度,成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可能犹如惊涛骇浪。这一阶段面对的人生挑战远比成人以为的多:从家庭过渡到幼儿园的分离焦虑,“二胎”到来的冲击,意识到死亡……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建立对世界的信任感、依恋关系与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成人需要放下成见,才能体会幼儿成长过程中的挣扎、爱恨、进退与不屈的努力。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幼儿期的生命经验将伴随人的一生,为后来的亲密关系奠定基础。精神分析流派发展出一套幼儿观察方法:观察者被要求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观察幼儿在生活中呈现出的感受、想法、幻想和愿望,这种训练培养了观察者的敏感度,有助于促进其对人类内在世界的投射、移情、反移情等现象的了解。同时,观察者作为一位旁观的陪伴者也为幼儿及其家庭创造了一个空间,对幼儿及其家庭产生了疗愈的效果。
《陪伴也是一种疗愈:从家庭到现实世界的幼儿观察》是一本解读幼儿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的科普著作,由精神分析重镇塔维斯托克幼儿观察研讨班的观察材料汇编而成,记录了18个幼儿的成长故事。从观察者对于幼儿细致而生动的观察材料中,读者可以学会解读孩子各种各样的信号,理解孩子的情绪与想法。也可以在观察幼儿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追溯自己的成长和被抚养的经历,从而看见曾经的创伤,接纳和疗愈自己。
本文摘编自《陪伴也是一种疗愈》,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节,注释见原书,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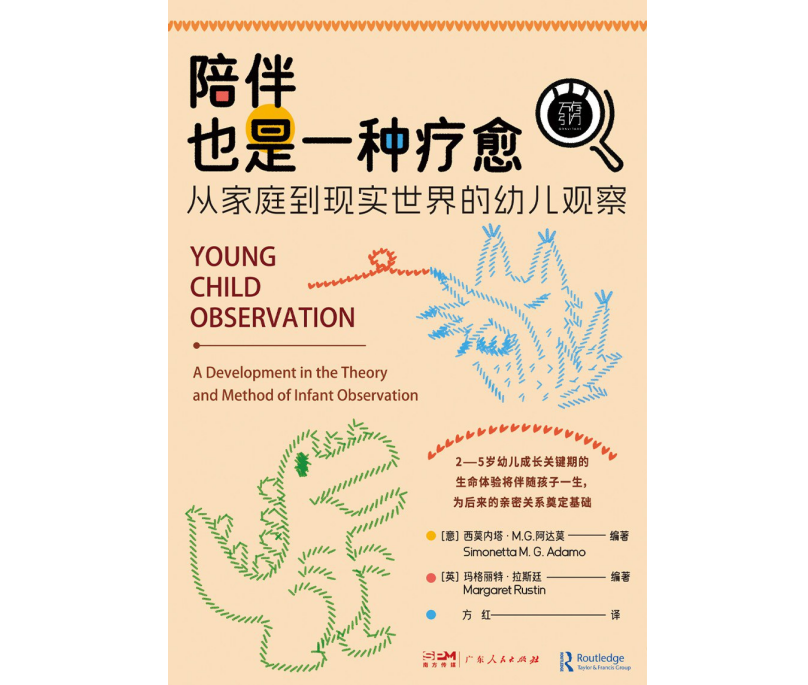
《陪伴也是一种疗愈:从家庭到现实世界的幼儿观察》,[意]西莫内塔·M.G.阿达莫[英]玛格丽特·拉斯廷编著,方红译,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人生最初的分离
这篇讲稿对幼儿在面对人生第一次重大的分离(离开母亲,离开家)时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清晰的、富有感召力的描述。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学习、结婚、生子、搬新家——所有这些事件通常都会唤起我们的希望:增加知识、快乐和成就感。正是这些充满希望的预期,让我们在一生中不断地去寻求新的体验。幼儿开始上幼儿园时也是充满希望的,预期会找到有趣的玩具,学会做他所羡慕的其他年长儿童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遇到可以成为朋友的其他儿童。除非之前有过非常失望的体验,否则,我们在一生中都会不断希望:某件新的事件会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想要取得的成就。
我们可能会赋予它希望,事实上还可能会将它理想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心怀恐惧,不知道这种未知的新情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我们可能会害怕新的环境或新接触的人会很恐怖;新接触的儿童会不好应对、不可爱;新的老师会很严厉、爱惩罚人、过于苛刻。我们可能会害怕自己没有生理或心理方面的能力来应对新的挑战;我们可能在新的环境中不知所措,由于新的想法而感到困惑不安。我们可能会害怕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害怕他人认为我们愚蠢、无知、没有才能;我们可能害怕自己产生不胜任感,害怕被人嘲笑、讨厌、排斥。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情境,所有这些想法都很可能会出现。
我们通常不会说自己有这样一些不安的情绪。我们可能会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应该再有这些恐惧,可能认为感到恐惧是幼稚的表现。但这么想并不对,因为这些恐惧情绪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儿童早期。对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我们从出生开始的所有经验都会留下记忆痕迹,而且,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情绪会始终保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生命早期的经验不会在意识层面上被记住,但通常会以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Klein,1957)所说的“感受的记忆”的形式重现—也就是说,会以身体的形式、心理状态和幻想的形式重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当前的情境在某个方面与早期的情境相类似,这些记忆就会再次被唤起。因此,我们在婴儿期和儿童期体验过的情感状态会一直保留在我们内心,它们绝不会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而消失。
与我们自己小时候的这些方面保持联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我们自己及他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幼稚的恐惧和欲望。如果我们想要正确理解幼儿的内心变化,那么,这样一种理解就非常关键。大多数两三岁的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想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当在陌生的环境中迷路时,他们无法找人帮忙找到回家的路;他们甚至不知道家在哪里。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通过行为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纪录片《北鼻异想世界》(TheWonderfulWorldofBabies,2018)画面。
罗伯特(Robert)两岁半了,只要一想到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他就非常兴奋。他喜欢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而且有人曾告诉过他,幼儿园有很多新玩具可以玩。当他和妈妈一起到了幼儿园,一开始,他寸步不离地待在妈妈身边,不过,过了一会儿,他便开始走到离妈妈稍远一点的地方,并在一张纸上画起了各种颜色的图形。一小时后,妈妈觉得他已经开始开心地安定下来,于是站起来准备离开。罗伯特立马冲到了妈妈身边,开始大声哭了起来,不过,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妈妈还是出去了,她走的时候对罗伯特说,她买完东西就回来。一小时后,妈妈打电话到幼儿园,老师告诉她,罗伯特很好,已经不哭了。
第二天,罗伯特到幼儿园一会儿便开始开心地画起了画,于是妈妈就离开了,不过,当她后来打电话的时候,听到孩子在哭。第三天早上,罗伯特不愿意离开家去幼儿园;他一会儿要再喝一杯饮料,一会儿又再要一块饼干,一会儿要妈妈再抱一下,一会儿又要点别的什么。到了周末,他发起了低烧,总体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当父母带他到公园去散步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到他们前面。当看到奶奶时,他没有像平常一样热情地向她问候,当他的父母去小卖部买饮料时,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开心地跟奶奶待在一起,而是不停地把她拉向父母走出去的方向,还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去哪里了?我要找妈妈。”
到了周一的早上,他不愿意穿衣服,一路哭着到了幼儿园。当妈妈在老师的建议之下打算离开幼儿园时,他大声地尖叫了起来。老师说,“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脾气不好”,但是因为罗伯特整个周末都显得很不安,而且这时候看起来又非常害怕且无法安定下来,妈妈最终还是把他带回了家。妈妈说:“除了有时候有陌生人来到家里时,罗伯特会有些害怕,在其他时候,我从来没见过罗伯特这个样子。”当妈妈后来回头去跟班主任老师讲话时,罗伯特紧紧地抱着妈妈,哭得非常大声,以至于这些大人几乎无法进行交谈。这位老师告诉妈妈,说她对罗伯特过于保护了,而这就是罗伯特现在无法与她分开的原因。
罗伯特的父母承认老师说的话可能有点道理,但却因为受到了指责而感到有些受伤。于是,他们反过来批评幼儿园老师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帮助。这样的相互指责并不少见,但一点作用都没有。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理解这种情境。我们可以从孩子的痛苦中得出些什么结论呢?我们怎样才能让他更能接受入园这件事情呢?罗伯特的母亲最后决定四个月以后再把孩子送回幼儿园,因为孩子现在太小了还不适合上幼儿园。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就真的会有很大不同吗?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一位幼儿发现自己被妈妈留在了陌生的环境中,跟一群自己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时,他会产生怎样的感受?要理解这种痛苦情绪的深刻性,我们就必须将关注的焦点指向生命之初,指向出生这个事件。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点:出生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种突然的结束。婴儿失去了他已经生活了九个月的世界。当他离开母亲的身体便再也回不去了,他所生活的液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可以自动地得到喂养,被包容在温暖的子宫的保护层中)变成了空气环境,他有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他被暴露在了冰冷的环境中,被刺眼的光线和刺耳的声音冲击着。子宫内的生活可能是限制性的,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无边无界的空间之中。而且,人类新生儿不具备移动能力,不能自由移动自己的身体,不能独立获取食物、温暖和庇护,不能保护自己免于危险。这种极端的无助状态使他感到非常恐惧,害怕摔倒、死亡。
法国医生勒博耶(Leboyer,1975)证明,在婴儿出生的过程中和出生后,通过最大可能地模拟子宫内的环境(这样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婴儿体验的连续性),可以减轻进入新世界这种重大创伤性体验的影响。这包括将光线调暗、在剪断脐带前把婴儿放到妈妈的肚子上、让婴儿尽可能快速地吮吸到乳房、把婴儿泡在温水中、温柔地按摩婴儿的身体等。在做完这些之后,婴儿的哭声会很快平息,紧绷的身体也会放松下来,开始探索周边的世界。
婴儿观察已经表明,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周,只有当与胎盘的联结被嘴巴可以随时获得的乳头所替代,子宫壁的边界对其身体的包容被一种紧紧包容、包裹的感觉代替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当与乳房相联结,被母亲安全地抱在怀里且得到母亲充满爱意的关注时,婴儿会感到无比幸福,但是,当他感到被切断了与生命之源的联结、没有被母亲抱持时,这种幸福感很快就会让位于大声尖叫和混乱的动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分离恐惧的缩影。威尔弗雷德·比昂将这种恐惧的状态称作灾难性焦虑(catastrophicanxiety)。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面临改变,这种焦虑就可能会压垮我们。显然,我们离开家的距离越远,就越会感到恐惧,就越会感觉到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我们害怕再次体验到像婴儿时期那样的无助和恐惧。我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害怕让我们自生自灭,在一生中所有涉及重大改变的阶段,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体验的影子。

纪录片《北鼻异想世界》(TheWonderfulWorldofBabies,2018)画面。
再来看看儿童的情况:儿童的年纪越小,事实上他就会越无助,因此,当面对新的和不熟悉的环境时,他可能体验到的焦虑感就会越强烈。应对焦虑的方式往往也与他在婴儿时期被抚慰的方式相一致。例如,我们看到罗伯特害怕被母亲丢下,紧紧地抱住她的身体不放,他不停地要吃的和喝的,一再要求母亲抱着他,紧紧地依附于他已经在生活中了解到的维持生命和安全所必需的所有这些重要联结。而且,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体验的连续性,可以帮助新生儿对完全未知的外部世界产生兴趣,因此,母亲存在的连续性,以及等到幼儿已经熟悉老师的时候再逐渐把他交给老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幼儿从家到幼儿园环境的过渡。在幼儿园里像噪声水平这样的因素,对于来自一个安静家庭的孩子来说可能声音太大,从而让他感到不安,有一个孩子就曾告诉我,罗伯特曾抱怨他的耳朵受伤了,他说:“我听不见音乐声了。太吵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审视了突然结束的余留影响,这种突然的结束是出生的一部分。不过,来到幼儿园的幼儿所体验到的极端分离当然也很少。每一次喂奶的结束、每一次被放到他自己的小床上、每一次妈妈走出房间,对婴儿来说都是一次分离,这会让婴儿意识到他和母亲不是一体的,他必须与母亲分离。正如温尼科特(Winnicott,1964)所指出的,“要一点点地慢慢让婴儿认识这个世界,否则,他会认为分离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母婴观察表明,只有多次经历这样的体验,即当婴儿害怕、饥饿或疼痛的时候,母亲都会及时出现给婴儿爱的关注,婴儿才会慢慢感觉到:当他需要的时候,有一个人会及时出现。在吮吸母乳的同时,他也吸收了一幅母亲照顾他的画面,并逐渐建立了一个关于母亲的心理概念:母亲是不管怎样都会爱他、安慰他并能够对他的快乐和痛苦做出反应的人。慢慢地,这些与母亲在一起的美好体验留下的记忆痕迹让他能够短时间一个人醒着躺在那里,在心里想着并重建与母亲之间快乐的感官互动。当他被放下的时候,他一开始可能会哭,不过他越来越能够唤起这种内心的画面,给自己提供一种被拥抱、被抚慰的感觉。父母要学会判断他们的孩子能够忍受哪些情况、他们可以离开孩子多久而不会让孩子陷入恐慌状态。有些父母会把孩子放到能隔绝声音的地方,这样孩子的哭声就不会干扰到他们;如果让一个婴儿过于频繁或过长时间地一个人待着,那他可能就永远都不能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建立起对可信赖的好母亲的信任。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有些父母连孩子哭一分钟都不能忍受:只要看到孩子有一丁点不安的迹象,就会把他抱起来。这种做法通常会影响幼儿获得利用自己内在资源的能力的发展,这样的幼儿会变得依赖性很强,往往依赖于母亲一直在身边给他提供帮助。我认为,罗伯特案例中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对父母而言,要发现对自己的孩子来说什么才是对的通常很难,因为在照顾婴儿,以及后来照顾幼儿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婴儿期自我被唤醒了,因此,他们往往会用婴儿期和儿童期他们自己的父母和照看者对待他们的方式做出反应。好的体验能够让婴儿带着希望去探究外在的世界。不过,虽然周围环境中的他人和事物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母亲通常始终是安全的港湾,只有当他感觉到自己可以安全地回到这个安全的港湾,他才会勇敢地探索外在的世界。
现在,让我们超越这些短暂的分离,来看看每一个婴儿在生活中都要面对的一次非常关键的结束:断奶。不管婴儿是母乳喂养还是喝奶粉,喂养的情境都为母亲和婴儿提供了亲密接触的机会。这是一种充满爱的给予和接受、抚摸和注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往往会发展出彼此之间的统一和分离、身体的亲密性和反应性。这为后来所有亲密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种最为亲密的关系的结束,对婴儿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丧失。在克莱茵看来,婴儿期处理断奶的方式,往往会决定我们后来一生中应对各种丧失的方式。
适应幼儿园生活
在考察了很多地方后,他们找到了一所幼儿园,用他们的话说,这所幼儿园“以儿童为本,而不是像其他幼儿园一样以成人为本”。但是,这是一种过度的简单化,因为如果我们希望成年人能够很好地照顾幼儿,那么就需要照顾到老师们的需要—也就是说,必须有人来帮助幼儿园的教职工减轻他们的情绪负担。不仅这群不到六岁的孩子会大吵大闹,把环境搞得一团糟,而且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还会对幼儿园教职工提出很高的情绪方面的要求。因此,教职工需要有机会定期聚集在一起,分享并讨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这样一个讨论小组或许可以帮助玛丽亚的老师缓解她所承受的痛苦,甚至很可能让她得到一些帮助,而不是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让自己感到不堪重负,以至于将情绪发泄到孩子们身上。我认为,这个案例还表明了一点:我们不仅应该注意那些大声地明确表达其不开心的儿童,还应该关注那些以安静的方式表现其痛苦的幼儿。就像罗伯特以公开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感受,但玛丽亚似乎被动地接受了被留在一个令人恐惧的情境之中的状况,而且这个情境与家中的温和氛围完全不同。

电影《再见我们的幼儿园》剧照。
有些幼儿在上幼儿园时,由于其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结束而有了心理创伤。詹姆斯(James)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父母是移民。父亲和母亲都需要出去工作才能维持生计,因此,他几乎是一下子就被放进了全日制幼儿园中。对詹姆斯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所有他曾熟悉的一切:父母、曾经照顾他的祖父母、一大家子人、整个熟悉的环境,甚至是他听得懂的语言。每天早上要去上幼儿园时,他都哭得撕心裂肺;在幼儿园,他总是紧紧抓着他从家里带来的一辆小汽车玩具不放,并经常躲在一个角落里;有时候,他会爬进一个纸板箱,在里面滚来滚去,直到筋疲力尽,然后睡着。他在午饭时间经常不吃饭,总是盯着门口看,他知道妈妈就是从那个地方消失的。幼儿园老师会把他抱起来,但很快又会把他放下,因为其他孩子也需要老师的关注。
像詹姆斯这样的孩子,除非给他们很多的个别关注,否则就会越来越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有的孩子会陷入绝望,甚至可能患上孤独症。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儿童没有能力处理其生活中的创伤性变化,但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让他们变得更为独立,这样的儿童可能会发展出坚硬的、保护性的躁狂外壳。例如曾在一些儿童之家待过的索菲(Sophie),她可以很快地跟送她到幼儿园的女士挥手告别,骑上一辆她在那里找到的自行车,在教室里疯狂地跑来跑去。当其他儿童挡在了她面前,她会一把将他们推开。当其他儿童手里拿着她想玩的玩具时,她会一把抢过来,如果他们抓着玩具不放,她就会咬他们。当其他儿童哭的时候,她会盯着他们看一会儿,然后在一旁大笑。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她身上那个较为温和、不安的部分已经去除了,她对任何让她想起自己那个脆弱自我的行为嗤之以鼻。
你可能觉得我所举的都是一些相当极端的例子。我之所以选择这么做,是因为这些例子所论证的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儿童身上,这些儿童在处理开始和结束方面存在困难,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事实上,这样一种危险始终存在,即有些儿童不能顺利完成从家到幼儿园的过渡,比如罗伯特,还有其他一些像詹姆斯这样的儿童会受到深深的伤害,承受极大的痛苦。不过,有一些儿童看起来似乎适应很快,但会变得冷漠,表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攻击性行为。我们所有人希望看到的是:儿童能够利用他们上幼儿园的经历来帮助他们扩展关系,发展技能,学会与其他幼儿分享,并喜欢上群体活动。一个幼儿能否顺利适应幼儿园生活,通常取决于以下因素:
1.幼儿的内在心理准备。正如我试图概括的,这取决于幼儿的内在安全感,而这种内在安全感发展的基础是可信赖的、相互理解但又不会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以及幼儿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挫折时内心能够保持良好体验的能力。
2.过去处理各种事件的开始和结束的方式。
3.当前处理各种事件的开始与结束的方式,这可以给幼儿提供一种连续感和安全感。
有些老师会到幼儿家里家访,在幼儿上幼儿园之前就对幼儿有了了解,并询问父母对于之前的分离幼儿都是怎样应对的。许多幼儿园都鼓励家长或幼儿非常熟悉的其他人到幼儿园陪读,直到幼儿可以完全适应幼儿园生活。就像一位老师告诉我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一个幼儿将以怎样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我一直坚持让父亲或母亲陪孩子一起待在幼儿园,直到我觉得他们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人待在幼儿园。这可能需要一到五周的时间。如果父母在那之前必须离开,我会留下他们的电话号码,一旦孩子变得不安,我就会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4.每天父母把幼儿交给老师的方式,幼儿在进入幼儿园时受到欢迎的程度,以及他与父母保持接触的程度。
5.一个新入园幼儿在融入群体之前所能获得的个别关注的量。
6.群体的大小:群体越大,幼儿越难与老师或另一个幼儿建立关联。
7.教室的大小:幼儿需要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可控的界限之内;在一个大空间里,他们会感到不知所措。
虽然以上这些是一般性的准则,但每个幼儿对于从家到幼儿园这样一种转变的确切的应对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相比于我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那些幼儿,有些幼儿的入园适应就容易多了。例如,露西(Lucy)是一个两岁八个月大的小女孩。她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小,她的父母很忙,但家人之间相亲相爱,父母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孩子经常到她家来玩。因此,她已经习惯了有他人的陪伴,与其他儿童分享她的玩具,而且必须与他们分享父母的关注。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一直渴望能够做哥哥姐姐做的事情,因此她变得非常独立。她渴望上幼儿园,当时她姐姐也还在上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老师与她父母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在露西独自一人定期上幼儿园之前的一段时间,她和她的母亲得到允许,可以每周去幼儿园一个小时。
在融入群体方面,她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一开始,到上午快结束的时候,她会非常疲惫,而下午在家里的时候,她会要求母亲给她更多的关注。有时候,当母亲不在房子里时,她会有些焦虑;而在其他时候,她会对母亲发脾气。露西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从家到幼儿园的转变也被以温和、细致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因此开始上幼儿园而导致的困扰较小。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在这些非常有利的环境中,幼儿也很可能由于自己不再是家中的小宝贝,不再能够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候让母亲只属于她一个人,而产生某种程度的焦虑和愤怒。
还有另外一种转变我也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幼儿园生活的结束和真正的学校生活的开始。如果一切顺利,幼儿园很快就会成为幼儿的另外一个家,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他觉得他会得到周围亲切的成年人的照顾,他喜欢待在那里,并且和其他幼儿成为好朋友。而离开幼儿园就意味着他要与这些他所依恋的一切分开。这样一种结束需要提前好好做一些准备,这样,由于一些重要事情的结束而产生的愤怒感以及由于分开而产生的悲伤感,才会有机会得到缓解。幼儿可能会因为其他新进幼儿园的幼儿将要取代他们的位置而产生妒忌情绪,他们可能会突然爆发出一些激烈的行为:将画撕个粉碎,破坏玩具,或者是对老师做出攻击性行为。

电影《再见我们的幼儿园》剧照。
还有一些幼儿可能会非常兴奋地不停谈论着将要上小学的事情,以至于幼儿园老师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些孩子是如此渴望离开幼儿园。这些老师通常会像卡特里娜的母亲一样,感觉遭到了这些孩子的拒绝,同时也感觉受到了伤害。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孩子只不过是在将他们觉得自己难以忍受的痛苦感受转移给老师而已,那将有助于我们忍受这样的行为:这些孩子通常会觉得幼儿园不要他们了,一群更小的幼儿将取代他们;他们会因为被抛弃而感到愤怒;他们会回避由于即将失去很多他们所深爱和依赖的东西而感到悲伤。
如果教师能够容忍这些幼儿的破坏性行为和拒绝行为,并一如既往地关爱他们,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幼儿的爱和悲伤最终都会涌现出来。就像一个小女孩在幼儿园快要毕业时告诉她母亲的:“我爱我们绿色的教室,那是我最喜欢的教室,我会想它的。”幼儿园教师可能也会觉得很难与他们所深爱的孩子们分离,而且难以哀悼他们的丧失。一位幼儿园教师提到,她就曾一直告诉她最喜欢的那个小男孩,说他只会制造垃圾,她就曾经常对他发脾气。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她知道自己在他学期结束离开幼儿园时会想他,对此,她非常愤怒,于是采取了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的方式来逃避失去他的痛苦。
像母亲一样,这样一种痛苦还会导致教师不愿意让幼儿离开,从而使得他们难以为上小学这一转变做好准备。对幼儿来说,上小学还涉及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到此时为止,他们一直是“小池塘当中的大鱼”,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大海中的一条小鱼”,周围有许多比他们年长的儿童,因此,他们感到害怕、迷茫、不知所措和无助。我知道有一些幼儿园教师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他们会带幼儿去初步参观幼儿们即将要上的小学,带他们看看教室,跟他们以后的老师和班主任讲讲话。
这样一种幼小衔接的活动非常有帮助,幼儿可以通过这种活动对小学形成一种直观形象的了解,并感觉自己在幼儿园老师和小学新老师的心里都有一席之地。成人还可以以自己为例,向幼儿说明:虽然当下的关系结束了,但大人们对他们的关爱还是有可能持续存在的。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事件的结束,那么,虽然有外在的丧失,但过去的美好体验会被幼儿用感激之心保存在记忆里,并且会成为陪伴个体终生的丰富内在宝藏的一部分。
原文作者/伊斯卡·威滕伯格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