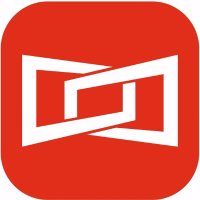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李彪
2014年前后,中国半导体行业掀起过一阵“去海外收购企业”的热潮。国内半导体产业当年正处于起步阶段,优质标的稀缺,政府出台并购政策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国内投资者“走出去”。紫光收购展讯通信与锐迪科、豪威科技从美股私有化退市后又被韦尔股份并购,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并购案。
然而十年过去,国际地缘政治已经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运行规则,跨国并购需经过重重审核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不下30万家半导体公司,而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总数已有200家左右。从2023年A股IPO上市阶段性收紧后,2024年新增半导体上市公司的数量仅有个位数,国内一、二级市场通道间积累了大量的半导体“存量资产”。
也是从去年开始,国内市场再起新一轮并购潮。与上次不同,这次并购潮的主阵地在国内市场,去年政府相继出台“国九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鼓励A股上市公司积极通过并购交易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政府也承诺以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
Wind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首次公布的半导体并购事件多达31起,其中超过半数是在9月20日并购新政出台后披露。2025年至今,与半导体产业相关的并购有近20起,有媒体报道统计“几乎每八天一个新并购”。
国内半导体投资机构元禾璞华合伙人牛俊岭是两次并购潮的亲历者。在上一次海外并购热潮时,他代表中信证券旗下金石投资作为联合投资方参与了豪威科技、澜起科技的私有化退市。元禾璞华的前身清芯华创当时是主导豪威科技和矽成半导体两起并购交易的资方,他在豪威科技交割后加入团队。
元禾璞华是由清芯华创与苏州市工业园区旗下国资机构元禾控股联合成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专门从事半导体产业链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投资。
元禾璞华创始人兼现任投委会主席陈大同是半导体领域的传奇人物,先后创办过豪威科技(后被韦尔股份并购)、展锐通信(后被紫光集团收购,与锐迪科整合成立紫光展锐)两家公司。其投资团队大多来自展讯通信、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一线半导体产业公司,机构旗下目前已管理十只基金,管理规模近两百亿元。
牛俊岭记得,2014年到2017年第一次半导体并购潮正盛时,国内半导体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半导体企业数量较少,投资人谈论的话题都是去海外更大的市场“找机会”。但在2024年最新这一轮并购潮出现时,国内已经产生了大量半导体公司,市场也经过大大小小多轮价格战,部分细分领域已进入内卷竞争阶段。
无论从加强国内半导体产业整合的角度,还是为市场上积累的存量公司寻找出路,当下推动并购都到了一个特殊节点,国内市场也从十年前的“找机会”过渡到了推动产业龙头整合、升级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并购”阶段。
但成功并购并非易事。今年年初,去年A股半导体公司发起的多起并购最近集中发公告终止交易,失败的原因包括交易价格分歧、股东意见不统一等一系列原因。界面新闻近日采访牛俊岭,与他交流了十年内两次并购潮的时代背景、半导体领域并购案容易失败的几类原因等。
两次并购潮:从“去海外看机会”到“系统性并购”
界面新闻:“国九条”“科创八条”“并购六条”这一系列鼓励A股市场并购的政策出台后,半导体领域出现了很多并购事件,并购在当下是不是一个行业共识的热潮?
牛俊岭:目前来看鼓励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是一个确定的趋势。
从2023年的下半年IPO开始收紧以后,到2024年上市的新公司几乎很少。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政府出台了政策来支持并购重组,包括“国9条”、“并购6条”。因为IPO关闸后投资退出的路径变少,鼓励并购的政策给一级市场的投资人和创业公司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类似于看到未来退出的通道关了一扇门,又开了另外一扇窗,所以大家都涌向并购赛道,尝试通过并购实现退出。
IPO关闸客观上也给了上市公司收购资产的机会。以往上市公司想在一级市场并购合适的公司标的,但标的公司更愿意去冲上市,被并购的欲望并不强烈,导致上市公司单方面想买资产时,愿意卖资产项目较少。
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段里,上市公司和被并购标的之间开始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很多并购公告发出,但并不代表这些交易都能成功。
界面新闻:半导体行业在2014年前后也产生过一次并购潮,像紫光集团并购展讯、豪威科技私有化,你也是这次并购潮的亲历者,那时候做并购是一个什么状态?
牛俊岭:从2014年到2016年底大概三年时间,是海外并购时代。像紫光收购展讯与锐迪科、豪威科技、澜起科技从美股私有化退市,还有北京矽成ISSI私有化、亦庄国投收购Mattson(屹唐半导体的前身)、建广资产收购欧洲安世半导体等汽车产业链相关公司。那个阶段应该有10到20个案例都是海外并购。
我有幸代表中信证券参与过豪威科技与澜起科技的私有化,当时是和清芯华创作为共同投资人。
并购与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相关。拿半导体来说,十年前,像华为、中兴通讯这些大厂还没有受到美国的制裁,也没有实体清单。在全球化时代,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厂商去买芯片、零部件等,很容易买到国外厂商生产的产品,性价比都还不错。对于国内大厂,购买国外质量好、大品牌产品是当时首选。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内半导体创业者没有生长空间,产品无法进行快速验证、小批量生产和大规模量产。
直到2014年,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半导体的发展。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的规划纲要,全国各省市区出现了多只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北京、上海等地设立集成电路方向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同时,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也应运而生。元禾璞华的前身是清芯华创,当时管理着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封测与设计子基金。
但在2014年到2016年第一次并购潮时期,专注于投资半导体的机构很少,国内专业投资半导体的机构可能不超过20家。中国半导体公司总数少,存量资产也很少,优质标的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并购不是以国内并购为主,因为没有存量资产,难以开展国内并购,所以只能走出去海外做并购。
界面新闻:第一波海外并购潮出现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牛俊岭:2017年之后,中兴通讯、华为等大厂相继被制裁,国内以半导体为主的硬科技领域进入到了国产替代阶段。
国产替代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创业者变多,尤其是半导体行业,主要有两类创业者,一类是本土创业者,另一类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人高管创业者。这些创业者在英伟达、英特尔、超微半导体等这些海外半导体大厂做到fellow(技术专家)或者高级副总裁级别,精通成熟的技术和资深的从业经验。他们回国创业后主要通过微创新,降低成本和价格,做好面向国内客户的服务,就很容易实现国产替代,以替换海外厂商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像ADI、AMD这些国外厂商,毛利一般都有最低标准,比如不能低于40%,但是对于国内的创业者来说,产品有40%的毛利已经非常好了,甚至30%左右的毛利也会吸引众多创业者。
界面新闻:2017年国产替代兴起后市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并购?
牛俊岭:国产替代兴起是没有并购机会的,因为科创板的开闸,给了很多创业者上市机会的可能性,在这个阶段创业者都希望通过上市路径实现资本化,没有人愿意通过被并购卖掉公司。
这时期开始创业的是消费电子,像智能手机、家电设备常用的模拟芯片,比如无线传输芯片、电源管理、功率半导体等,相对来说是市场规模大,通过技术上的微创新、降低成本、起量快,较容易达到科创板的上市标准。
国产化替代从2021年到达顶峰后,半导体行业几乎每个细分赛道都涌现出了多家企业,半导体行业开始到了内卷的时代。内卷时代最大的特征是打价格战,毛利很低甚至负毛利。这种情况也无法做并购,因为很多企业几乎没有净利润,上市公司没有动力去并购一家毛利很低甚至亏损的企业,对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和未来产业发展都没有实质性帮助。
界面新闻:2024年IPO收紧是不是一个特殊节点?市场环境形成了一种倒逼作用力?
牛俊岭:目前看是一种倒逼机制。
跟2014年相比,半导体行业已经涌现出了较多的创业公司,存量资产变多了。现在上市通道收紧,很多投资基金因期限及DPI原因倒逼项目退出,IPO收紧加上国家鼓励并购等原因,确实出现了并购的特殊时间节点。
当下来看,退出机制倒逼的同时,也是半导体上市平台公司通过主动产业整合做大做强的真实意愿。
半导体每个赛道上市公司都出现了龙头企业,像北方华创、拓荆科技、华大九天、华勤、江波龙。国家鼓励产业并购的目的是把上市公司做大做强,通过优质公司合并,加强业务与技术整合,使其具备国际竞争力。
界面新闻:回头来看,两次并购热潮有哪些主要的不同?
牛俊岭:2014年的海外并购热潮更像是出现在特殊窗口期的“机会型并购”。国内没有存量资产,我们选择从海收购企业,大家谈的都是“找机会”。
当时优先选择的并购交易就是中概股回归。在国内创办的公司去美国上市,没文化差异又懂中国市场,收购后并购整合的难度小,成功率高。后来还去收购华人掌管的海外公司、纯外国人管理的公司,整合难度不一样,但都是在找机会。
最近的这次并购热潮更像“系统型并购”。国内半导体公司总量大,存量资产多,细分赛道又有龙头公司,无论是因为市场环境变化,还是行业发展的阶段,都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整合。
半导体并购为什么容易失败?
界面新闻:并购热潮的另一面,去年A股半导体公司发起的多起并购最近集中宣布终止交易,像汇顶收购云英谷、奥康国际收购联合存储、慈星股份收购武汉敏声、是不是国内半导体并购失败率相对较高?
牛俊岭:虽然有很多并购公告密集发出,但并不代表这些交易能够成功。
事实上全球并购失败率都很高,不只中国。只是过去很多交易不公开,而这次因为主要发起并购的都是上市公司,需要按照要求进行公告,所以关注度高,最后一旦终止,外界就会觉得失败率很高。
界面新闻:并购交易容易失败主要有哪些原因?
牛俊岭:一个并购案例,除了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外,还涉及第三方的监管、以及买卖双方各自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诉求,这些都构成了并购交易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像交易估值、交易定价机制和支付方式,还有并购标的涉及的公司实控权变更、对赌、锁定期等方面,都可能造成并购失败。
与一般的直接投资相比,并购参与方很多。涉及到买方和卖方。如果是上市公司买非上市公司资产,会涉及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少数股东。
再看卖方,卖方一般有多轮股东,不同轮次的投资人诉求不一样,有天使轮、A轮、B轮、C轮,这中间涉及一个差异化定价的问题,不同轮次投资人对公司估值、风险与收益需求不同,尤其是股东里面有国资的时候,国资对于被收购的诉求以及对价格的认可非常重要,如果国资的意愿无法顺利达成,这次并购交易就无法继续。
监管方,包括交易所和证监会,也是上市公司并购案的重要一方,虽然并购六条等相关政策给予了并购交易的多种支持,但对于并购方案的创新突破还是比较谨慎的。还有一旦交易内部信息泄露造成二级市场股价异动,也会给并购案的成功带来不利的重大影响。
界面新闻:上述几起终止并购案中,公司透露交易价格谈不拢是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是因为一级市场前两年对部分公司估值过高?
牛俊岭:2021年是全球一级市场资金流动性最充裕、热度最高的顶峰,很多投资人都投到了周期性顶部,尤其是当时火热的半导体行业,热钱太多,投了很多比较贵的公司。现在回过头来后那就是最高点。
界面新闻:2023年的时候投资行业人士形容一级市场处于“冰封”状态,近期有没有升温?
牛俊岭:之前一级市场投资人情绪普遍悲观,但从去年9月国务院开会宣布若干逆周期调节经济措施后有所好转,近期二级市场,特别是A股及港股市场的回暖也带来一些积极正面因素。
但从一级市场实际的募投管退来看,机构募资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市场上新募集的资金中国资背景基金占比较高,包括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国资直投;同时直接投资的资金属性也是国资直投基金占比较高,市场化基金活跃度仍然偏低。
界面新闻:强调退出、强调从投资项目获取回报这两年是一级市场最重要的话题。IPO收缩后,很多投资人讨论希望并购能成为退出的一条通道。但一个现实是:国内风险投资退出环节主要靠IPO,占比为30%-50%。而美国等国家主要靠并购,IPO占比不到10%。
牛俊岭:未来并购作为一条主要退出通道,占的比例会远超过IPO。
国内半导体市场的存量资产已经很多,而上市公司已经有200多家,这个数字相比欧美成熟市场上市公司已经多很多。
半导体公司未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合并;第二,上市的产业龙头公司试图去并购非上市公司的半导体企业。
过去国内并购比例小,创业公司都想走上市之路。去年IPO关闸后,未来的上市审核标准依旧很严格。未来市场是一个“并购时代+创新时代”的局面,对于以关键领域技术创新为主的公司将会走上市之路,其余更多企业将会走并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