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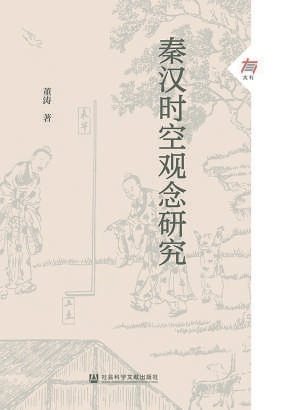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董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时空观念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和认识,也是人们认知宇宙、自然的一种最为通常、普遍的方式。史前中国先民对天人关系和宇宙、方位的认知,大都与时空观念有着紧密联系。从先秦到秦汉,中国古代时空观念及相关科学技术相互促进、长足发展,既提升了古代中国人对时空、宇宙的认知水平,也奠定了与这种时空、宇宙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的基础,使中国古代文化、科技呈现出鲜明特色。
天文学支撑起原始农业发展
从人类历史演进看,最初的原始农业的产生,促进了以时空为主轴的原始天文学、农学等的萌芽和发展。原始农业是早期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革命,它创造的人工栽培的生产方式,不仅为史前人类的食物来源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为人类的定居生活及社会组织的建立、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支撑最初的原始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就是原始天文学,这是因为人工栽培的原始农业需要有精确的时间观念,即对历法、节气、气象的掌握,这直接关系到人工栽培作物的收成及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例如错过了农时,那么农作物的歉收就会造成先民的生存危机。同时,早期人类的诸多政治、军事、生产活动,也离不开对气候、环境的了解。因此,在人类最古典的科技中,以时空为主要对象的天文学始终是人类最重要的科技门类,也是早期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早期天文学伴随着史前先民的生产、生活而一同发展。从考古资料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后的聚落遗址就发现了原始天文学遗迹。例如在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就发现如龟甲、骨笛、叉形器成组出现的随葬品;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中,也发现选用真玉精制的如玉珏、玉钻孔匕形器、玉斧、玉锛以及钻孔圆蚌等“神器”;在湖南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下层,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的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和39个排列规律的祭祀坑,在出土陶器上发现了凤鸟负日、獠牙兽面(饕餮)、八角星纹及其组合图案,显然它们既属于祭器一类,也是其时先民太阳神崇拜的写照。
从大量人类学材料看,这种太阳神崇拜遗迹,主要来自史前先民基于生存条件而对早期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等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但是在史前,这种公共服务产品往往是通过原始宗教的方式来获取的。例如史前宗教祭祀天地、神祇的祭坛等设施,就包含着观天测地、了解节气、预告风雨雷暴、驱邪祛病等诸般功能。所以,早期巫术所蕴含着的宗教与科学、迷幻与理性等内容,正是先民生产、生活所需求的各种实际功能的展现,在原始宗教的幕布下隐含着史前社会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上的诸多发明、创造。
科技背后隐藏王朝统治密码
从世界古老文明的发展看,与时空观密切相关的天文学、数学等不仅是服务于早期先民社会的文化之源,也是早期国家公共职能的重要元素。《秦汉时空观念研究》一书,以秦汉天文、测度与计时仪器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中的天文仪器资料,对秦汉时人的时空观、天人观等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该书重点探讨了历史早期的时空、天文测绘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对“规”“矩”“准”“绳”,以及土圭、圭表、璇玑、浑仪、漏刻等测绘计时工具的产生、发展、功能、运用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无疑使我们对秦汉的时空、天文观念及测绘、计时仪器有了新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该书还对隐藏在这些仪器、观念背后的科技知识及政治文化内涵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分析、研究,例如对规矩、准绳与时空、宇宙观念,璇玑、浑仪与星象模拟中的时空认知,漏刻与精确时间观念,以及威斗与时空模拟、政治斗争中的厌胜作用等的关联都做了爬梳、阐释,使我们能够知晓秦汉时期测绘仪器的功能、作用及时人时空观、宗教观的变化等。书中亦经由对天文、历法等古老的科学技术进行分析,将秦汉时人的时空观与“天人合一”“天人之际”的政治、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考察,进一步论述了秦汉时空、宇宙观念的宗教文化的特征。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根据星象制作的璇玑玉衡等天文仪器,并非单纯的测量工具,也蕴含了王朝统治者试图借助天文、星宿等宗教观念来维持人间的等级秩序的现实意图。为了更好发挥这种测量工具的作用,王朝统治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天象的简单模拟,而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通过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掌握建构起一种能够预知吉凶、防范禁忌等的宗教文化,这也是古代择日而行的思想基础。所以,尽管看似是纯粹涉及自然科学的时空观念,但是当它加入了政治、宗教的内容,就成为秦汉时代普及的“天人相兼”的政治文化,并被统治者当作对秦汉社会进行整合、控制的工具。
因此,在对秦汉时期的时空观和测绘工具进行研究的同时,亦要注重隐藏在其背后的王朝政治文化及其变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秦汉时期的科技、文化及其与王朝政治的关系。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